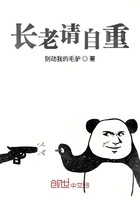八、悔之莫及
院方通知郦颐萍,程华手术十分理想,现已痊愈明天即可出院。
她屈指算来,二十八天过去了。这二十八天真是度日如年,多么难熬啊,焦躁、不安、茶饭无心,几乎天天跑医院。但是,按医院规定,无论什么人都不许见面,所以她每次来,只能看看电视而已,程华的脸、脖子始终缠着一层厚厚的白纱布,后期扣上一个半透明的面罩,面孔模模糊糊,根本看不清楚,这更增加了她的烦闷和忧虑,每次都带着几分怅惘离去。
凡做这种手术,完全把受术者封闭在一间无菌室里,直至伤口愈合方可走出来,一般要三十五天,程华因为身体素质好,二十八天就痊愈出院了。
在家属接待室,安尼小姐轻盈地迎出来,微笑着告知郦颐萍说,该院建院至今,十五年来,这一例手术特别成功。同时祝贺她选择了一个有天才的丈夫,愿她幸福,家庭美满,前程如花似锦。
“选择一个好丈夫?什么意思?”郦颐萍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了安尼小姐一句。
“夫人,这不是很好理解吗,你为什么会在亿万人中间不会认错人?认错您的丈夫?就因为每人的脸谱,区别就在这里。所以在千百人中,您一眼就会认出您所认识的人,如果没有这颗人头,试想,您能区别得那么准确无误吗?那么,程先生换了另一个人的头,他的脸谱就是那个人的了,这当然意味着您选择了一位新配偶。我们曾经多次进行过这种手术,而且是夫妻双方事先商量好的,各自愿意。”
“啊!”郦颐萍脑袋轰的一声,顿时眼前一片漆黑,两腿发软,只“啊”了一声,跌坐下来,再也说不出话了,过了好一阵子,不知是安尼小姐采取了急救措施还是自己苏醒过来,她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长长嘘了一口气,用手掐着发胀的太阳穴,轻轻敲着几乎要炸裂的头,瘫坐在沙发上,站不起来,泪水恰似珍珠项链断了连接的丝线,颗颗珍珠噼噼啪啪地落了下来,润湿了一大片地毯。此刻,她只有泪水、悲伤、悔恨,没有一句话,每根神经如同冻僵了一般,停止了运转,失去了传递信息、思维、判断的功能,呆若木鸡。安尼小姐坐在她的身边,说:
“那么,您选择的时候,没有和丈夫商量好吗?不知道会出现这种事情吗?”
“我想得很简单。”她摇摇头。
“噢,夫人,您瞧,他来了。”安尼指着门外,这时,程华由一个人陪同走进来,安尼说:“夫人,这就是程华先生,您看手术做得多好。程先生,您夫人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拉米的头被移植成活之后,很快就恢复了智力,这时院方把程华来到医院和到《人体器官零件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录了像,给拉米看,使他了解他的头是怎样移植到程华躯体上的,所以,安尼称他“程华先生”时,他并不感到意外。程华,暂时还是叫程华吧,四下瞧瞧奇怪地说:
“这就是郦颐萍小姐,您的夫人呀,怎么,觉得陌生吧。”
“不,”他说,“这位女人不是我的夫人,我的夫人哪去了?为什么没有来?噢,我记起来了,她,她改嫁了。那是因为混蛋史密斯欺骗了我,把我搞垮的,我不会放过他的,这个魔鬼。”最后这句话他几乎是在喊叫。
郦颐萍呆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面前的这位程华,那里是她所熟悉的程华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是程华,这可怎么办呢?她忽然想起是不是医院骗了她,是程华的身体吗?想到这里,她一下子跳起来,抓住他的手,把衣袖撸到肘部,看到一块熟悉的黑痣,喃喃自语道:
“是的,是他。”
再看,面前这位程华,是碧眼高鼻,一头褐发,方才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明白,安尼说:
“夫人,现在的程华大脑信息完全是拉米先生的,这需要您重新组合家庭,适应新的生活变化。“
郦颐萍惊讶地说:
“头颅移植手术都这样吗?”
“不,这需要预先声明,向院方提出要求,保留受术者原来大脑的信息,只有这样,我们才进行特别处理,把受术者大脑储存的信息,在手术中间输给您购买的那个头的大脑。这样,术后他的思维就是原来的思维了。凡是不预先声明者,我们一律视为放弃原有信息。当然,输出原信息是很费钱的。而且术者目的,多半是想换到一个比自己原来的头更有天才的头,所以,建院十几年来,提出这种要求的很少,我们只做了十三例。”
安尼说完,又补充道:
“您会幸福的,他是一位很能干的经理,会有可观收入的。”
“别说了。”郦颐萍心烦意乱,如同一团乱麻的思绪,怎么也理不出个头来,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今后怎么样她也不知道,照现在看来是凶多吉少,前途莫测,生活道路维艰。
拉米的一支烟吸了一大半,这时又说话了,一口特达尼市的方言土语,浓重的土音,郦颐萍一点也听不懂,没有办法,安尼小姐说:
“拉米先生,啊,不,程华先生,请您用世界语讲话吧。”
“您叫郦颐萍小姐,我不认识您,恕我直言,小姐,我是经营化妆品的商人,三年前是被同行史密斯用卑鄙的阴谋手段,把我搞垮台了,公司倒闭,经济破产,老婆出走,孩子流浪街头,现在我是孑然一身。但我不想组合什么家庭,我已厌倦了,讨厌所有的女人与我生活在一起。家庭,我诅咒所有的家庭统统崩溃、瓦解,他给我的心田留下了永远不能磨掉的疤痕。您,小姐,恕我冒昧地说一句,只能做一名佣人留在我的家。”
郦颐萍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令人无法容忍,她一挥手,怒不可遏地叫起来:
“放屁,滚出去。”
程华,不,该叫拉米,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不理解郦颐萍为什么突然发起脾气来。还没等拉米出去,她把便携式冰仓抱起来,冲出医院,向寓所跑去,边跑边伤心地流泪,一滴滴泪珠打在冰仓的透明罩上,程华的头在泪水的冲刷下变得模糊不清了。
郦颐萍像置身在十冬腊月的暴风雨中,穿着单薄的衣裤,周身被冻得麻木了,继而僵直了,失去了一切知觉,机械地向前跑着,跑着,永远不停地跑着。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犹如一个没有思维,没有身体,没有血肉的幽灵,在无始无终,无光无热、广漠荒寂的黑暗宇宙中急驰的一粒尘埃,漂泊着,游荡着,没有目的,没有追求、没有希望,看不到光、看不到人、看不到周围的一切死的物体和活着的精灵。只有一个念头,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眼前发生的悲剧无法挽回了。
她像着了魔一般,两条腿不受意识的支配,不停的运动着,疯狂地向前奔跑。一个柔弱的女子,哪里经得起这样猛烈的狂风暴雨的突然袭击,她始终支持不住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像一棵娇小的幼树,被拦腰吹折了。
九、此路不通
她迷迷糊糊地跑着,神差鬼使般的进入了高速公路,一辆黑色轿车迎面飞驰而来,以每小时250公里的速度向她冲击,郦颐萍的生命之火在一秒一秒地熄灭,死神一步一步的向她逼近,转瞬之间,她的灵魂就会升入天国,人间的烦恼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了,留下的只是历史陈迹,千种情思,万般愁绪,都会在冥冥之中得到慰藉。
郦颐萍向着汽车奔跑,黑色轿车向她冲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汽车上的电脑以每秒百万次的速度运算着,精确的计算障碍物的距离,汽车和郦颐萍进入了危险间距,车内出现了危险的信号,同时传出切断油路和紧刹车闸的命令,那年轻的司机踩了死死的一脚,脚自动也起了作用,车戛然而止,停了下来。可是,郦颐萍的脚停不住,还在奔跑,撞在了汽车的左边大灯上。黑色轿车后面一大串汽车立刻被迫停下来。
那年轻的司机愤怒的下了车,向她狂暴地叫喊起来,可是,她已经昏倒在公路上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是谁,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小小的诊所里。她的伤并不重,医生没费多少时间,她便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在沉沉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这丝光使它恢复了对周围的感知。
她没有升入天国,她依然是这个尘世间的生灵。此时此刻她所感觉到的只是做了一场梦,一场噩梦。可是当她记起往事,看到床头的冰仓时,意识到现实生活比噩梦更加可怕。一念之错,可能铸成千古悔恨,这沉重的打击,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郦颐萍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不知今后的道路怎么走。
她真想立即飞回家乡,再也不离开母亲的身边了。可是,她怎么能把程华的身躯丢下不管呢?她是很爱他的呀,尽管在生活中她与程华有种种矛盾、纠纷、吵嘴,那不过是在夫妻生活这盘香色俱佳的菜肴中,加入一点辣味和五香粉,更增加几分迷人的味道,在爱情的长河上激起的涟漪和浪花。这一切,是爱的长长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啊。当她和他回首往昔岁月时,迂回曲折的小小插曲,是他们品评爱情生活的幸福滋味的所在。
她,怎么能把程华的身躯抛在异国他乡而自己回家呢?
唉,爱情生活的浪花、彩点、五香粉,多么迷人的词呀。只是,只是这一次可不那么浪漫,简直是狂风恶浪,电闪雷鸣,苦涩的碱水,给她留下的绝不是美好的记忆,而是在心灵深处刻下了难于磨灭的伤痕。她,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程华的头颅和他的身体无可挽回的分离了,她悔恨自己在丈夫面前太没有主见了,不然,绝不会出现这么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决心把真实情况向拉米说明,得到他的同情和谅解,把程华的身体还给她。她抱着一线希望来到拉米的住处,陈述了她的苦衷和想法后说:
“先生,实在对不起,我把全部真实情况都向您讲过了,这恐怕伤了您的心。当然,这件事需要和您商量,因为再把您的头送入《人体器官零件公司》去,把我丈夫的身体还给我,是一件痛苦的事。”
拉米沉吟了半晌,他的心潮起伏着,难道他应该放弃天赐的生命吗?没花一文钱的投资,换来了宝贵的生命,难道还要拱手相让吗?再回到那冷冰冰的寂寞的人体零件仓库里去?拉米以他的道德标准,权衡着得失,无论如何他不能放弃生命,无价的生命。他冷笑道:
“小姐,您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是,您要知道,我也有我的难处啊。这样吧,您购买头颅的钱和手术费用我加倍的付给您。您总该满意了吧,小姐。”
“不,先生,我不要钱,我需要丈夫,需要充实的生活,金钱是买不到我和丈夫之间纯洁、真挚感情的。”
“小姐,您的感情我不理解,我毫不夸张地说,特达尼市全体公民,都不会理解。”拉米说。
“我不信,言过其实吧。”她回答道。
“我的哲学是,一切为了金钱,它是人生意义的总和,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拉米冷漠地说道:“您应该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
“实在太可怕了。”郦颐萍周身几乎在颤抖,说:“在我的道德规范中不是这种赤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否则,我是不会冒昧前来商量这件事的。”
“哈、哈、哈!”他笑得叫人毛骨悚然,“这不可能,我也不相信,我的夫人就因为我破产了,成了穷光蛋,才出走的。后来,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公司里当一名职务卑微的小职员,父亲给我的日薪少得可怜,刚刚够我的生活开销。”
“父子也这样?不可思议。”她睁大了眼睛。
“我说过,一切为了金钱,道德、信仰、伦理、感情、爱情、思维、理论等等,不过是金钱的附属物而已,这是特达尼市最时髦的理论,极为平常。为了赚钱,人们干出的任何事情,谁都不会感到奇怪。”
拉米说得很平静,似乎这里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可改变的,伦理道德,做人标准,亘古以来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稍停顿了一下,又述说起他的一段不幸遭遇。
那是一天的早晨,他破产后的第十七天,没有到父亲的公司去上班,处理他的产业。在沉重的压力下,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就是这天早晨,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耻辱的日子,他把惨淡经营了十几年的总公司和子公司做为抵债移交给了他的对手史密斯先生。在移交仪式上,史密斯是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他讲话拿腔甩调,就像法官对犯人那样横眉立目。就是这个该千刀万剐的史密斯把他所有的产业吞吃掉了,把他挤入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行列里。就在这晦气的一天上午,他用颤抖的手在交接书上签上了他那不光彩的名字:拉米。
如果他不是一个刚强的汉子,他会当着台下几百人的面落下泪来,事后也许会自尽。可是,他没有。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母时,连笔也拿不住了,滑落在桌子上。他谁也不看一眼,掉头跑了出去,失魂落魄的冲到大街上。他刚刚穿过三条街,一颗子弹射过来,击穿了他的心脏,当即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回忆到这里,他从痛苦中回到现实,说:
“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可能有人把我送到了医院去抢救,通知了《人体器官零件公司》。想不到我还有今天。按理我应该谢谢您呀。”
郦颐萍听到这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清醒还是做梦。和这样一个只知金钱,不懂感情的拜金教徒在一起生活该是多么痛苦。她说:
“难道你不会想念自己的孩子吗?”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不为儿女忧心如焚呢,何况他的儿子在街头流浪。他低下了头,显然是动了感情,家庭崩溃,妻子出走,拉米身亡,这可能是天命,让拉米的孩子承受最不幸的生活待遇。
“有什么办法呢,我找不到我的儿子了,不知道他在哪里。即使找到,事隔这么长时间,他可能不认我这个爸爸了。”他闭上了眼睛。
“那么,您妻子不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吗?她不想孩子?”郦颐萍又问道。
“不会的,她已改嫁,另有新的欢乐,以往的生活如同青烟,早被时间的轻风吹散了。小姐,您的心肠太美好了。可惜,商人,不,不是所有的商人,是有的商人,感情是有限的,他们有无限的尔虞我诈,想方设法搞垮对方,而且是不择手段,这就是我们的信条。”拉米叹了一口气,又说:“我不得不去适应,我改变不了这种生活,只能顺其潮流飘游。”
“我明白了,先生,再见。”郦颐萍说完推门走了。
拉米追出来,赶到她面前说:
“小姐,您不是要怨恨我。我也有我的苦衷,您想过吗?我的大脑信息,所有的记忆都是我原来的,那么,我的言行、信条、道德、思想、观念……总之,一切都是固有的,都是拉米的,不是程华的,我怎么会违背自己的意志去****不愿干的事情呢?”
“拉米先生,我明白了。我不难为您。但是,我对失去亲人的心情,希望您能理解。”郦颐萍痛苦地低下了头。
拉米沉吟了半晌,说:
“您客居在此,不明白特达尼市的规矩,所有购买、移植头颅的人,都要在手术协议书上写明,必须把植入头颅大脑中的信息,经过大脑信息处理系统的筛选,把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那部分抹掉。这样,植后的头颅,只保留知识和智慧,而再也不记得过去的家眷、亲人、同事了,换上被植者的大脑的生活信息,只有这样,头、身才是个统一体。面容不同,这也要妻子预先同意才成。像这样做的保留移植头颅的全部信息,这算是一个例外了,我也无能为力。您虽然为失去亲人感到很痛苦,但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是值得庆幸的,不然,我这个人就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真是悔恨莫及。”
“您还有补救的办法,程先生的头不是保存在冰仓里吗,您再找一个完整的身躯,重新移植一次,就能恢复您丈夫的生命了。”
“谢谢您的关照。”郦颐萍走了。
这时,她才意识到,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拉米坚持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在特达尼市,法律明文规定,头颅移植后一切活动有充分的自由,生活道路、宗教信仰,参加党派等等,可以重新选择,被植头颅的大脑信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但被植入身体之上,一切思维活动就是正常的、合法的,他人无权干涉,更无权强迫重新手术或对大脑信息进行重新处理。也就是说,在这种法律规定下,拉米完全有理由拒绝郦颐萍的要求。
拉米看着她走远了,不无感慨地说道:
“可怜的人。”
十惊心一幕
在郦颐萍到处奔波营救程华的时候,她看到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使她痛苦得几天睡不好觉。
有一天,安尼来找她,约她去散散心,不要老是为丈夫的事而苦恼。郦颐萍说:
“我没有心思,哪里也不去。”
安尼小姐对着镜子扭摆纤细柔软的腰肢,毫无顾忌地说:
“你这个人真是死心眼儿,男人算什么,不过是墙上的泥皮,身上的衣,爱穿就穿,爱脱就脱,什么爱情不爱情,说穿了,不过是性激素在捉弄人,叫人神魂颠倒。你说是不是。哈,哈,哈。”
这一段时间,郦颐萍和安尼小姐之间经常接触,产生了一点友谊,在寂寞的时候,她常常来找郦颐萍,彼此也不像刚见面时那么客气和拘谨了,安尼小姐充分解放的性格也渐渐显露出来。在这样一位女性面前,郦颐萍尽管有很高外语水平,但是,这时她连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苦笑了一下,算作回答。就这样,她被安尼拉走了,去看安尼最感兴趣的事。
这是一个天朗气爽的周末,微风拂面,街心花坛的红花绿叶、萋萋小草散发出怡人的清香。她们驱车到郊外去参观一次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情景。
郊外是一片旷野,稀疏的林木,点缀着这块绿毯般的草地,这里是远郊,显得古朴而具有原始的自然风貌。制片厂大队人马来到之后,破坏了这里恬静和谐的情调,变得格外烦乱噪杂,一切现代的、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所具有的病症,噪音、污染、拥挤等等,正在向远郊蔓延着。拍片器材已运到现场,摄制组人员已准备就绪,在很远处还有一大群观光的人,附近停放一架小型直升飞机,她和安尼刚下车子,现场拍摄就开始了。导演通过无线电话喊着:
“各组准备好,马上开拍。”
“准备就绪。”各组陆续回答着。
“好,开始。”导演命令。
一个衣着不整,跑得满头大汗的人冲过镜头,直向附近的飞机跑去。他的后面很远的地方,几辆警车尖叫着警笛,车篷上的红灯在不停地闪亮,紧紧追过来,也冲过摄影机镜头,这时推成近景,两个警官在对话:
“不能放过他,他偷了那么多的钱,在我们眼皮底下溜掉太丢脸了,人们会骂我们无能。”
“放过他,上司也不会同意。”
“糟了,他向直升飞机那边跑了,他若登上飞机我们不好办了。快请求派一架飞机来。”
“总部,总部。”一个警官在通过无限电话呼叫。
被追扑的那个罪犯钻进了飞机的驾驶舱。警车飞驰过镜头。直升飞机的引擎发出轰鸣,旋翼飞转,几分钟后,机身轻轻地摇动起来,慢慢向上升去,很快便进入预定的位置,驾驶员报告说:
“高度189米,位置气垫上空。”
“好,准备……”导演回答。
这时,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道:
“导演,不行,气垫不知怎么搞的,鬼才能说清楚,它有点怪……”
“少罗嗦,怎么回事?”导演不耐烦地说。
“气垫漏气了!”
“停止下跳,返航。”导演抓起无线电话,向飞机下达了命令。
郦颐萍无心看这些他根本不感兴趣的事情,不过她还是问了一句:
“安尼小姐,他们在干什么?”
安尼仰头望着返航的直升飞机说:
“这是拍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一部叫座的影片,导演设计的一个惊险镜头:一名罪犯在被警察追捕过程中,钻进一架待飞的直升飞机里,劫机起飞,又从飞机上跳下来逃走。是从189米的高空跳下来的。”
“噢,那不把影星摔死了吗?”
“地面有气垫,摔不死。但是,明星是不干这种用生命换铜板的职业,那些明星同老板订合同的时候,就明文写上,哪怕是极小的冒险,他们也不干。所以,老板不得不出钱雇佣替身演员。“
“什么叫替身演员?”
“就是代替那些明星从飞机上或高层楼房顶上跳下来的演员。凡是有生命危险的镜头明星都不屑一顾,让那些卑微的、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去干,然后,老板给他们一笔不算多的钱,就算是冒险的报酬。”
一切又都准备停当了,上述场景又重新来一遍,直升飞机起飞,悬在气垫上空,导演通过无线电话指挥着,驾驶员说:
“现在,飞机在189米上空。”
“好,开拍!”导演喊了一声。
这时,摄影机对准直升飞机。不一会儿,周围看热闹的人,发出一片惊叫声,郦颐萍抬头看时,只见一个人跃出飞机,飞快的向下降落,飞机向远处飞去,那人还在迅速坠向地面,她看到从飞机上跳下来的人没有伞,紧张得不由自主的喊了起来:
“唉呀,糟了!”
她张着的嘴惊得闭不上了。安尼似乎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她在那里看得十分开心,跳跃着,双臂向上高举,拍着手欢叫着:
“真棒,比那一次都精彩!”
这时,那个人又在空中打了两个滚翻,以每秒五米的速度冲向地面。郦颐萍看到这里,不由得周身哆嗦起来,激烈跳动的心,紧紧用双手捂住眼睛,这种刺激实在太强烈了,她有些经受不住,凄苦的叫了一声:
“这个人完了。”
安尼微笑着把她的手拉下来说:
“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每当听到有这种拍摄我是必到的,有的人从二十二层楼的晒台上跳下来,还有个人从340米高的电视塔上以每小时190公里的速度跳下来。但是都没有这次精彩、开心,那些人跳的很笨,独有这次,在空中还有花样儿,真开心极了,老板会多补偿他钱的。”
那人落在一块直径二十七米,厚三米的气垫上,郦颐萍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心房渐渐安静下来,安尼拉着她的手说:
“走,看看这位可怜的替身,他真有点本事。不过,也有摔死的,有一次,气垫漏了气,那个替身当场就摔死了。”
“这太残忍了。人摔死了怎么办?”
安尼小姐笑道:
“摔死就摔死了,老板为赚钱,替身演员也是为了钱,死个人算什么。合同写得清清楚楚,一切生命危险自负,就完了。”
说话间,她们已来到刚刚从空中跳下来的替身演员面前。当她们看着面前这位空中飞人时,都愣住了,原来是拉米。拉米看看她们,低下了头,说:
“为了重振家业,击败史密斯,我要赚到一笔钱,不得不来冒险的。”
郦颐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好像是她从飞机上跳下来一样,由于过分恐惧、可怖、害怕的刺激双腿而不停地抖动,抱住安尼小姐哭起来说:
“安尼小姐,程华太可怜了,一但气垫漏气,他就会粉身碎骨的呀!”
女人的心是热的,也是软的,尽管安尼在这种社会中长大,但,她还是流下了同情的泪水,默默地扶着她离开了拍摄场地,边走边说:
“夫人,在我们这里,用生命换钱的事太多了,我见惯了麻木了,习以为常。人在这种环境生活惯了,心也变得像铁石一样硬,像霜雪一样冰冷。您的感情像一团火,炽烈的火那样烤着我的心田,使我感觉到温暖,唤醒了人类固有的本性和良知。您和程先生的感情太纯真、太高尚了,在我们这里是很少见的,实在可贵,我真羡慕您和您丈夫程先生,你们是幸福的。您使我感到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充实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您放心,我一定尽我微不足道的力量,使您的丈夫再回到您的身边。”
“太感谢了!”
当郦颐萍一个人向寓所走去的时候,她扪心自问:
“我自私吗?拉米不该得到他再生的权利吗?”
她又回答着:
“他应该有这种生活的权利,但程华,程华的身躯太可怜了,不能,不能这样。”
爱情的火使她想不下去,爱情大概都是自私吧。
十一一号新闻
拉米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老板给他的酬劳金刚好够买一条纯种牧羊狗,或是一条被淘汰的警犬。他来到预先约定好的狗贩子那里,把钱丢过去,那人点了一下,牵过一条毛色美丽的中等个头的狗来。这条猎狗虽然不太大,但在棕色的毛间,周身分布着许多不规则的、大小不等的圆形白色毛斑,看去很像一只小梅花鹿,虽然不是特达尼市达官显宦、富贾豪绅夫人、小姐视如掌上明珠的名贵品种。可是,这条狗很乖,能做出很多令人发笑的各种动作,但它对破案却不那么用心,警官老爷们因而很讨厌它,盖棺论定,它是一条不务正业的狗,所以警方就把它淘汰了,被狗贩子收了去,又转到拉米的手里。
拉米为了振兴被史密斯搞垮的家业,以图东山再起,他不惜用生命去换取这笔钱,作为发迹的本钱,买下这条不受警方欢迎的狗。这样,被拉米称为“梅花鹿”的警犬就朝夕和他相伴了。只从那次空中冒险之后,他再也没有谋到职业。他主意拿定,买下这条狗,做一笔狗交易,成交后积蓄一点钱,然后,走他的老路,去经营他的化妆品。但现在不行,银根太紧,没有力量与史密斯一争雌雄,故而,他偃旗息鼓,卧薪尝胆,为日后东山再起养精蓄锐。他研究了各种商品,他看中了狗这个能跑能叫的商品。当今,养狗之风大盛,主人对狗关怀爱护无微不至,有的人为了赚钱,居然办起了狗食店、狗服装店、狗美容院、狗医院、还有为旅游者开的狗旅馆……可谓洋洋大观。绅士、淑女不惜重金购狗,不吝钱财为爱犬购买华贵的高级服装,以及各种美味佳肴,享尽了人间富贵生活。
谁如果说狗不是一个好动物,是传播狂犬病的罪魁祸首,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拉米知道,狗是最受人类垂青的动物,这是世上所有动物都要刮目相看的。追其根由,恐怕是因为狗对主人摇尾乞怜、百依百顺、又会看家吧。可现代的狗又有了新的职业,是家庭的点缀、玩物、为主人逐除寂寞和无聊的最理想的动物。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大概他没有预料到,当今狗会身价百倍。
拉米有一个小小的统计,本市有九百二十万只狗,年营业额五十亿特达尼元,多么可观的交易呀!
狗的最大用处不在这里,那些养狗人不惜重金为爱犬开销,他们觉得有一条美丽聪明的小狗在身边,就能使空虚的大脑充实起来。在他们的灵魂里有一条跑来跑去,狺狺吠声,是多么有趣呀。
拉米虽然看到了特达尼市种种人类社会的变态现象,也深知可以从中赚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他只有一条被警方淘汰的“梅花鹿”,从这条不算名贵的狗身上能榨出多少利润呢?他挖空了心思,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于是乎,他终日不出门,潜心训练这条“梅花鹿”,教他本领,主人处在危急中或是危险中时,它能去救助。经过日夜努力,“梅花鹿”终于学到了这种本领,拉米便把它浓妆艳抹地打扮了一番,拉到街上,到富人经常出入的商场去转。
这天,他正牵着“梅花鹿”闲转时,看到一位拄拐杖的老头,拉米认得,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计算机大王,真是巧了,必须在他面前表演一番。拉米在老头走到身边时,突然装作昏倒了,“梅花鹿”见主人倒下,便狂吠起来,在马路上蹦跳不止,终于拦住一辆小轿车,咬住司机的衣角,拽到拉米的身边。司机看到一个气息奄奄、口吐白沫的人,以为是得了急病,便招来几个人,把他抬上救护车,呼啸着奔向医院。汽车刚刚跑了两分钟,拉米便苏醒过来,用微弱的声音说:
“先生,太感谢您了,我癫痫突然发作,多亏我那条狗了,拦住您的车,又遇见您这样好心肠的人,我得救了。现在,我好多了,不必到医院去了。这是给您的报酬。”
一条狗,救了身染暴病、突然发作、生命垂危的主人,成了养狗社会的一大新闻,报纸、电台、电视台,蜂拥而至,采访拉米和他的“梅花鹿”,连日播出、刊登消息、发评论、有关养狗的知识……当然,上述种种,都是拉米花了很多钱,精心策划的。“梅花鹿”,这条被警方抛弃的狗,它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般荣誉,转瞬之间,身价百倍。那些体弱多病、生怕突然病倒的豪富巨贾,对那些私人保镖并不信任,天知道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也许盼着主人早点死掉,如果顺手还捞到一笔钱,也可能与黑社会的人合伙蓄谋害死他的主人呢,人是最不可信的。于是,他们感到不如有一条忠实于自己的狗在身边稳妥。所以,当这样的消息传出,那些体弱多病的豪富和树敌过多的巨贾,为安全计,愿出高价争先恐后的购买这条“梅花鹿”。
拉米看准了这笔交易是有利可图的,达到了他所希望的数额之后,便把“梅花鹿”拍卖给了那位年近七旬的计算机大王。
有了这笔钱,当然还不能和史密斯一决雌雄,因为这笔钱和史密斯现有的资本比,太微不足道了。这笔钱只能使他的生活略安定下来,不至于为了糊口而疲于奔波,给他东山再起,与史密斯决战赢得一刻喘息之机。他非常清楚,必须另找进财之道。
天无绝人之路,机会来了。
有一天,他约朋友去海滨划船,汽车进入海滨停车场,碰到一位某大学化学系教授,他们都是老相识了。当时,太阳正毒,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因而,他们都没有去划船,都想跳到水里去游泳,当他们换上游泳衣的时候,对面走来一位姑娘,老教授无意中瞟了一眼,发现那位姑娘满面粉刺,挺漂亮的脸蛋,被粉刺影响得难看了,教授感叹道:
“这姑娘若抹上布朗教授新发明的105号青春剂,不用三天就会粉刺全消,面如桃花。”
拉米的朋友并没有介意这件事,向前跑了几步就投入大海的怀抱了,而拉米以他多年经营化妆品的职业嗅觉,敏锐的感觉到:“谢天谢地,苍天有眼,赐我良机,这是击败史密斯的强大武器呀!拉米虽然听了这消息为之震惊不已,但外表平静,让人看来是若无其事的问了一句:
“哪个布朗?”
就是F大学化学系的那个副教授,全系只有他是个单身汉,他偶尔发明了这个小玩艺,其实也很简单,用百分之零点八的105号剂加入雪花膏里,或是其它涂面油、膏、粉里都可,加后擦面即可痊愈。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拉米微笑着挽起教授的胳膊下海去了,但他心里确在想:
要想办法搞到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