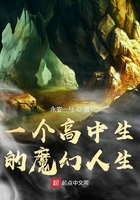过了一段时间,雅各布·让对犹太人涌入上海的原因又有了更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带,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日军占领区内的一个“孤岛”,只能通过海路与外部世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无法在上海地区继续行使自己的职权,而日本占领军当局一时也还来不及在上海建立起地方傀儡政权,使上海在对外事务方面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无需办通常的入境手续就能进入的大城市。特别是从1937年秋至1939年秋,近两年时间里,外国人进入上海不仅不需要签证,而且也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预先找到工作并出具警方提供的品行证明,这对那些被关过集中营、以“非法”途径逃离欧洲、来到上海时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来说无疑是个天赐良机。
那么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欧洲犹太难民是什么态度呢?雅各布·让引用1939年中国人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的刊文作了介绍:“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我们只要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我们应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
这些欧洲犹太难民为什么偏偏选择已经被日本法西斯占领的中国上海,并且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到上海的呢?雅各布·让走访了很多从奥地利来的同胞,他们满怀感激地记住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但在当时,为了保护这名向他们这些落入生命即将被剥夺的茫茫苦海中的人抛散“救生圈”的恩人,为了后来的犹太同胞能够继续得到这名中国人的帮助,他们暂时隐去了他的名字。雅各布·让在报道中说道:
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以签发赴上海的签证的方式救助了大批犹太难民。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上海正处于“护照签证失控”的状态,欧洲犹太难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入境,但犹太人仍须持有签证,以证明目的地才可获准离开奥地利。签发签证的人也知道,多数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的目的地不一定是上海,但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同情和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还是向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了成千上万份签证。很多犹太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从意大利乘船或者通过陆路由苏联顺利抵达上海。当然也有很多人利用手中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菲律宾或者其他国家。
逃到上海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如何?遇到困难到哪里去取得应急的和必要的帮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雅各布·让又陆续作了一些记载和报道:
鉴于进入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对难民提供援助与救济的组织也增加了。上海的犹太富商、社团和国际犹太救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帮助、救济和安置那些几乎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
1938年10月,在沪犹太富商嘉道理家族成员霍瑞斯·嘉道理出面召集成立了“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该团体拥有多名犹太名流,到1938年底,共筹集到8000美金。另一名嘉道理家族成员埃利·嘉道理则和有关人员成立“复兴基金”,目的在于帮助犹太难民创办一些中小企业,增强自救能力。
沙逊家族的第三代核心人物维克多·沙逊捐了15万美金作为“复兴基金”特别款项,不仅如此,他还捐出苏州路400号的河滨大楼,作为上海犹太难民接待站,使数百户犹太难民得以入住。
同样富有的亚伯拉罕家族和依托格家族开设了公共厨房,每天向约600名难民供应伙食,著名的阿哈龙会堂也被用作接待站和难民厨房。
此前记者已经报道过的,从1939年1月起,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相继成立了爱尔考克路、熙华德路、汇山路等多个路段中的多个犹太难民营,这些相对集中的难民营几乎合成为一个“工”字形。
与此同时,国外的犹太人组织也给予了上海犹太难民大力支持。如1938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的“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为上海犹太难民提供咨询、联系、贷款等各项服务。
最突出的是美国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JDC),该组织于1939年成立了上海办事处,当时每隔一段时间即写出上海犹太难民情况的报告,并在美国募集了大量的捐款,一时成为当时援助难民经费的主要来源。
其余的有各国旅沪侨民、中国教会和其他一些非犹太救援或慈善团体,如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伦敦会及美国育婴堂等也都捐房、捐款资助犹太难民。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市民在自己也沦为难民时,依然克服种种困难,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了欧洲犹太难民,尤其是虹口地区的中国居民,腾出了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不少中国医院尽管缺医少药,还是腾出地方收治犹太难民,挽救了不少垂危的生命。
那些俄国犹太人还巧妙利用自己“中立国”的特殊身份,成立一些救济组织,将救助对象从原来的东欧犹太人逐渐扩展到德奥犹太难民。
记者在此除了对这些以及那些至今不知名的在危难中无私地向犹太难民提供帮助的救援组织和个人进行记载并表示感谢外,也是为了向还在陆续涌入上海的犹太难民提醒,在他们走投无路或者需要各种各样的帮助之时,可以去向这些救援组织求助!
对于犹太难民的生活状况,雅各布·让这样写道:
从纳粹魔掌下逃脱的犹太难民在离开维也纳、奥地利、德国以及捷克、波兰等德占区时,被纳粹以种种理由的抄家、搜身、“抽税”等方式搜刮殆尽,到达上海时,大多身无分文,生活极其困难。绝大多数人因此选择了物价、房租相对便宜的虹口地区,如同更早光临的日侨。历经沧桑,铸就了我们犹太人坚韧求生的特性。
在来自德、奥等国的犹太难民中,有不少知识阶层人士,如医护人员,他们纷纷组建诊疗所、难民医院,在难民救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9年3月,以这些医护人员为骨干,在华德路建立了一所拥有120个床位的难民医院,内部居然设有X光部、牙科、眼科及产科等。记者前往调查了解,据称其收入足以抵支。
难民中的那些教师则组织难民的子女学习,对成年难民进行职业培训,开展自救;难民中只要有编辑记者,他们就会办报办刊,此时难民营中有着多份德文报纸(比如本人,就供职于《上海犹太记事报》);只要有艺术家的地方,他们就会举行露天音乐会,演奏萧邦,演奏德沃夏克,上演意第绪戏剧。
毋庸讳言,我们犹太人素有经商的天赋,不少犹太难民在提篮桥一带开办了许多咖啡馆、餐馆、杂货店、理发店、药房和面包铺等。
“八一三事变”后一度萧条的虹口街市竟然喧闹起来。以舟山路为中心的街区处处可见德文店招,奥式露天咖啡馆也出现在街头和屋顶露天平台,提篮桥一带因而被称作“小维也纳”。
对于绝大多数难民来说,找不到正式工作,就意味着只能到处打零活,替洋行看门,干杂差,或者在街头练摊。
在武定路的旧货市场上,便有不少犹太小贩。记者就亲眼观察了其中这么一位,他不顾过路人的奇异眼光,大模大样地站在一只破木箱上,手里挥舞着一块块肥皂,“高人一等”地与客人讨价还价,那发音不准的英语听来有些滑稽,偶尔还夹带一句沪语吆喝:“犟来,犟来。”见买主面露难色,他便侃侃而谈起来,什么原本此地摊位较挤,多亏近邻几个中国摊主紧缩摊位,才让出一只木箱的地方给他;什么那肥皂是他自制的,在欧洲已流行多时……直说得买主心动。肥皂成交以后,他又送给买主一瓶廉价染色药水,以示友好。傍晚时分,犹太小贩在那只木箱上发了一会呆,见实在无人光顾,才拉起那只装有四只轮子的木箱,回收容所吃晚餐,吃他喜欢的馄饨、菜饭和中国白脱——腐乳。
虽然生活艰难,但是我们犹太人仍然在上海这块土地上顽强生存,并且保持着我们犹太民族特有的乐观和幽默诙谐。但不可否认,也有些犹太人因穷困不得不靠乞讨度日,还出现一些盗窃、打架争吵。生活更为困难的是那些无一技之长的妇女和以及儿童。因之也出现了某种丑恶现象。据了解,有五名妇女为生计所迫,登记卖淫……但绝大多数犹太难民仍能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共同谋生。
在历经了纳粹迫害,千万里颠沛流离地逃生,登上了上海这片“诺亚方舟”并开始艰难度日,除了衣食住行的艰辛苦楚,宗教信仰的坚持与心灵的慰藉与精神家园的建设,更为重要。为了继续坚持开展我们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活动(虽然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的犹太同胞的宗教礼仪与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在这片并非很大的“犹太社区”,建立了几座同胞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上海较著名的犹太教堂,共有三处——虹口区华德路上的摩西会堂、位于西摩路500号的拉希尔会堂和博物馆路20号的阿哈龙犹太会堂。其中摩西会堂成为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原来这里是一座三层的民居,1928年由俄罗斯犹太人设计改建为摩西会堂,1938年以后,这里更成了犹太难民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摩西会堂是座尖顶拱门的巴洛克风格的三层建筑。犹太人的安息日从每个星期的周五开始,当太阳下山了,三颗星星出现在天宇中,犹太男人们开始汇集到摩西会堂,女人则在家点燃两根蜡烛。负责主持犹太人的宗教仪式的拉比,在此为年龄到13岁的犹太小孩举行洗礼仪式。
此外,在犹太社区,也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文娱、体育、媒体出版等项活动,甚至足球运动爱好者还经常在这一方天地里组织足球比赛,并且成立了“上海犹侨俱乐部足球队”。1939年4月23日,在犹太儿童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下,第一届上海犹太运动会在荆州路体育宫举行,这是上海犹太人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运动会后,犹太难民足球队并入“上海犹侨俱乐部足球队”,参加上海足球联赛,并一直雄踞上海足球联赛甲级队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