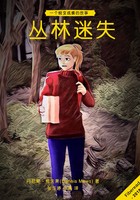“我陪着你去!”
让任可没有料到的是,荣欣绶主动提出和他一起赴沪。
“我们茶叶公司在那里有一个分公司,我正好以此为掩护。”
这是任可在向荣欣绶说自己要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任可早在成行之前,就给自己定好了此行的任务:除了想方设法帮助密尔经学院的师生筹集款项,使他们早点动身转往上海“安家”,还要多方了解一下上海犹太难民安置与犹太社区的情况,因为那里有不少是通过自己和维也纳领馆发给的签证逃来的,自己当然愿意善始善终,看到他们在上海能够生存下去。同时,自己还有完善“云南计划”的任务,也要深入了解一下推行该计划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任可心中有一个对谁都没有说出来的疑问,隐藏在心头很久了的一个疑问,他想到上海实地查看后,看看能否廓清,那就是为什么“云南计划”自己在维也纳时就有所耳闻,但是直到现在,仍然还只是一个“计划”,而没有实际动作?是推行不了,还是没有人去落实?如同国民政府做许多事情一样,高射炮打蚊子——虚张声势?蒋委员长不是总骂部属“空谈误国”吗,其实,久在国外的任可早知道这是政府与军方官僚集团的事实和现实。甚至,这也是任可原来宁愿在国外工作的原因之一。另外,任可最近越来越多地听说了日本人在试图实现一个阴谋,还给这个阴谋起了一个非常形象化也特别对日本人“胃口”的一个名字,叫什么“河豚鱼计划”,或者是“河豚计划”!但是,既然是日本人的“阴谋”,处于绝密状态,在重庆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用河豚鱼来施放毒素,还是去毒求鲜,利用其美味?自己要想办法,摸清是怎么回事,而到了上海,可能通过朋友多少耳闻一些。任可想起了也是他帮助办理了签证的一位维也纳记者朋友,任可帮助他去了上海,听说他在上海的犹太人办的报纸上和上海的《申报》等媒体上,陆续发表刊登了一些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的报道,可以去找他。当然,面上的情况可以通过报纸来做一些了解,但是,像所谓“河豚鱼计划”这样的秘密阴谋,即便记者探听到了,也不敢或者根本不可能刊发在媒体上,只能是当面了解。
任可的这些想法与计划,自然是不便向荣欣绶提起的。但是,他也希望能通过自己此次赴上海“出差”这件事,证实一下荣欣绶对自己的感情,自己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作为一个结过婚的男人,能有这么一朵“茉莉花”对自己倾心,当然不免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但是,猜也能猜得到,想采摘这朵“茉莉花”的男人,绝对不止自己一个!
“告诉你,除了利用我们的分公司,我们还有一个记者朋友。你去上海,肯定愿意多了解一些情况,记者可是“无冕之王”,通过他们,比一些面谈汇报的“官样文章”可能知道更多的真实情况。”
“那记者叫什么,是谁?”
“你要带我去,到那你就会知道。不带我去,告诉你也没有用。”荣欣绶似娇如嗔地顽皮。
“那好,我带着你去。但是,我们两个是什么身份?”
“夫妻,当然是夫妻。”
“那好,我们就先假扮夫妻!”
此刻,任可还想到了一点,如果真的能向由自己发放签证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了解情况,倒必须有一个人来代自己出面。上海犹太人社区虽说是位于虹口的提篮桥一带的公共租界内,日本暂时还未染指,仍旧由美英法和工部局控制,畸形地成为了“国中国”、“城中城”般的“上海孤岛”,人如四方辐辏,一时华洋杂处,竟然成为了人才聚集、资金密集、富商巨贾密集及难民密集的地方,呈现出了一种“畸形繁荣”。但也正因为此,那里鱼龙混杂,藏污纳垢,敌特蛇潜,犹如京剧里的三岔口,各方势力在那里“摸黑暗战”。自己既需要了解情况,又不能让曾经当面领过自己签发的签证的犹太人认出来,以免暴露身份,引来麻烦,必要之时,即可由荣欣绶来出面。
主意已定,任可和荣欣绶以及“提篮飞”一行三人就上路了。任可与荣欣绶假扮新婚燕尔不久,去上海看望一对夫妻,同时,任可还是一名前来调查犹太人生活状况的博士学者,“提篮飞”南江就充当他的助手。
一行三人辗转来到上海。他们在虹口的原来的美国租界、现在的公共租界内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任可与荣欣绶既然是扮作夫妻,就合租了一套内外间的客房,南江自己单住一间。他们租住的这个地方,离“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不远,便于任可先解决要紧的筹款事项。
稍事休息,第二天,他们就来到“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
办事处是一幢哥特风格的四层小楼,一至三层都是六开间,四层顶层是两开间的小阁楼。红砖灰砖相间,倒也别具一格。巧的是,上海犹太侨领艾尔克曼与办事处负责人、常驻代表鲍伊德正聚在一起商量事情。
“我是任可,曾经担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
“哦!久仰,幸会幸会!”还没有等任可自我介绍完,艾尔克曼与鲍伊德两人不约而同站起身来,与任可热烈握手。作为上海犹太社区的领袖和专门救济犹太难民的办事处的主任,他们早就听说过任可,但没有想到任可会亲自来沪,他们能在这里见面。
寒暄了一阵,任可从怀中取出杉须贺前后两次给他来的信件和电报:“我之所以来找你们,是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立即帮助密尔经学院的师生筹集款项。这400多名师生,已经在外漂泊近一年,一路上,经过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已经身无分文的他们好不容易到达了日本,却被逼令限期离开。陷入绝境的师生只能转赴上海,但经费只能由你们来筹集提供。”情况紧急,任可快人快语。
两位犹太人当然知道密尔经学院是欧洲一所著名的学习和研究犹太人的经史典籍礼仪制度宗教传承的机构,而且知道这是目前欧洲唯一的一所保留下来了全体师生的犹太人的专门经院。
“鲍伊德,你看……”艾尔克曼向鲍伊德狡黠一笑,似乎心有灵犀。
任可本以为自己这个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可能让他们为难,为防止走漏消息,事先并没有与他们取得联系。任可一路上搜肠刮肚,想出了好几条说服他们的理由,志在必得,现在看他们似乎会心对视,不解其意。
“哦,任博士,你来之前,刚才我们正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的同胞来到上海,虽然生活跟以前是不能比了,但是,你肯定了解,我们犹太人,只要是给一块立足之地,无论如何也能生存下去,这几乎是民族的历史造就的一种生存能力。但是,我们不能丢失自己的传统,不能没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我们正缺少犹太“拉比”和宗教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虽然在社区也已经有几个“拉比”,但是,懂得宗教和具有坚定的信仰的人远远不够。不怕任博士笑话,我们正在发愁,也正在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他们的到来,简直就如你们中国人所说的“及时雨”,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所有旅途和安置经费就由我们来筹集好了,任博士不必担心!”
这真是出乎任可的预料。
“走,任博士,我这就带你去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正好能够容纳400多人。”性急的艾尔克曼说着就站起了身。
“是呀,你去看看一定满意,一定放心,它是“阿哈龙犹太会堂”。”鲍伊德也说道。
任可一行三人随着他们来到博物院路20号,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平面为椭圆形、立面为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屋顶为钢结构穹顶。
“阿哈龙犹太会堂建于1931年,是哈同为纪念其已故的父亲,独资捐献建造的。当时,他聘请了公和洋行的威尔逊建筑师给他设计。竣工后捐赠给犹太人社团,成为了旅居上海的犹太人重要的活动场所。”艾尔克曼说道,“走,我们到里面再看看。”
进得会堂,一层分布着演讲厅、会议室和阅览室,拾梯而上,二层布置了庄严肃穆的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犹太会堂,会堂可容纳400多人。
“太好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像样的一处会堂,非常适于密尔经学院的师生使用。”任可不禁赞叹道。
不久之后,密尔经学院的全体师生再次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上海。令这些九死一生的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几乎进了“天堂”。他们早已经听说,一年之前,他们逃离波兰密尔小镇不久,那里的密尔经学院就被占领的纳粹党卫军翻了个底朝天。纳粹没有搜到他们认为一定藏在那里的“圣经古卷”,丧心病狂恼羞成怒,便将师生们没有来得及也根本没法带走的所有经籍书卷,包括学生用的课本全部焚烧,这座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犹太教的高级宗教经学院毁于纳粹的战火与歇斯底里之中。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而今,在中国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找到了他们本以为此生再也无法找到的地方,延续他们的学习生活,传承他们的宗教,慰藉他们饱受创伤的心灵。
欧洲最著名的密尔经学院终于在上海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一直进行着教学活动。师生们坚持每天学习15小时的制度。中国印刷厂商协助他们印刷出版了绝大部分塔木德经文和迈蒙尼德的著作,以及哲学、伦理和宗教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一百余种,保证了该院师生的学习资料。该院在上海甚至出版发行了《我们的生活》和《新律法书》等宗教报刊。这所经学院也成为了随后纳粹对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的大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欧洲东部地区的神学院。
战后,密尔经学院师生迁至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成立了密尔经学院中央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