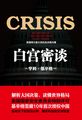法国发生的暴力革命迫使英国政府变得日趋保守,但相当数量的英国和爱尔兰民众仍然受到了革命思想影响,他们开始变得日益激进。当然,受到影响的也远不止英国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因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而心生怨恨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多。无论在哪个时代的何处角落,愤青的出生率一直都比较平稳,但是,在1790年代似乎超生了……
对于这部分日益激进的民众来说,迎接他们的将是那些害怕步法国后尘的政府所实行的高压统治。在英国,“革命群众”受到的高压尤为严重。美国虽然已经和英国脱离了关系,然而那里仍旧是理想的垃圾堆放场,从1790年起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为了逃避在英国国内受到的(他们自己找来的)压迫,纷纷踏上了前往北美的客船。由此,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第二次移民浪潮开始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者说——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外,均加入了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派阵营。随着这些人的加入,反对党,尤其是激进的反对党实力逐渐增强。
伴随着第二次移民浪潮到来的,便是在不久之后将会主导美国社会的政治社团。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社团形式,政治俱乐部风靡当时的欧洲和美洲。广大民主改革主义者充分发挥了其价值,为各种持不同政见的人提供了安全的可以自由谈论和策动政治问题的掩蔽所。然而,畅所欲言与其对立面——腹诽——其实是没有区别的,而多数的这种社团也并无实际存在意义,无非是给人一个发牢骚和扯淡的地方,以满足民众“参政议政”的欲望。拿到今天的中国来说,这类社团在早期美国社会的价值就好似网吧、BBS、网络游戏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价值一样,如果不是此类设施和组织的存在收容了诸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游民,恐怕这些家伙会满大街去扮演古惑仔,进而对社会治安造成真正的危害。其实浅薄的人在政治社团内也只能是偶尔有机会改变一下自身的角色——从跟着起哄、人云亦云的喽罗,变成可以偶尔畅所欲言、胡说八道一番的“喷子”,反正在这类社团内是没有人会来追究责任的。所以,一切问题并不会随着畅所欲言而有什么改变。
20世纪发达的印刷业与21世纪随着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可以赋予任何一个愿意求知的人不亚于古代先贤的知识量。但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到社会习惯、落后的信息传递速度、有限的印刷以及发行渠道等影响,普通民众还远远谈不上摆脱无知与愚昧,他们会本能地被华丽的辞藻、慷慨激昂的演说和相貌堂堂的偶像所蛊惑(不得不承认,直到今日这种现象依然普遍),从而成为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民众由于其掌握的信息量和政客的不同,两者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是不可能处于同一个“位面”的,许多在议政社团内被视为至理名言的看法或者政策,拿到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恐怕会显得极为可笑。民众必须在学习中进步,历史的教训将会使他们远离极端。当然,在这之前,民众将被蒙昧笼罩。发生在1793年4月的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公民埃德蒙·热内(Citizen Edmund Genet),在美国的恩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斩首示众3个月后,搭船来到北美。
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他受到了当地民众英雄凯旋般的欢迎,那些还未忘却自己曾经反抗英国国王统治的人们,将热内视为了法兰西革命的象征,当作了一个反抗暴君统治的代表。5月初,法兰西形象大使,舌灿莲花且相貌堂堂的热内先生北上前往合众国当时的首都费城,和美国政府展开正式的外交斡旋。
热内赴美的目的主要有两个。首先,当时由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集团“雅各宾派”所统治的法兰西共和国,希望通过热内的活动来洗刷其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所产生的国际恶名;其次,或者说这才是最主要的——煽动美国船主进行海上私掠(海盗)活动以袭击在加勒比海域航行的英国商船,并策动美国冒险主义者远征西属佛罗里达地区,进而达到将美国引入战争的目的,以便减缓英国集中于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法国本土所造成的压力。
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费城给予了热内非常热情的款待,而热内迷信于他在抵达美国时受到的热烈欢迎,在执行预定计划的同时,开始尝试说服美国国会反对近期华盛顿总统宣布的“完全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使其倒向法兰西共和国。很不幸,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或者说他错误地把美国政府当作了美国民众那样的存在群体。热内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官方的不满,进而萌生出敌意。
在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看来,合众国似乎应该无条件加入法国阵营,推动并开始这场浩浩荡荡的“荡涤一切专制”的大革命。但是华盛顿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却对此坚决反对。各种国会辩论的记录充斥着那一段时间的国会讨论记录,对于杰斐逊一派的主张,以及他们对于法国革命那异乎寻常的热爱,华盛顿曾公开指责“这将使合众国陷入危难”,而汉密尔顿亦在他控制报纸上发表文章多次予以抨击——“真正的爱国者对待自己的国家应像对待妻子那样矢志不渝;外国就是那些会腐蚀忠贞、破坏幸福的情妇”。
8月2日,华盛顿首次在集会演讲中公开谴责热内,质疑他是否试图将美国置于“对外战争,内部混乱”的境地。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内一反常态,不论是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还是杰斐逊为首的共和派,联合了起来一致响应总统的谴责。最后国会通过决议,照会法国政府,要求召回他们的特使埃德蒙·热内。华盛顿的谴责和国会的要求遭到了美国民众的抗议,这可能是乔治·华盛顿自印第安战争以后头一次遭到民众谴责。但是这场角力的赢家是华盛顿和美国政府,总统的个人威望压倒了那个头戴假发脸上扑满白粉、怎么看也是这种极端的手段导致了他们最后的悲惨下场。性取向都不大正常的法国人。随着支持官方的报纸大谈起革命年代“华盛顿头领”的种种业绩,民众的谴责就逐渐被服从的沉默所取代。
9月初,热内灰头土脸地离开了美洲,雅各宾派政府所希望的美洲盟友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然而,正是受到了热内的鼓舞,众多热衷政治却又缺乏常识的美国民众被鼓舞起来。他们无知又无畏,充满热情。这些人更为热忱地投入到各种政治结社和沙龙活动之中,并据此认定自己也为国家进步做出了贡献。
“宾夕法尼亚民主协会”就是这样一个在热内到来期间兴起的政治社团,由该州的数十个类似的小型团体合并而成。这个社团的成员公开支持法国、支持大革命,希望以法国为借鉴来提高国内的“自由和平等精神”。在“宾夕法尼亚民主协会”的鼓动下,缅因和佐治亚的40余个社团合并了起来,而且这些大型化的社团的主张也越来越激进。
通常,社团的领导人由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和律师充当。然后是一大群劳动者——手工业者、小农、到处打零工的无产者构成。他们在领导人的鼓励下坚决反对华盛顿政府越来越严重的“君主化倾向”,宣称将誓死捍卫“1776年原则”。这些人组织集会、举行示威、发表演讲、送上陈情书,尖锐地批评政府和国会的现行政策。他们斥责华盛顿政府奉行的中立原则是“懦弱地讨好专制而毫无宪政可言的英国”,并表示美国应该公开站到法国一边,甚至加入对英国的战争也在所不惜。
这些抨击有些是正确的,比如对汉密尔顿过激的经济政策。但另一些,比如对政府中立的嘲笑以及其不惜开战的态度,却分明是无知且无畏者那种建立在愚蠢基础上的狂妄。就如同底比斯诗人平德尔说的那样——对那些未经历过战争的人而言,战争是甜蜜的。这些无知的人,这些多半在1780年以后才成年的“愤怒而血性的青年”,是根本不会了解贸然加入到欧洲战乱中为激进的法国革命政府火中取栗,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政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虽然如大卫·布朗(David Brown)这样的极品倒霉蛋屈指可数,但是一场政治沙龙与政客之间的口水战是免不了的。民众有嘴,政府有报纸。
大卫·布朗案件
这是美国建立初期的一个著名案件,其揭示的内容足以令这个国家以后的所有执法者有所警惕。
大卫·布朗是某一类美洲居民的典型代表。他于18世纪20年代末在康涅狄格的伯利恒出生,独立战争时期曾在大陆军团服役。战后,他和许多不甘寂寞的美国老兵一样,在跨洋的商船上谋了一份差事,并借此周游了世界。他到过至少19个欧洲国家,并在回到北美之后游历了全国。其间,他一直靠在各地打短工谋生。
1789年,已经年过半百的布朗抵达了马萨诸塞州的戴德姆。起初当地居民并不怎么注意这个小老头,但是其丰富的阅历和多彩的游历故事使他逐渐成为当地的知名人物。而他个人的经历也使他相信,建立政府是富人剥削农民、工匠以及其他劳动者的阴谋。他的这种观点顺应了当时马萨诸塞州的普遍观点,迅速在当地民众中传播开来。
布朗极度厌恶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令他如意,众所周知,合众国宪法最后还是在马萨诸塞州得到了通过。这不由得使布朗怒火中烧。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这个独立战争的老兵还是做出了他毫无根据满嘴跑火车式的指控——他指责政府领导人将西部内陆富饶的荒地据为己有。“500万人中,只有500人享受着税收的收益,不管社会上其他人贫困潦倒、衣食无着。”他的这些指控被有心者收集了起来,编写进了众多的宣传册子里广为传播。
在1790年前后那场沸沸扬扬的政治风波中,布朗对于新政府夸大到不切实际的抨击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当时的美国人民本能地喜好把政府以及一切能找到的权威象征套上恶意的理解。所以尽管布朗的指控如此荒唐,然而在当时确实很有市场。至少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僚们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去召开集会撰写文章,为这所谓的“万分之一的特权”作了诸多澄清。所以布朗会被当局记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1789年的12月初,布朗大叔终于察觉到他要倒霉了,因为波士顿的报纸正在将他称为“混乱和起义的源头”。在次年年初,波士顿的联邦公诉人(现在的检察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签发了逮捕他的命令。大卫·布朗跑了,他以打短工为生,并在此期间周游了合众国当时全部的13个州。不过他注定无法永久躲下去,当《镇压叛乱法》在北方公布执行的时候,告密者将他卖给了执法部门,于是联邦的捕快抓住了流窜数年的布朗。检察官对他作出了恶意诽谤政府、援助叛军等指控。对于这种涉嫌叛国和通敌的罪人,法官定出了高达400美元的保释金,这在当时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劳动者10年的积蓄。布朗当然无力支付这笔钱,那么等待他的唯有牢狱之灾。
老愤青大卫·布朗就这样在监狱内度过了一段时光,直到布朗等来了法官塞缪尔·蔡司(Samuel Chase)主持的联邦巡回法院,而他即将迎来判决。一般意义上,法官是用来作出公正裁决的职业,但是蔡司的所作所为显然背离了他的职业操守。这位法官深信,批评国家的行政部门无疑是与这个共和国为敌,所以他要杀鸡儆猴。而此时的布朗已经被关了很久,极度渴望自由和宽恕,所以他对于联邦检举人的指控供认不讳,以求得谅解和宽大。但是他的坦白对于蔡司法官是无济于事的,而且这位法官非但想惩处他这个叛徒,还想挖出其他的“同党”。塞缪尔·蔡司法官要求布朗供出他的“同谋”和他那些小册子的订户名单,但是这遭到了布朗的拒绝,“那将使我失去所有的朋友”。
布朗的下场是被判处480美元罚款和18个月的监禁,而这笔巨额罚款是这个游民根本不可能付得起的。在这个带有明显“杀一儆百”味道的判决内,蔡司指控布朗“扰乱秩序……散布谎言,危险地试图煽动社会上的无知群体”。所以,法官大人据此认为,不应该允许公民如此激烈地评论公共事务。也许法官的指控是正确的,严格地说布朗确实犯下了上述所有错误,但其行为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还算不上是“罪行”的程度。而有关“试图煽动社会上的无知群体”之说,他又何尝不是“无知群体”的一员呢?如此动用联邦的暴力机关来惩处一个信口雌黄的人,未免小题大做并有失公允。
布朗就这样悲惨地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几乎没有探监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主审的法官或者联邦公诉人是不是还在检举布朗的“同党”。
直到联邦党人在1800年的大选中失败,杰斐逊代表的共和自由派上台,这个可怜的说错话的小老头才重获自由。
华盛顿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经济专家费希尔·埃姆斯第一个按捺不住。他朝着那些社团分子们猛喷道:“(你们这些)暴乱的温床将使美国陷入混乱,就如同雅各宾派在法国的所作所为那样!”作为一位受过系统教育且具备良好自制力的绅士,他的恶语到此为止。但对于抨击华盛顿政府的“君主制倾向”言论,埃姆斯仍旧忍不住要多说几句。对究竟支持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以一番生动的描述作为非正面回答:“君主制像一艘造型优美的小船,它航行顺利,直到某个昏庸的船长使之触礁为止;而民主制则像一个木筏,它永不沉没,但糟糕的是,你的脚总是湿的。”另一位已经很难查到确切姓名的联邦党人便没有埃姆斯那么好的修养了。他充满恶意地评论当时闹得最凶的社团“肯塔基民主协会”(Kentuckys Democratic Sociey):
“(那里)啸聚着数量可怕的叛国者,其中包含众多可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制造可憎的混乱,喧嚷着好斗的噪音,是座像地狱一样的叛乱者的学堂,反对所有正常秩序和平衡的权力机构!”
基于对英语的常识,我们仅仅从其形容词数量的多寡,便能知晓其中包含的恶意。
这场政治风波愈演愈烈,然而在它即将爆发的时候却因为一场意外天灾而偃旗息鼓。
1793年夏天,酷暑袭击了当时形势最严峻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威士忌酒暴动的故乡。热风夹带着酷暑之气席卷那里的农田,草木枯竭、河泉干涸。8月初至10月下旬,黄热病侵袭了那里的城镇,大群蚊子传播着致命的黄热病。疫情无法控制,大批繁殖的蚊子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不论是民众社团还是联邦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