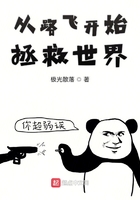吴王锦瓯从树荫后走了出来,一种仿佛是将黑夜中的凝重色彩又再加深几分沉重的窒息感,就好象名器锋刃上凝结的一种阴沉,自她的身后覆盖了上来。
“只是觉得皇姐好兴致,身体不适还能在此欣赏夜景。不知父女亲情叙得如何啊?”
“亲情?我也以为自己不再天真,也许我们都是这种越是得不到,就越是想要的性格吧。”
夜宴淡淡地应着,然后拧着眉毛,肩头微微抖动着轻轻笑起来。
“那现在我和皇姐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伤心人应当互相同情才对。”
冰冷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隐藏的烈焰,锦瓯的眼睛凝视着她单薄的背影,一瞬不瞬。
“伤心人?在你身上可丝毫没有体现啊。”
夜宴依旧没有转过身,只是垂下头嘲讽着。风轻轻地荡漾着,被雨打得零散的花瓣微微地吹动,潮湿的空气中,带着某种香甜的味道。有一阵风轻轻吹强些,那柔弱得美丽的花瓣就撒到了地面上,像是初冬的雪飘落在地面。
“哈哈哈,伤心,伤心,伤的就是心,又怎么能从外表看得出来?就像刚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高贵的皇姐会对一个小小的探花动了真情啊。”
他在黑暗里大笑,不羁而又放肆,绯色官袍上添金绣的蟒纹图案,在夜色中翻飞着狰狞。
“王弟今晚的话,好象特别的多。”拧了下纤细的眉毛,轻轻伸手接过飞起的一片花瓣,缓慢抚摩着柔软的瓣面,让有些混沌的思绪渐渐变得清晰。
“皇姐,我只是想找一个盟友,能帮我达成目的的盟友,如此而已。”
惊异于夜宴被说破心事的波澜不惊,他眯细了眼睛,说出自己的目的。
锦瓯看着她的白晰手指,在夜色中有一种奇异的剔透光泽,反而是满天的星光有些黯然失色,这一瞬间他被蛊惑得怦然心动。
“哦?不知王弟想怎样个结盟法?”
她说着却一愣,一件还带着人体温度的披风覆盖上了她的身体,修长而白晰的手指顺势在她的腰畔合拢搂住了她的身体,他的呼吸在她的耳边徘徊。
“皇姐,他要死了,这个消息不管是不是真的,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呵呵,你等不到他死的那一刻了吗?这么多年你都忍了,这几天你都忍不了?”
僵直的身体随即放松依靠在他的怀中,她微微地笑了起来,黑色的眼睛因为即将到来的宫廷阴谋而沉静得没有一点光泽。
“他最喜欢的儿子福王锦渊就要回来了,还有难道皇姐就不想,看看他在临死前被自己最讨厌的儿女夺走一切时的表情,那将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扣住她腰间的手不自觉地扭曲着,那耳畔的呼吸也越来越挚热喷吐在她纤细的颈项上。憎恨得近乎哀伤的感情从锦瓯身上蔓延而来,随着那呼吸在夜宴的身上荡漾开来,无法形容的哀伤奠定了将一切都摧毁的决心,她知道这个古老的皇朝又将迎接一场血变。
不知道过了多久,夜宴才缓缓开口:“那么,黎国未来的君王,我要你对夜氏还有对我许下一个承诺。”
“苍天可鉴,大地为证。锦瓯有生之年都将会保证夜氏的平安,我这一生一世都会守护皇姐,如违此誓,不得善终。”
夜宴猛地被转了过来,星光闪烁下她看见他狠狠咬破了自己的唇角,然后吻密密实实地压了上来,血腥的味道从唇齿交缠中蔓延进了她的口腔。
使劲推开他,反手一个耳光落在了他的面上。
看着锦瓯线条优美的下颌上滑下了鲜血的痕迹,而夜宴苍白的嘴唇上也有了鲜艳的血色。她有些气息不稳地微喘着,唇上有着滚烫的热度,可是一种自体内深处泛滥而上的寒冷却让她几乎无法呼吸。
“我们的血已经混在彼此的血中,这样的承诺你可放心了吧。”没有理会挨打的面颊,他伸出舌添掉唇边的血迹,然后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我希望你知道,锦瓯。我可以喜欢你,因为你是我的弟弟,我决无可能爱你,亦因为你是我的弟弟。”
她放下手,抬起冰冷的没有温度的眼睛看他,声音也同样的没有任何温度。
“这个皇宫里,只有你是喜欢我的。”他在这么说的时候微微垂着头,因为刚刚那记耳光,几丝乱发从额头上垂落下来,为美丽的容颜投下带着阴冷味道的暗影:“不用担心什么,这个吻只是个誓言的见证而已,皇姐。”
紧紧地盯着他,许久夜宴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然后她转身迈步。
锦瓯凝视着她款款离去的身影,一股奇妙的感觉忽然在他的心中沸腾了起来,他想立刻冲上去,把她抱在他的怀中,再不松开。是的,他爱自己的姐姐,不是以弟弟爱姐姐的情感,而是以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心情。现在,这也许是一份不敢让别人发现,不敢说出口表白,甚至于不敢让第二人知道的感情。可是没有关系,他可以等,总有一天这天下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可以等……
深夜,旒芙宫烛火已经燃得殆尽,窗外风声低啸,吹得窗棂沙沙有声。
“何冬,九妹身边的侍女或者是近侍有没有能熟络一下的。”
夜宴站在窗前,风吹得衣袖飘然,那声音低得近似呢喃。
“老奴这就去办。”何冬恭顺地倾身。
“越快越好,本宫想知道她最近一切行踪,还有父皇身边也要密切留意。”
“是。”
庭院中盛开的芙蓉树,已经展开了翠绿的枝叶,状如华盖的枝条婀娜舒展。芙蓉花在夏日炎炎时,才会初绽,毛绒绒的粉生生的,仿佛刚落下一场粉色的鹅毛雪,站在树下,惟觉芬芳馥郁得悠然神往。
可是旒芙宫的芙蓉花却开得火红,据说要此花开得越是红艳,就越需要人的血肉来滋养,所以这满园的芙蓉树下也不知道埋了多少的冤魂。
夜宴看着窗外在夜风中摇曳的芙蓉树,像是在看自己的影子,细长的眼中闪动着温柔得近似哀怜的情感。
锦璎我的妹妹,请不要怨我。爱情本来就是一场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从小,你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而现在的自己除了用伤害和占有来保卫自己的一切,已经再无他法。
许久,她终是疲倦地闭上眼睛,唇角向上微微挑起轻笑出声,把所有的情绪流动都隐藏在了眼皮之下。
连续几日的大雨终于停了下来,整个镜安经历了雨水的滋润后,万物都在阳光里舒展开了身体,仿佛连续狂暴的大雨根本没有发生过一般。夜宴看望了夜玑端后,坐在稳步行走的马车中行往宫中,她依旧能感觉到空气中带着特有的清澈感觉,呼吸之间草香气息的空气流入了她的身体里。
轻微颠簸的马车,让她闭起了双眼,刚刚在清平公府的谈话又跃然脑中。
“前儿我进宫,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谢流岚的婚事,条件是我支持福王锦渊继位,并且铲除掉吴王锦瓯,还有在他登基后我必须自尽。”
水般柔滑的声音温柔地响起,纯粹就事论事的口吻却带起冷酷的涟漪,在有些昏黄的房间里面荡漾,仿佛说的是他人的生死。
回到镜安后,夜玑端一直在发烧,断断续续的高烧让他产生了畏惧阳光的毛病,屋内的窗被蝉翼纱蒙上,在有些刺鼻的汤药味道中安息香的袅袅轻烟在空气里迷漫。
当夜宴走进他卧室的时候,夜玑端倚在榻上,身上依旧盖着锦被,那长长的发像枯草披在愈见单薄的肩上。
“舅父,请放心,锦瓯对我发过誓,他登基后会保夜氏和您的平安。”
“当然,没有夜氏他拿什么登基,他现在的情况比他老子当年强不了多少,如果你是男儿……唉不说了。”
夜玑端刻薄地扭曲了嘴唇,笑意以冷酷的弧度勾勒出。可当他看见夜宴抽紧的尖尖的下颌和有些苍白的脸色的时候,一种难以形容的负罪感让他选择了沉默。
“舅父,婚礼定在什么时候。”
听着夜玑端蕴涵了深重危险的话语,她只是侧头,调整了一下面部的表情,保持淡然地说道。
“一个月后,再迟,锦渊就会回来了。”
“舅父,父皇他那么轻易就相信你了,不会有什么问题?”
“呵呵,相不相信也没有什么,我们都在拖时间而已,看谁先能把谁铲除了,他以为我手上没有了兵权,便等于老虎没有了牙齿,殊不知他的好儿子已经和御林军统领勾结在了一起,到时候怕他落得和先皇一样的下场了。”
冷笑着说完,夜玑端手轻轻地放在她的手上,苍白手指上的翠绿扳指儿幽幽地闪光,冰凉得让她忍不住一阵轻微的颤抖。而他的眼睛似乎忽然变得更深更沉,幽幽深不见底。
“夜宴,他是你选择的人,无论如何舅父都希望你幸福。”
突然,马车停了下来,打断了她的思绪。
“出了什么事?”
“启禀公主,前边似乎是北狄的殷王,和新科探花起了争执,把路堵住了。”
侍卫有些犹疑的声音响了起来,这条朱雀大街两旁既无府邸亦无商铺专为王公贵戚通行便捷而设,一品以下的官员来此就是触犯黎国律法,不知道探花郎怎么会在此出现。
夜宴心中一惊,把珠帘挑起往前看去,明亮的光线一下子钻进了车内。
不远处,谢流岚似乎正被悱熔的手下抓住捆绑了起来。
夜宴心中一声叹息。悱熔正在用让情敌直接消失,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以他北狄现在的国势,已经敢当众放言迎娶公主,那么运用一个小小的阴谋让谢流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人粗暴地把谢流岚按倒在地,拳脚交加下,鲜血喷薄而。一旁殷王悱熔却露出了雪白得仿佛是狼的獠牙一样的牙齿微笑着,满意地看着鲜血四溅。
她闭上了眼睛,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刺进了心肺,车厢里似乎有什么喀哒的响了一声,低头看去,原来一只染了凤仙的指甲折断在了掌心。
“去请殷王住手,然后告诉他谢大人是本宫约他在此的。”犹疑了一下,夜宴继续说道“还有就说本宫听说,城北五里有一所白云寺,寺中姻缘树据说极为灵验,三日后便是吉时,到时可保佑他心想事成。”
侍卫听命走道了殷王身旁,在他的耳畔低低回禀着,不一会悱熔那双没有任何感情波动的眼睛转向她的马车,然后露出了只有他们彼此知道深意的冷笑。
片刻之后,侍卫便搀扶着谢流岚,上了夜宴的马车。
“多谢长公主搭救,下官不胜感激。”
放下了帘幕之后,诺大的空间似乎因为他的进入而狭小了许多,谢流岚安静地靠在软椅里,青色的官袍上全都是泥土,还溅得有暗红色的点点印记。而他似乎并没有因为满身的瘀伤血迹和零乱而感到狼狈,那修长的手指依旧平静地整理着衣衫。
夜宴缓慢地摇动着手中的苏绣团扇,一双墨色的瞳孔没有任何感情地看着对面的男子。
“大人客气了,如不嫌弃,本宫送你回府吧。”
“多谢公主。”
看着那对凝视着自己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睛,他忽然觉得有一种面对强敌的战栗,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对一个女人产生了这种感觉。
夜宴也看着谢流岚那双沉静的眼,他的官帽已不知被打落在何处,几缕掉落的发却被汗水粘湿在额头上。看着他的发际滴落大颗的汗水,和抠因为痛楚而用力扭曲的手指,此刻她的胸口中有着无法抑制的疼痛。
鲜血自唇角渐渐滑落,在他的面上留下了一条鲜红的痕迹,忍不住微微蹙起眉,粉色的缠枝宝相花袖下纤细白晰的手指握着丝帕,伸了出去,可是他却下意识似地往后躲闪。
“你不用怕,你面上有血迹。”
“不敢劳驾公主。”
无力地将身体依靠在身后的软垫上,他用自己袍袖往面上胡乱擦拭着,声音与眼神却是完全不曾改变的坚定。
曾几何时,他曾经对她许诺终生,可此时此刻他却只是焦急地躲避着她。一时间她心头是空荡荡的,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觉得难受。
夜宴带着难以言喻的挫败感侧过头望向窗外,外面透进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黑色宝石一样的眼睛在这样的强光下却并不黯淡,可只有自己知道心头火燃得近乎爆烈。
谢流岚这时方才敢看着她,那眼神,如此的复杂,一种类似回忆的神态从眼底流露了出来,疲惫的样子却是更加的明显。
终于马车停了下来,谢流岚毫不犹豫掀帘走了下去,站稳后才对豪华马车内的她,躬身行了一礼。
“多谢公主搭救和相送之恩。”
“谢大人不用客气。”夜宴有些清冷的声音从帘后传了出来,看着在明媚的阳光下,他可以隐隐的看到她的安静而优雅的身姿。
“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父皇的旨意明日就会下来,一个月后我们就是夫妻了。”
夜宴拉开了侧面的帘子,看着本就狼狈的谢流岚面色瞬间变得更加雪白,她的心中流淌起了奇妙的感觉,欢喜,忧愁,悲伤还是无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
察觉到她的视线,谢流岚微微地抬起了头,当他们的眼睛对上的时候,他看着她,想说什么,但是夜宴的手一抖,帘子放了下来,隔断了他们。
然后感觉车缓缓动了,调转了方向,往皇宫走去。
一日后,黎帝下旨,把长公主夜宴下嫁新科探花谢流岚。
就在他们筹备婚礼的时候,黎国的皇宫已由一桩丑闻而拉开了争端的序幕。
九公主锦璎私自偷溜出宫,前往白云寺和北狄殷王偷情被发现,黎帝凝舒一气之下吐血晕倒,太医诊治之后,皇帝身体欠安这样的事实终于诏告天下,太医很含蓄地暗示众人,皇帝已经时日无多。
黎帝所居的乾涁宫中本极是敞亮,多宝格的窗敞开着,檐下碧树花影,风吹拂动,夹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幽香飘荡在空中。
他们一干人坐在外殿等候着,殿内的花架上摆放着照顾的花朵长的欣欣向荣的蔷薇,那丝绸一般的柔软花瓣像是舞女身上的轻衣舒展着,在金黄色的阳光之下摇曳着优雅的香气。可是不知为何夜宴却好似闻到了混合着那腐朽的气息,在空气中飘散着,她微微拧起了纤细的眉毛。
正在众人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何明绨从内殿走了出来。
“殷王爷,皇上传诏您进去。”
悱熔不出所料的从椅上站起,一旁的余德妃却先他一步开口:
“何明绨,本宫要先见皇上,你去通报一下。”
“回娘娘,皇上说了他今天身体不舒服,谁也不见了,还请各位早些回去吧。”
余德妃的面色一变,张了张口终是没有说什么。
玉贵妃的脸色也是近乎苍白,福王锦渊远在北疆,最快也要两个月才能赶回,而黎帝已经不知道能不能支撑到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