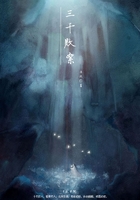大量的不识字的农民和有限的几个略懂签名算账的乡土小知识分子,确实不足以再造社会秩序。所以,绵延十八年之久的捻军和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捻党,一直以“填饱肚子”为最高奋斗目标。故而,其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分量,也轻若鸿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的重大缺陷。
我们关注那些“伟大的历史转折”,关注“开辟了新纪元”,关注“斗争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此种种。但我们极少关注那些永恒的历史命题:民众的肚子需要填饱,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始终缺失。
所以,教科书习惯于提供这样一种近代史线索: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清末宪政→辛亥革命→……
还有那些程序化的表述:“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另一个更真实的近代中国,在这种宏大的描述中,有意无意地被遮蔽和消解了。
程序化表述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劳苦大众,被庙堂抛弃,不得不为了获取一点点生存保障而把自己投入‘江湖’的滚滚洪流当中……”
这个“江湖”,包括了捻党,也包括了捻党之前的天地会、白莲教;还包括了捻党之后的哥老会、义和团、洪门、袍哥、青帮、白枪会、红枪会……甚至于一贯道。
这些林林总总的江湖帮会,历史早已给了它们各式各样的定评。天地会和白莲教被贴上了“反清复明”的标签;哥老会和袍哥们身上既有辛亥革命的荣光,也有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的劣迹;义和团带着蒙昧推动了一场盲目排外运动而被西方惊为“黄祸”;洪门一直要求他们的“大哥”孙中山给予自己一个合法的政党身份;根据地里的白枪会和红枪会在国共两党与日军之间艰难地辗转腾挪;一贯道则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组织”。
但是,历史忽略了这些:
天地会初期真正的宗旨其实是“互相扶持,彼此周济”,它的成员和首领人物为水陆通道上和城镇的下层劳动群众、三教九流、无业游民以及农民,这些人对“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并不感兴趣。据统计,1796—1850年的五十五年间,涉及天地会的事件共有九十六宗,其中为了“遇事有人帮助,免人欺凌”者二十六起,因穷困而“敛财分用”者十五起,为抢劫富户而“得财分用”者三十九起;攻掠城镇“竖旗起事”者仅仅十一起。说到底,仍然是无保障流民们“填饱肚子”的问题。
而在喊出“灭洋”口号之前,义和团和它那些千奇百怪的“前身”,譬如梅花拳、大刀会等,已经在华北平原活跃了近半个世纪,当地乡绅和小土地主把它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在政府失职的情形下抵抗土匪,保护村庄和家族。
一贯道的壮大同样缘自庙堂的社会保障在华北的多年缺失——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华北成为沦陷区之后,历届日伪政权均无意关注民生,而孜孜以为日军搜刮军备物资为主业;其后国共内战,华北再遭兵灾,一贯道趁机壮大。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的话说,一贯道已经成了北平的“第一大党”。1950年底,北京海淀地区一贯道徒有两万多名——那年全区只有十四点三万人。华北另一重镇天津,解放前夕有道徒二十余万人。一些农村地区,一贯道徒占人口的比重更加惊人,河北隆化县解放前有一贯道徒五点三万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山西省天镇县在1950年有一贯道徒三点三万名,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河北省宣化县有一贯道徒三点六万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为成年男性。据1951年初绥远省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一贯道人员估计在三十万以上,约占全省人口的11%。个别地区问题更加严重,如兴和县加入一贯道者占全县人口的14%强。一贯道不仅人数多,并且渗透进了新政权的基层组织。山西省代县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千名党员中,有18%参加了一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