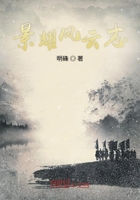臧语臻并没有明确答复汪澜是否还会每天过来。汪澜本来是不抱希望的,第二天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不料临近中午的时候,臧语臻却不期而至。汪澜慌乱的爬起来洗漱,臧语臻故意跟她开玩笑说:“还说不减肥呢,都快中午了,你怕是早饭还没吃的吧?”
汪澜羞涩一笑,说:“这几天都是您做饭,今天就尝尝我的手艺吧。”
臧语臻饶有兴味地说:“哈,真的呀,那今天我可有口福咯!”
汪澜忸怩说:“我可不会什么大餐,只会做青菜肉丝面。”
臧语臻说:“家常饭能做出自己的味道就好,你不许反悔哈,我可是迫不及待的想先尝为快哪!”
臧语臻曾尝试让汪澜联络同学一起报团出游,汪澜拒绝了,理由是不想再浪费他的money,其实内心里,是她渴望能尽可能多的和他呆在一起,看书,聊天,甚至以前一无所知的京戏,因为臧语臻的喜欢,她也会和他一起整场整场的看下去。
臧语臻喜欢泡上一壶茶,就着茶香,听着京戏,寻常生活,便多了余韵悠长的味道。汪澜跟着臧语臻一起看京戏,惊异于唱词的精致典雅。两人大多时候是静静欣赏,偶尔臧语臻会给她介绍一些京戏里相关的诗词或历史典故。慢慢地,汪澜也会由京戏联想到熟悉的诗词掌故。
有一回,看京戏《春闺梦》,汪澜问:“这个是不取自陈陶的《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臧语臻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汪澜接着看下去,剧情很简单,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将士们已然战死沙场,森森白骨堆积在无定河边,而深闺中的妻子,则相信丈夫还活着,仍在闺中切切盼望夫君归来。因有所思,故而成梦,在妻子甜蜜的闺梦里,为丈夫的心有灵犀,突然还家,久别重逢,不尽缱绻,无限温存:“愿此生常相守怜我怜卿”。无定河边,森然白骨谁个收?春闺梦里,温柔香衾有良人,却不知白骨红颜,天人两隔。
汪澜看着看着,不禁潸然下泪。
暑假里有一周时间,臧语臻参加教委组织的一个培训班,白天不能过来,汪澜觉得每时每分都仿佛被一再的拉长,再拉长。幸好一高家属院对面就是文化广场,市图书馆就坐落在广场北侧,臧语臻不来的时候,她就去图书馆里看书,常常看着看着,书上的文字模糊起来,一个面庞在书页上倒是越来越清晰。
和汪澜相反,臧语臻好像刻意把两人的关系限定在某种他内心认定的距离。他会每天过来陪她,陪她度过高考后难熬的等待时间,但是又避免和她过于靠近。
高考录取通知书终于下来了,汪澜如愿以偿被上海的F大学录取,臧语臻兴高采烈要她一起出去吃大餐庆祝。汪澜轻轻摇了摇头,臧语臻兴致不减地说;“你等着,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臧语臻出去的时间似乎长了点,他回来时候,汪澜有点坐立不安,接过他手里大大小小的食品盒放在餐桌上,却忘了打开。
吃过晚饭,两个人在书房又闲聊了会儿,天已很晚了,臧语臻和往常一样要离开,汪澜阻止了他,他复坐下,两人一时都没了话,静静听着楼下家属院孩子们的笑闹声越来越远,直至归于平静。
书房里的空气似乎有些凝滞,臧语臻首先打破了平静,说:“你不跟家里说一声吗?”汪澜半天没做声,臧语臻缓了一下,解释道:“你知道,我不是要你走。但是,跟家人说一声也是必要的。你看?”
汪澜依旧没回答,深深埋着头,双手掩面,许久,臧语臻才听到她隐忍的啜泣,他一瞬有些心慌,站了起来,局促道:“汪澜——”
汪澜抬起了头,脸上泪水四溢,含混说:“我不要离开!”
臧语臻温和地说:“只要你愿意,可以一直住这儿。”
汪澜擦擦眼泪,顿了一下,清晰地说:“我要和你一起,永远!”
臧语臻愣住,清癯的面颊上泛起红潮。他窘迫的样子可爱极了,汪澜忽地起身,孩子气地冲到他面前。臧语臻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她掂起脚尖,鼻尖一下撞上了他的鼻尖,她不由“呀”了一声,臧语臻反应过来她是想亲吻他,却不得法,心里忽然溢满了温柔的疼痛,他扶住她的肩,微微侧首,轻轻吮住她柔软的唇,汪澜有一瞬眩晕,双手不由环紧了他的腰。
稍倾,臧语臻温柔而坚决推开了她的肩膀,“不——”
汪澜抬起婆娑的泪眼,望着他,目光里有着深深受伤的绝望。
臧语臻的手滑落下来,轻柔而坚决地说:“不行,我们——”
汪澜转过了脸,臧语臻看不到她的表情,再次被弃如敝履的感觉整个的攫住了她,她咬紧嘴唇,默默退后两步站着。臧语臻看到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拉过一张椅子放在她身后,试图扶她坐下,她倔强地挣开了他,颤抖得仿佛飓风中的小舟。
臧语臻两手轻轻扶住她的肩,叹息似的叫着她的名字:“汪澜。”
这一夜,臧语臻破例留了下来,没走。
接下来的日子,汪澜每天都像生活在云端里。臧语臻的心里眼里,只一个她,宠溺的爱着。以前看到早恋中男女同学的亲密举动,她很不以为然。现在无时无刻和臧语臻守在一起,她却仍然觉得不够,偶尔臧语臻出去采买生活用品,她都感觉一刻仿佛一年那样长。
汪澜最爱听臧语臻的如珠妙语,因了她的存在,臧语臻文思泉涌,即使日常生活情景,从他口中说来也大有意趣。
汪澜少女幻想中的种种场景,似乎都在臧语臻身上一一得到了应验。
因为宅在家里的缘故,臧语臻不再中规中矩的着装,常穿着宽大的白色圆领衫晃来晃去。历经岁月磨砺,他依旧保留着阅读写作以及笔走龙蛇的习惯,他说着略带本地口音的普通话,会在愉悦的时候即兴吟一两句诗词,或者哼几句地道醇厚的京戏。
有时候来了兴致,臧语臻会铺好一张宣纸,和汪澜两人一递一行写大字,臧语臻很惊异于她一手端正的楷书,和他的狂草相映成趣。
汪澜被母亲逼迫苦练多年书法,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书写的快乐。她喜欢和臧语臻一起共读,看到愉悦处也会出声朗诵,常常引来他的击节赞叹。
臧语臻藏书甚丰,有天汪澜抽出本林语堂的《红牡丹》,他却阻止了她打开书本的举动,说:“不要教坏了我的宝呀!”
汪澜一抬下巴骄傲地说:“早看过了我!”
臧语臻把手按在书上,饶有兴味地问:“你喜欢书中哪个人物呢?”
引得汪澜孩子气也上来了,说:“就不告诉你,咱们都写下来,看一样不?”
于是两人各自在纸上写下,拿在一处看,都是“若水”二字。
臧语臻问她是怎么喜欢上若水的,汪澜说:“看到他出场就喜欢了!若水出场时候,瘦高白净,穿一件宽大的袍,脖子上不扣纽扣儿,松垂着像个口袋——这样穿法够有多舒服!”
汪澜自顾说着,就见臧语臻抻抻衣衫,摸摸脸颊,故意拉长了声音说:“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像说某人的呢?”
汪澜不禁笑倒在他怀里:“坏人,你怎么?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啊!”
汪澜边笑边在臧语臻怀里钻来钻去,却感觉臧语臻拱起身子刻意的和她的身体保持着距离。汪澜不解问:“你干嘛?还自比若水呢,有你这样煞风景的推人家的若水么?”
既然被她看破,臧语臻也不再遮掩,更加明确地推开了她:“傻丫头,不知道是为你好!”
汪澜哼一声,不屑地甩了下手,却感觉自己的手碰到了臧语臻身体的某处凸起,她看着臧语臻瞬间变成通红的脸,懵懵懂懂知道了他说是为她好的确切含义。
被汪澜盯着看的臧语臻不自然地转身,背对着她,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汪澜从后面抱住了他,把脸贴在他背上来回摩挲着,臧语臻试图挣脱她:“好澜澜,别闹了,我出去买好吃的给你。”
汪澜呢喃说:“我知道,你是不是很辛苦?”
臧语臻顾左右而言他:“买东西,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汪澜心疼说:“现在晚上10点好不好,买东西吃,你找理由也不是这么找的。”她转到他面前,再次抱住他:“我不想你忍得这么辛苦!”
臧语臻把下巴搁在她肩膀上,深深叹了口气,抬手揉了揉她的头发,缓缓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没什么辛苦的。”
从前妻红杏出墙到现在,臧语臻已经两年多不近女色,特别是和前妻那一晚不成功的经历,使他一度以为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某种障碍。和汪澜在一起之后,她无心的亲昵举动常常勾起他身体的强烈反应,他只能拼命压抑自己,她那么年轻美好的一个人儿,他真的不忍心亵渎了她。
汪澜的脸贴在他胸口摩挲着,感受着他狂乱的心跳,闭了眼睛慢慢说:“可是我想做牡丹那样的事情,既然早晚要发生——”
臧语臻抱紧了她:“傻澜澜,你知道那样意味着什么吗?”
汪澜脸红的发烫,依旧不敢睁开眼睛,她怕自己会瞬间失去了勇气:“我准备好了,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