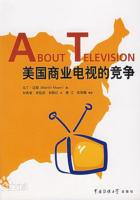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民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论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得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占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的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图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涂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厂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二角塔。那金字塔(据最近《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六号,页一四七)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日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者的口标:
为学要如金字塔,
要能厂大要能高。
【点评】
胡适强调,要根据自己的性情和爱好读书。读书求知,原为更好地做人。但今人读书重功利性,无视人文修养,读书就像吃快餐,饱腹而已,所以没有营养,难以发展真正的兴趣,难有真正的事业。
读书要精而博。读书要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读书精,就会读出精华;读书要博,可开阔视野和思维,增广见识,长智慧,厚修养,成就通才。说明读书既要专心致志,又要博览群书,做到高、大、尖,如金字塔。
胡适本人自小就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不只读“正书”,还读“杂书”。比如,他少年时就喜欢读四大名著等半文言或白话小说,使他很早就意识到提倡白话文的重要性。他学贯中西,所以能对中西文化做对比研究,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端,看到西方科学和民主以及科技的优势,所以他能在思想和学术两个领域做出开拓性的贡献。
看似无用的兴趣阅读,其实最关系着一个人的志趣和思想,让人终生受益。真正的事业,都是自己兴趣的链接。只是,现代人急功近利,还有多少兴趣阅读?生存压力大过从前,有多少闲暇顾及兴趣阅读?
【链接】
“杂读”成就胡适
胡适三岁开始读书,除了学堂里的书,他还读了大量“课外书”,这些课外书适合胡适的真性情,培养了胡适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十一岁能看懂古文时,先生就让他读《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易知录》还好,因为有标点,读起来不觉吃力。但《通鉴辑览》没标点,需要用红笔点读,所以胡适读得慢而吃力。二哥发现后,就让他改读相对容易的《资治通鉴》,让他自己点读,胡适很快喜欢上了历史书。
在读书的过程中,胡适发现朝代帝王年号最难记,一日突发奇想:我何不自己编辑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呢?让那些难记的更好记!想到就做,他还真的编了七字句的歌诀!这直接培养了胡适对传统国学的研究兴趣。胡适自己曾说,这是他最早的“整理国故”。
读《资治通鉴》,丰富了胡适的知识,提高了阅读能力,开阔了思路,不再迷信鬼神,变得大胆,日后更加理性,追求科学,相信个人的积极探索之力,最终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在上海求学时,胡适接触到“新学”。邹容的《革命军》,梁启超的书,让少年胡适心潮澎湃,豪情万丈,甚至还与同学一道当“愤青”,联名写信痛斥上海道台袁海观,愤而退学。这时,少年胡适思想激进,已自命“新人物”了。在澄衷学堂,胡适刻苦学习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科目,在这所有名的新式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如鱼得水,各方面得到长足发展,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胡适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喜欢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于是把自己名字改为“胡适之”。胡适还喜欢读梁启超的书。读他的《新民说》,为改造“老大国民如病夫”的观点热血沸腾,思绪跟着梁氏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随之流泪,随之振作。而梁氏的《论毅力》,更让少年胡适深受鼓舞。胡适自己曾说:“我在二十五年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
《新民说》让胡适思想大开,让他看到中国之外,还有更多的民族和更先进的文化。
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让胡适眼前一亮,感觉“学术思想”的有趣,心中有了“学术史”这个概念。但当胡适由佩服到发现梁氏的缺点时,胡适就产生了自己写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野心”。这个念头让他力量倍增。胡适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作《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从此,他留心读朱子《近思录》,阅读宋明理学,进一步读梁启超的《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和《正义堂丛书》等。胡适信心百倍,还发起成立“自治会”,他带头演讲《论性》,批驳孟子的性善说,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只承认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可善可恶”。当时,胡适还读了英文版《格致读本》,接触到浅近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从此萌生。
就是在这种广泛的“杂读”中,胡适培养了自由科学的思想,培养了大胆质疑的精神,最终创造了开拓性事业,并成就学术上的一家之言。
5.查字典的好处——谈字典的功用
【题解】
本文写于1925年4月25日夜,又题名为《胡说》。原载于1925年5月2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21期。
《现代评论》为综合性周刊,于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1928年12月29日出至第9卷209期停刊,其间还出版3期增刊和一批“现代丛刊”。王世杰负责编辑,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高一涵、唐有壬、陈源、徐志摩等,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该刊具有较浓的自由主义色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各方面。丁西林、凌叔华、闻一多、沈从文、胡也频等作家也是在此开始崭露头角的。
在这里,胡适强调了读书“手到”的一项重要功夫——翻字典。字典是读书人的工具书。在字典的帮助下,读书效率更高,欲望更增,兴趣更广。
【原文】
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我又常对朋友说:“读书不但要眼到、口到、心到。最要紧的是手到。手到的工夫很多,第一要紧的是动手翻字典。”
我怕我的朋友和学生不记得我这句话,所以有一天我编了一支《劝善歌》:
少花几个钱,
多卖几亩田,
千万买部好字典!
它跟你到天边;
只要你常常请教它,
包管你可以少丢几次脸!
今天我偶然翻开上海《时事新报》附刊的“文学”第一百六十九期,内有王统照先生翻译的郎弗楼(Longfellow,1807-1882,今译为朗费罗,美国诗人)的《克司台凯莱的盲女》(亦作《克司苔克莱的盲女》)一篇长诗。我没有细看全文,顺手翻过来,篇末有两条小注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条注说:
此句原文为This old Te Deum,按提单姆为苏格兰的一地方名。
这真是荒谬了。Te Deum是一只最普通、最著名的《颂圣歌》,Te是你,Deum是上帝。原文第一句为Te Deum Laudamus(上帝啊,我们颂赞你),因此得篇名。这是天主教一切节日及礼拜日必用的歌,所以什么小字典里都有此字。我们正不须翻大字典,即翻商务印书馆的《英华合解辞典》(页一二三三),便有此字。这又不是什么僻字,王统照先生为什么不肯高抬贵手,翻一翻这种袖珍的字典呢?为什么他却捏造一个“苏格兰的一地方名”的谬解呢?
第二条注说:
此处原Deprofumdis系拉丁文,表悲哀及烦郁这意。
这又是荒谬了。这两个拉丁字,也是一篇诗歌之名,即是《旧约》里《诗篇》的第一百三十首,拉丁译文首二字为De Profundis,译言“从深处”,今官话译本译为“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此亦非僻典,诗人常用此题;袖珍的《英华合解辞汇》(页一四七零)也有解释。王统照先生何以看轻字典而过信他自己的“腹笥”呢?
我因此二注,但忍不住去翻翻他的译文。译文是完全不可读的。开始第四行便大错,一直到底,错误不通之处,指不胜指。我试举一个例:
当我倾听着歌声,
我想我回来的是早些时,
你知道那是在Whitsuntide那里。
你的邀请单可证明永无止息时;
我们读这几句完全不通的话,正不用看原文,便可知其大错大谬。果然,原文是:
And,as I listened to the song,
I thought my turn would come ere long,
Thou knowest it is Whitsuntide.
Thy cards forsooth can never lie.
我听这歌时,
我就想,不久就要轮着我了,
你知道我的日期是在圣灵降临节的,
你的纸牌(算命的用牌)是不会说诳的。
这四句里有多少错误?Turn并非僻字,译为“回来”,一错也。ere long是常见的习语,译为“早些时”,二错也。Whitsuntide乃是一个大节,什么小字典都可查,《英华双解辞汇》页一三七五并不难翻;今不译义,而加“那里”二字,可见译者又把此字当作“苏格兰的一地方名”了,三误也。这番话是盲女对那预言婆子说的,故说她的纸牌不会说诳。今译cards为“邀请单”,不知这位穷婆子邀请什么客?四误也。Lie更非僻字,译作“止息”,五误也。Forsooth译作“可证明”,六误也。即使老婆子发出邀请单,邀请单怎么会“证明永无止息时”呢?此七大误而一大不通也。
全篇像这样大谬的地方太多了,我再举一句作例罢:
他已来到!来到在末次!
原文是:
He has arrived!Arrived at last!
这样的句子尚不能翻译,而妄想译诗,这真是大胆妄为了!
一千八百年前有位姓王的说:
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奔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衡·对作篇》)
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但我们的朋友,负一时文誉如王统照先生者,也会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我真有点“心涌,笔手扰”了。
【点评】
勤翻字典,是读书人的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功夫。查字典可避免主观臆断,避免出丑。王统照那样的诗人还犯错误,更何况一般人呢?
不爱翻字典,是读书态度不严谨,要么懒惰,要么自以为是。尤其做学问的人,更要勤翻字典。文章千古事,一旦谬误,贻害无穷。胡适为此编了《劝善歌》,浅白晓畅,劝人多查字典。
字典看似枯燥无味,但其中有丰富的知识。善于看字典的人,里面不仅有知识,还能看出历史及文化的变迁。看字典乐趣无穷。央视一套的《汉字听写大赛》和《成语大会》节目,既是对传统汉字和成语知识的学习传承,又是对它们的弘扬和发展。在传统文化叫好不叫座的今天,是一种有良知的努力。
【链接】
新文化运动中的王统照
王统照(1897-1957),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他少年早慧,自小熟读四书五经。中学时他便尝试写了律诗、绝句、乐府歌等旧体诗词达170余首之多,后自编成《剑啸庐诗草》集。也是在此时,他就发表了章回体小说《剑花痕》,还编写了话剧《云南起义》,自饰蔡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