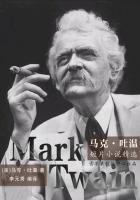你没有看见我的脸。
已经是四月末了,山坡上,梯田里,花朵都凋谢了,剩下尖锐的果实装扮成叶子,哗啦啦,倒掉的就是一大片。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你穿着短袖衬衣,在盘子里调好饱满的色彩,滴落在画布上,你不管,你一笔画过去,之前的痕迹都不见了,而新的痕迹出现了。
你退后,眯起眼睛。看,太阳出来了,花台里面新开了几朵红色的蔷薇。
你还是没有看见我的脸。
画家结婚的时候,整个家族的人都来了。乡下的老祖父,失散多年的舅舅,刚刚从广州打工回来的表妹,浩浩荡荡摆了四十二桌酒席,祖父那天很高兴,一直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喝酒,舅舅看了,说:“爸,你别喝多了。”——于是抢过了别人给祖父倒的酒,一饮而尽。祖父一言不发,眯着眼睛,拿过酒杯,把杯底剩下的几滴酒一一舔干净。新媳妇站在台子上,看见祖父的样子,“扑哧”笑出了声。
她站在台子上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伴娘就让她去换衣服了。出来的时候,新娘子穿一身酒红色的旗袍,笑语嫣然,迷倒了全场的男人。画家得意洋洋地挽着新娘一桌桌敬酒,一杯杯喝酒,有人起哄,对画家说:“快跟新娘子说个‘我爱你’给我们听!”
画家笑了,终于对新娘说:“我爱你。”
人人都看见,姑娘的眼睛,就那样红了。
画家告别老婆孩子来画室画画已经快一个星期了。天晚的时候,他画完画,儿子给他打了个电话,儿子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给我买个新玩具。”画家连声说“好”,然后妻子就夺过了话筒,她柔声问他:“创作还顺利吗?记得晚上早点睡,不要老是熬夜。”
他答应了她,毫无意识地坐在窗台上,看着蔷薇花已经开了,想着春天就被这么开尽了,听着妻子温柔的唠叨。末了,他说:“我出去吃饭了。”
画室在离城市两个小时车程的白鹭山上,出去走十五分钟就到了白鹭镇的正街。整个白鹭镇就只有这一条街,两家馆子,一家卖饭,一家卖面。面馆靠着猪肉的铺子,夜色已经有些浓了,肉铺子门口点着灯,招摇着几条很难看的猪肉。画家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走进了饭馆。
饭馆的隔壁是一家木匠的铺子,木匠是画家在白鹭镇上最熟的熟人了,几年来他长期给他制作各种画框,终于弄得像模像样。木匠有点龅牙,讲话的时候地方音更重了,但他非常热情,看见画家来吃饭,一抹脸就走了出来,问画家说:“吃饭啊?我们也还没吃,和我们一起吃吧!”
画家连连推辞,终于把木匠给推了回去。他走进馆子,点了菜,吃了起来。吃了不一会儿,木匠又跨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碗,他说:“今天我老婆做了盐煎肉,你吃吃看,我们这里的猪肉特别好吃。”
画家推辞不过,终于接受了,夹起一片肥肉放进嘴里,立刻,在唇齿间溅满了金黄的猪油。
画家吃了三碗饭,结账出门时,看见隔壁的木匠铺子里钻出来一个女人,中等身材,头发很长,显得很不寻常,穿着一条连衣裙,颜色看不清楚。她低着头,擦着画家的肩膀进了饭馆,画家听见里面在打招呼,问她说:“小唐,你来收碗吗?”
他想:原来是木匠的老婆。
画家结婚之前,和家里人大吵了一架。他父母都反对他这么早就结婚,对象又是一个家世不明的姑娘,家里面父母不在了,亲戚也没几个,无依无靠的,根本没个照应。
母亲是一个退了休的小学教师,她拍着桌子,指着儿子的鼻子,大骂:“你结什么婚啊,那家人什么底细,你什么也不知道,酒席都坐不满,就要结婚!”
父亲倒很冷静,喝一口茶,对儿子说:“你们都还年轻,是不是再想想?以后的路还很远,你们也有各自的事业要干啊……”
他女朋友坐在卧室里面,假装什么也没听见,看着床对面那一柜子的书,默默发呆。画家走进来,拉着她的手,猛然把她拉了出去,姑娘在白炽灯下抬起脸,直对着父母,脸色青白,索索的嘴唇,很是茫然的样子。
画家搂着她的肩膀,对父亲说:“你看清楚了,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娶的女人,除了这个,没有别的!”
说完,拉着姑娘,摔门走了。
一直走下五楼,到了大门口,姑娘才开了口,她说:“你没必要为了我……”声音终于哽咽了。
他们在街上晃了一整夜,画家不回家,姑娘就陪着他。坐在通宵营业的小吃店里喝豆浆,一碗一碗地,服务员要扫地了,他们就挪桌子。最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四面八方都是镜子,画家坐在姑娘对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她的后颈,有一个漂亮的骨点微微突起,好像有一只莫名的手,把她高高提了起来。画家拿出本子画了起来,姑娘抬起头,看着他,笑了,问他说:“你又在画我?”
然后她说:“你不要老画我了,我不好看的呀。”
“怎么不好看?”画家反驳,“好看的。”
姑娘不再争论,低着头喝豆浆,轻声问他说:“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结婚呀,”画家说,“结婚以后,还可以生两个孩子,最好两个都是女儿,都长得像你,我要画好多画,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山里面自己修一所房子,修那种细长的窗户,一直通到天花板的,你一定喜欢。”
姑娘抬起头就笑了,她说:“那可以种满一个花园的花和果树,一年四季的都有,这样就永远有新鲜水果吃了。”
“是啊,”画家停下画笔,看着她的脸,“我们可以种很多葡萄,搭一个凉棚,下面放着椅子,夏天来了,你看书看累了,就摘葡萄吃。”
她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低声说:“过来亲我一下。”
他就凑过去,亲了她一下,她的嘴唇,凉凉的,带着黄豆的芬芳。
第二天,画家起得很早,他在画一张小画,但画得很仔细,来这里快一星期了,他一直在画这张画。自从在市立大学当上了老师以后,画家沉浸在教育和培养信徒的乐趣中,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愉悦地作画了。
那天他开车来到白鹭镇的时候,看见镇门口种了一小株葡萄,顺着竹竿爬了一截,生着几片叶子,虽然如此,它的茎依然死死缠绕在竿上,一张一扬,线条是那么的漂亮。画家突发奇想,就决定画这么一张画,用的是黑色,绿色,和隐隐的宝蓝色,抹着土黄的底。
他沉浸在那些线条中,弓着身体,攀附在画架上,或者直立起来,划下狠狠的一笔。今年儿子要上小学,妻子说最好去念双语学校,母亲念叨说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因此,画家决定来画室待一个多月,要画至少十张画。但他走火入魔似的,重复在这张画上,不断地叠加着,否定过去的线条,长出新的线索,或者分裂为二,生根发芽。
他不知不觉地,画了一个上午,抽了一根烟,突然就觉得饿了。
他也懒得再出门去,到厨房里从带来的一箱方便面中拿出一包,开始烧开水。
水还在炉子上,门铃就响了,开了门,是木匠。他骑着一辆三轮板车,车上是大大小小的一摞画框。木匠咧着嘴问画家好,他说:“你看,你来那天说要的框子,我加班加点地这就给你做完了。”
画家说了声谢,向车上看去,这才看见有一个女人站在停好的三轮板车旁边,扶着那些高耸起来的角。她低着头,头发很长,应该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女的。今天,他清楚地看见她连衣裙的颜色,是橘红色的,穿着一双奶白色的皮鞋。画家几乎被那双鞋纯净的色彩迷惑了,想要走过去,看得更清楚些,却听见炉子上的壶悲伤地叫了起来。
他连忙开门让他们把东西搬进来,闪身进了厨房去泡面,等他把一切弄好了,出来,看见框子已经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墙角,木匠和他的妻子站在门口,前者看着他,保持着习惯性的微笑。
画家说:“你再给我做几个外框,完了我们再一起结账,行不?”
木匠爽朗地笑着说“好”,画家走到桌子边,撕了一张纸,说:“我把尺寸写给你,你们先做吧。”
他写好尺寸,转头,看见木匠还是站着,他的妻子却已经坐到了沙发上,并且看着桌子上的一本书,是一本很老的小说,画家前天从房间里找到的,也不知道是谁忘记在这里的。“你要是喜欢,就拿回去看吧。”画家一边把纸递给木匠,一边脱口而出。
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有一张很白的脸,这在这里很不寻常,眼睛不大,但是很柔软,神色一时有些茫然,然后,她确定了他是在同她说话,于是点头,笑了,说:“好。”
她的声音有些潮湿,像山里生长的小丛灌木。
木匠连声道谢,略带着不安。画家送他们出了门,看着那女人的背影在拐角消失了,她手里拿着那本书,晃来晃去,像拎着一只母鸡。
最开始的时候,画家也没有想到要结婚。他们住在一起了,早上,姑娘起得很晚,他起床了,坐在床上看着她,就拿出本子来给她画像。
画到一半,姑娘醒来,眼睛深黑明亮,像从来就没有睡过。姑娘跳起来说:“你为什么又在画我?”说着,跳过去,夺了画家的素描本,伸手就把画撕了下来,再一抖,撕成了两半。
画家一股无名火起,用力地推她,问:“你为什么撕我的画?”
姑娘说:“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回来那么晚!”
“几个朋友聊天啊。”他说。
“我等你等到三点钟,晚饭都没吃。”姑娘撅着嘴。
“那你不能让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陪着你啊!”
姑娘一句话也不说,爬起来,穿上衣服,默默地刷牙洗脸,然后穿鞋就要走人。
“你去哪里啊?”画家莫名其妙,一把拉她回来。
“出去走走。”她低声说。
他火了,伸手过去一拂,门口柜子上一堆玻璃瓶子噼里啪啦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都是香水瓶子,裂开了,尽是芬芳,浓烈地冲刺着。姑娘连连打了两个喷嚏,眼泪顺着流了下来。顿了顿,还是甩了画家的手,跑了出去。
画家一个人站在房子里面,满屋子的碎玻璃,他管也不管,坐到沙发上,重新拿起素描本,开始画画,凭着记忆,画刚才姑娘撕掉的那张画——画就是这样,一旦被画上了,就脱离了对象,成为了自身的本体——为了摆脱这些胡搅蛮缠毫无意义的句子,画家猛地从荆棘中站了起来,终于决定立刻就下楼去找那个姑娘。他翻遍了沙发,找到了钥匙,穿上鞋子,冲出了门。
画家在等电梯下来的时候,朋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你昨天要我打听的画室,我找到了,下午来不来看?”
画家按着下降的按钮,按了好几次,对朋友说:“算了,我以后还是在家里画画。”
他下楼去,满院子都是狗,他烦躁地走出院子,发现姑娘正在对面路边等他。她穿着长裙子,坐在台阶上,裙摆落了满地,双手托着脸,面无表情地正对着他,脸上泪痕未干地,笑了。
画家走过去,蹲下来,摸摸她的脸。“你刚才是不是想和我分手?”——黑黑一对眼睛,看着他,期期艾艾地,问。
他说:“我不会和你分手的,我们结婚。”
她说:“你骗我。”
他说:“真的,我画一百张画,存够钱,我们就结婚。”
早上,画家出了门,有些懊悔:昨天,他发了一个下午的呆,不知道在想什么,像被洗脑了一样,什么也没画。他向镇子走去,沿岸都是树木们蓄势待发的潮润气息,空气中有一种莫名的花朵的香味。他无聊地点着打火机,要去买几包烟。
杂货店离木匠的铺子有三个铺面,远远地画家就看见了木匠的妻子,她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穿着围裙,盘着头发,在杀一只鸡。
她脚下放了一个精美的小瓷碗——画家强烈怀疑就是那天晚上盛盐煎肉给他的那个——左手握着鸡脖子,右手握着菜刀往鸡脖子上一抹,画家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情,血就被放到碗里了,鸡挣扎着,用力蹬着腿,可是这些都不管用,血盛满了大半碗,它终于没了动静。
女人满意地看了看鸡的脸,把它放在了台阶上,然后端起碗,拿着菜刀,进了屋。
画家有些惊诧,大气也不出地从有些溅出的血滴边走过。
他去买了三包烟,迫不及待地拆开一包,点上一根,狠狠抽了一口,像是压惊。他转身往回走,就看见木匠的妻子又出来了,这次放在凳子边的是一桶热水,她弄湿了鸡,蘸着水,一把一把地拔下鸡毛,丢到簸箕里。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画家可以看见她光亮的前额,不时掉下几根头发,被她麻利地吹开了。
画家从她身边走过,迟疑着要不要跟她打个招呼,她却看见了画家,抬起头,对他笑了。
她说:“你昨天借给我的书,真好看!”
那本书画家看了不到十页,只得虚应了一声。但因为那本书,她对他的态度亲切了很多,把满是鸡毛的手在桶里涮了一下,问他说:“买东西啊?”
“买烟。”画家挥挥手里的烟。
“给我一根?”女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