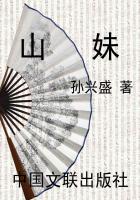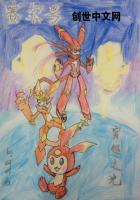谁能忘了中国名指挥郭文景呢,一个灰发长飘浪漫味十足的男人?他在十年前指挥交响团演奏《和平交响曲》,让多少炎黄子孙流下了泪水。自那以后,郭文景的演奏风靡全球。郭文景一出现在舞台,欢迎他的掌声一波接一波涌起。他的手一挥,全场戛然安静。钢琴、定音鼓、汉语的合唱响起,鸟叫,旋律上升,雪山融化,万物在河流两岸生长,阳光和煦,浮现出一幅幅春天的音画。一改合唱曲中的沉重,变得轻快、华丽和抒情。
“《悬棺套曲》!”我差点叫出声来,抓住身旁娜塔丽的手直摇晃。郭文景的这个剧,是根据中国三峡古代传说改造的殉难剧,但有着极强的可塑性,在北京的演出着重于宇宙性;在拉萨的演出则是史诗;在长沙、昆明的演出类似乡村行吟剧;在重庆的演出,却像一个超现代化的川剧;在纽约和巴黎的演出则是
中世纪神秘剧。从舞台无布景、乐队、合唱队的设置来看,正在这城市演出的《悬棺套曲》倾向于清唱剧。形式简单,反而使套曲本身的魅力表现得更为完整,更能击中它所想揭示的生命、命运的本质及神秘莫测。
娜塔丽从舞台掉转脸,黑暗中,亮闪闪的眸子仿佛在说,不枉此行吧!她不允许我看广告,不允许我问别人,就为了让我这一刻激动。
两次低音单簧管,加上六孔竖笛,使乐器成为透明。高音乐器吹低声调。
与伴唱的四川高腔相衔,二胡接了过去,悲怆、细腻地展开,舞台上重复地响起川音的悲呼:噢,哪个人爱我吗,哪个人会爱我吗?笛子和定音鼓,将大量的音响色块卷裹开。我恍若在游行的队伍中,重新辨认一座座城市,我曾经到过的所有的城市,包括这座娜塔丽的城市。如一个切分音,一个声音在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音乐厅里查叛乱信号的秘密警察,不只在布拉格有。假声的男高音又哀号起来时,京胡在高音域伴奏,管乐之合奏给整个乐调一种奇玄的风格。
我在哪里啊!已不在人世的母亲朝我走来,她伸出双臂,想拥抱我,却被一层透明的薄膜相隔。她的嘴唇启动,口形像是在说,皮肤革命革来革去有什么用?皮肤还是皮肤。母亲的正确在于把所有的不正确变为更正确。我们的肤色,我们的快感,我们的傲气与谦卑,我们上下嘴唇的狂恣,我们的富裕贫穷、青春衰老都在皮肤上;人的美丑也取决于皮肤最简单的安排,所有的反馈也在皮肤上。离开皮肤,一切都没用,真的没用!只有死亡才可使我们抛开皮肤,远离感觉世界的烦恼。
乐曲进入新的一章,为上一章华彩的顶峰,它讽刺、讥笑,好像在调侃一切歌剧,然后,是定音鼓和钢琴,加入急不可耐不可阻挠的旋律,是无羁的狂欢。女高音温柔地展现她的装饰音,把川音糅成说唱式的吟咏。
我是一个对音乐狂热到生病,迷恋到可以自杀的人,音乐居于我心中的位置与写作并列,虽然我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唱歌时五音不准。相对艺术,爱情属于次要地位,不管是对男人的还是对女人的爱情。我爱上艺术时,正是少年时期,理想、远大抱负之美好教育,却掩盖不了文化大革命留在精神上的伤口和血迹。未来之恐怖,与未来光辉灿烂都是不可靠的假定,唯有艺术,始终属于仰望位置,在我面前。
现在,在未来的边缘上站着的我,音乐,写作,可爱之极的爱情,泛泛地回忆,或长久深深地遗憾都退得遥远。有什么东西可使我信任,可将生命相托?又有什么东西可打动我,再抛洒出几滴热泪?我不会,也不相信其他人会,即使我面对郭文景的音乐,即使我有那么几分钟回到一九六八年、一九八九年时的布拉格,回到一九六八年、一九八九年时的中国。
因此,当我瞥见面朝舞台右边第二个包厢里的花穗子时,竟觉得是个幻觉。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我和她仍是同一类人!十八世纪宫廷贵族夫人装束的花穗子,肩臂裸露,乳房撑起,头发高绾在头顶,一只手举着望远镜。装饰着巴罗克风格半裸的天使的包厢内,还有哈谢克。她的背后是张俊,打着黑领结。
同样的,如果花穗子看到斯梅塔那歌剧院池座里的我,用这残破的身体和心灵去抚摸郭文景的音乐带来的回忆,她也会吃惊的。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半老徐娘,丧失掉多少珍贵的东西,远远不只是面皮的细嫩与乳房的坚实!
舞台上,穿蓝袍的女声,穿白袍的男声,随着指挥,让主合唱曲流畅地进入终曲,超度的经文在把迷途的灵魂送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