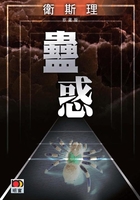圆形人工喷泉,五百七十个喷口齐放,八十八盏灯打在喷泉上,富丽堂皇的音乐厅正在演奏宏博壮远的《八仙梦》序曲,这个大型歌剧被誉为东方人的《尼伯龙根指环》,是种族神话的再现。
盛服奇装的男女观众聚精会神,跟随指挥棒进入蓬莱仙境,主人公将被魔妃收走,变化成一个小石蛙。经过地狱降魔等磨难,他的胜利,他的成佛是注定的,带有些许世纪修愿积德的良好的宿命。
红丝绒的地毯在我的脚下移动。
柔软的皮椅座位,金色的前厅走廊,这个夜晚的流逝恍如幻觉,不同于以往逝去的日子。我在大提琴有力的挥舞和小提琴作为配合的低泣声里,从台上庞大的交响乐队统一协调的动作之中复苏过来:这是一个虹身人面。
在我躲藏期间,曼哈顿时局的转换之眼花缭乱,令全体美国人精神紧张,只有某一类人不惊讶,那就是我这样的每天都在注视的旁观者。
高僧打卦问卜,说桑托巴本图克感应虹之子已早夭。即使那孩子还在,桑托巴本图克死了,差不多一样,除非教内高僧们出来主持公道。但阿巴年札不愧为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按照制造的遗嘱,圆满地解决了大法师继承问题。
教内不得不承认他为摄政,另一派人马清除的清除,不清除的早已宣誓效忠新主人。
通向四面八方寺的所有街道,悬挂着新鲜的花朵和彩带,路旁洒了两条白色石灰线,屋顶插挂伞、盖、幛、旗帜。在前大法师圆寂时值一年有余的这天清晨,新大法师坐床大典响起了唢呐、大号、皮鼓、铜钹。每扇门每扇窗飘出焚烧加有香料的松柏枝子气味。而我成了数十余华里长欢迎的僧俗民众中的一员,暗自庆幸自己已是个不相干的外人,阿巴年札有的是他尽心尽力忙的事,哪里还会再注意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我退出狂热的人群,独自走了一段路。然后坐上双层巴士,我想避开不看的坐床大典却在巴士里的电视里播放。
我回到蜗居的非对抗区,只偶尔才去南曼哈顿。谈不上讨厌,也说不上喜爱。由于南曼哈顿政局重新稳定,格外繁荣,这块中曼哈顿也跟着兴旺得无以复加,富丽多彩。各民族至少在表面共同维持了安宁的共存景象,全世界都庆幸南曼哈顿有了英明的领袖。阿巴年札的神权帝国计划,也许只是政治上的叫牌,根本不想付诸实施,至少在目前,在没有真正权力威胁的情况下,倾向于维持一个和平局面。南曼哈顿现在变成比新加坡还整齐漂亮平安的花园城市,各处的秩序和洁净叫人透不过气来。
压抑?这算得了什么?我不知自己滞留在这儿是出于何种目的。一两夜的失眠,转为夜夜的失眠,伫立窗前,眺望一片灯火,忽明忽暗,神思云游。去相信桑二没死?中了那么多子弹,他当然死了。或许我只是在等待冥冥之中的一声轻轻的召唤,等待一个等候许久的契机而已。
万鬼节还未到,中区街上全是戴着幽灵鬼怪面具的人。有的人唱跳,走火绳,跳踢踏舞、咔嚓步,三三两两黑影,在涂满下流、野蛮、粗鲁的字句和图画的墙之间游逛。和北曼哈顿的景致有许多相似,但稍有安全保证就成了一种供游览的奇观,多少使一些人不敢去北区的奇异心理得到满足。北区在他们眼里是废弃的房屋、玻璃窗罩一层铁丝网、店铺统统装警铃,越朝北去越看不见街上有公共电话亭。浓烈的宣传所组成的危险使游人不敢涉足。
街灯砸了,第二天路警就装上去。也许中曼哈顿的存在就是让人们在此好好透一口气,本着这一点自由的味道,使那些已习惯自己社区秩序井然的循规蹈矩之人竟然也闻讯前来。秩序很好,对社会很重要。但人最想摆脱的不就是这玩意儿吗?
第五大道在我灌满风的斗篷似的外衣上呼呼闪过。
不一会儿,四十二街就近在眼前。今夜星光比以往任何一天都斑斓,但天特别高、厚重,发绿地朝后缩退。
“好吧!你可以加入这一段舞。”老板是个胖女人,样子像意大利人,挑剔地看着我裸露的身体。“但要一星期试用期,我们才正式签合同。目前两天领一次薪水,小费自得。”
桑二给我的钱已经快用完。为减少可能出现的危险,我早已不去前哥伦布大学领那份奖学金,没准奖学金早就自动或被动地取消。我得找工作——中区工资低,但我不想到南区富裕的东方集团当什么子公司孙公司秘书这类的角色。我得自己挣一口饭吃,毕竟舞女的工资比教授还高。
我穿上衣服,跟着老板走到化妆室。
设计师、化妆师、服装师围了上来,重新剥去我的衣服,打整我的头发、皮肤,套上美人鱼的贴身长裙,和皮肤色泽、薄厚衔接得天生一般。
镜子里没有半点我的模样,只有黑眼珠,湿湿的,像泪盈满眼眶,虽不那么年轻俏丽,却比往日动人,沉静中融入沧桑。这还未达到我要的效果。于是,我在颧骨、手臂上的文身加了两刷子银色,既遮掩了原文身的色泽,又出其不意地鲜亮。
日本国公主千千明美出场!司仪兴奋地向全场报告。
我拒绝用升降机。理由是我的游泳技艺你们即刻就可看到。话刚一说完,我便像一条真正的鱼,射入碧蓝透明的池水里。在水里扭转身子,一件件外衣自己游离开去,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时间在我的身体上抚摸梳理、消隐。猛地,我从水里飞了上来,稳稳地站在水面舞台上。
全场鸦雀无声,几乎在同时,掌声如风暴和台风袭来,仿佛整个房子结构倒转了一百八十度。陶埙、螺号、单弦琵琶、琴加入进来。
垂下眼睫毛,我轻轻一摆动下身,不知怎么地,那紧粘在皮肤上的鱼鳞裙子便滑落到水里。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当然知道这是个无上装酒吧,并非脱衣舞表演厅,但这时我也无法可想了,我不能头场就演砸。但这不是我来此的目的。伸展四肢,微睁开眼睛,我把身体折成一枚花蕾、一个花蕊、一朵怒放的花瓣。
男人们从座位站了起来,连女人也停止了谈话、品酒、抽烟。
大张的钞票放在池子边沿的玉盘里。呻吟声从乐器里逐渐扩散,配合着水纹的波动荡漾。我从水底一撑手,倒升出水面,笔直地,然后双腿一劈,叉在水面上倒旋转起来。第二场暴风雨刮了过来,掌声齐鸣,即使停止变幻的灯光,那每张脸也一样泛着奇奇怪怪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