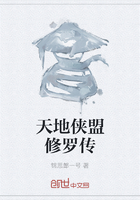她把今天赚到的钱尽数放尽衣柜里,而后好好细算一遍,看到底还需要存多少钱才够宁小邪以后念大学。
十五块人民币不翼而飞,让她心痛不已,她断定,这就是宁小邪的旧病复发,倘若家里遭了贼的话,绝对不可能只拿走那么点钱。
那是她第一次打宁小邪。细长的皮条在宁小邪的身上烧出了一条又一条的火线。她一面狠狠地打,一面哽咽着说:“你说!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到底答应过我什么?!我供你念书,教你做人,看来,全是白费了!”
宁小邪在狭窄的卧室里哭得喊天抢地:“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不是偷钱,我真的不是偷钱……”
后来,宁小邪的一句话,使她再也用不出半点气力。宁小邪捂着通红的双手说:“妈,今天是你生日!”
她忍住热泪,悄悄地走出房间,终于看清了木桌上的糖醋排骨。宁小邪萎缩着,跟在她的身后,喃喃地说:“妈,我没有偷钱,我真的没有偷钱,我只是想在你生日的时候给你做一盘糖醋排骨,让你也好好吃一回肉……”
顷刻,在她内心积压的情感和生活的委屈,如同山洪一般喷薄而来。她紧紧地抱住宁小邪,禁不住大声嚎啕。
那盘面目全非的糖醋排骨是她生平吃过的最好吃的菜。从来没有一种菜,可以让她吃到泪眼潸潸。
期末考试如期而至。语文试卷的最后是一道命题作文,《我的母亲》。
她笑问宁小邪:“你都把我写成什么样子呢?”
宁小邪说:“妈妈,我写你是上天最好的馈赠。”
一生的温暖
西部志愿者还没来的时候,一直都是我带这个班。
教室在山洼里。雨天积水,冷天风大。村里没钱,不可能新建学校,只能自己想办法。
为了防寒,教室只留了东面的一扇窗户。他就是窗户下的孩子,名叫张天佑。
他母亲说他自小体弱多病,多灾多难,因此,给他取名天佑,意在祈求上天保佑。
他成绩不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很少说话。有的时候,一个人坐在窗边,整整一个上午,连位置都不挪一下。
冬天来了,天逐渐冷了。东面的窗户时常呼呼地刮进刺骨的大风。我用废弃的试卷把窗户粘了起来,但没过两天,就被大风吹破了。被撕裂的纸页,摇摇晃晃地挂在窗户上,寒风一吹,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他坐在窗边,经常冷得缩成一团。
最后,我从地里捡来了两个装尿素的口袋。裁开,平铺,用钉子把它牢牢固定在窗户上。
口袋上,有两个特别扎眼的字,尿素。他一抬头,就能看到。很多孩子利用这个事情从他身上找乐子,给他取了十几个外号。什么尿素小子,什么猪八戒,多得我都记不住。
他母亲在家里昏倒那天,我恰好坐在办公室里改作业,誊抄花名册。因为第二天,从北京毕业的两个大学生就要过来任课了。我总不能把自己在职期间的作业留给他们来完成吧?
我用板车驮着他母亲,一路小跑。他跟在后面,使劲儿帮我推车。寒风呼呼地在山洼里回荡,我停下身来,把厚实的棉大衣铺在了他母亲身上。
乡里的医生说,没有大碍,不过是有些贫血症状,再加上长期劳作,营养不良,才会导致忽然晕厥。
准备回去的时候,山路已经漆黑不见五指。没有月光,无法前行。
我们只能在乡卫生院的空床上凑合一夜。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他马不停蹄地往学校赶。这从首都毕业的大学生可能就快到了。前天,村长和校长和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要做好准备工作,不能迟到。
他只穿了一件皱巴巴的棕色毛衣。他的小脸被清晨的寒气冻得通红。没吃一点东西,又跑了那么久,实在撑不住。
我把棉大衣脱下来,想给他披上。他扭动着双肩,拒绝了。我又跑上去帮他披上,他再次拒绝。如是再三,终于接受。
我蹲下身来,一面帮他紧上扣子,一面反复不停地说,别急,没事儿,慢点儿走,山路滑,反正都是要迟到的。
他怔怔地看着我,始终没有说话。
工作交接完毕之后,我去了乡里。那件大衣,也就忘在了他那儿。
很多年后,有人出资重修学校,村长又把我叫了回去,说务必参加新校落成的典礼。
我去了,却没有认出他来。后来,是他向我报出自己的名字,我才隐约想起那个名叫张天佑的孩子。原来是他出资重修学校。
典礼之后的宴席上,他举着酒杯跟我说,老师,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件棉大衣吗?我至今仍然留着。它给了我一生的温暖。
陪他走完最后的人生
我始终不能读懂父亲的眼神,当他在年终换取日历的时刻。他佝偻着背,将墙上的最后的一页日历取下来,挂上崭新的时光,哀叹着说:“唉,有一年过去了。”
那时,我对新年总是充满了欣喜。它意味这隆隆冬雪,悠长的假期和一连串火红的炮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兴许还能换上一身新衣。因此,我爱新年,爱墙壁上的最后一页日历,甚至,爱匆匆流去的时光。
我并不知道,那些使我热爱的时光会将逐步将我领向衰老,并且它们一去不回。倘若我当时已经明白人生与时光的联系,我必然不会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没过几年,我的下巴开始渗出细密的胡茬。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窗外嬉戏的孩童,听炸裂的爆竹,有着恍如隔世的落寞,但心中到底是欢喜的。我一直渴望长大,成为男人,担起该有的责任,去实现永不更变的梦想。
数年间,家已搬迁多次,换了城市,我亦从无知的孩童变成了莽撞的青年。可有一种东西始终不曾变过,那便是墙壁上的日历。无论云南还是广西,湖南抑或四川,它始终安安静静地平靠在内屋的白墙上。它像一种亲切的口吻,一个特立的标示,告诉我家的存在。
父亲依旧换着日历,只是不再悲叹。早年的粗重活计使他患上了无法彻底根除的病症。医生说,他的风湿老寒腿是因为长期立于水中作业造成的,而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则是拜黄土地所赐。
阴天下雨,父亲就只能安静地坐在火炉旁。我时常想起他当年站在秧田里工作的模样。他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一家人,可年复一年的劳动所赐予他的,却是这样形影不离的病痛。我实在为他觉得不公,但我从不愿说出,我怕他会因此感伤。
这些年,他已换了模样。那些粗白的发和干涩的咳嗽都像是一夜间从他身体里钻出来似的。他变得越来越喜欢说话,尤其碰上年幼顽劣的孩童,更是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罗嗦的老头。很多年前,这是他一直痛恨的事情。他时常责备街角那些成天玩闹的老头,说他们为老不尊,可今时与之相比,他似乎并无任何差别。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尤其在新年之后的那几日,更是让人觉得他有些莫名其妙。他失去了当年的耐性,一件事情只要反复交代两遍还未有人照办,他便暴跳如雷,吼声震天。我和妻子都怕了他,尽量哄着他,让着他,就像当年他容忍我的所有过错一样。
又一些年过去了。我的父亲终于像墙壁的最后一页日历,被时光无情地抛在了脑后。我与他从此相隔,再不复见。当我慢慢步入文学的路途,试图用文字去解答人生的困惑时,渐渐明白了他中年之后的心境。
当你韶华飘逝,风烛残年,当你记忆模糊,来日可数,你定会明白一位老人的所有惧怕和坏脾气的缘由。其实,他们多想你伸出双手,搀着他们,溺爱他们,就像他们当初耐心教你走路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们走完余剩无几的人生。
在年的更替中老去
记得学堂里的孩子曾在冬至大雪时问我过一个奇怪的问题:年是什么?我思索了片刻,不知如何回答。
到底年是什么呢?是崭新的碎花棉袄与母亲的千层底,还是一包隐在鲜艳油纸内的甜腻糖果?抑或是一串在家门前劈啪炸裂的炮仗,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都不是,它们虽是那么逼真,那么不可或缺,但仍旧无法释义年的命题。
我想,年得是一本泛黄的日历,因此,它必须要与时间有关。于是,我在草纸上将它等算成分,等算成秒,等算成一把具体的数字。可这些毫无生趣的数字,就是匆匆的一年,与又一个匆匆之年的开始吗?
最后,我只能牵强地告诉学堂的孩子,年是青春。是的,年是青春,可青春这种东西是该有归宿的,到底,谁才是它的归宿?而它,又到底该是谁的青春呢?
我在脑海中搜索一切关于年的记忆。幼时,大伯远在红果,每年冬至才风尘仆仆地回来一次。因此,一年之中,我与他相处的时间总是短暂到只能用小时来计算。但这丝毫不曾影响我对他的思念与记忆。
他是个中年遭弃的男人。我当时并不明白离异是何结局,但依稀明白,那将意味着后来的漫长孤独。我害怕孤独,因此,我义无反顾地认为大伯也害怕孤独,并在心里默默觉得,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可怜的男人。
他喜欢坐在杯盘狼藉的八仙桌前听我用尖细的童声唱《潇洒走一回》。每唱完一遍,他就会爽快大笑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脆响的人民币放在酒杯旁。我被这不知所谓的氛围鼓噪着,没完没了地唱,直至喉咙沙哑,声嘶力竭。
我清楚记得,每每唱到“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谁也知人间多少的忧伤”这句,他的双眼里便会注满晶莹的热泪。
遗憾的是,童年的笑声还未全然消泯,他便随风而去了。再没人从千里外风尘仆仆赶来看我,用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听我唱走调的《潇洒走一回》,而我,也再没了那种甜蜜的渴盼。
我由此渐然觉得,年是旧三百六十五天的消逝与新三百六十五天的开始。旧的已经过去,已经被淡忘了大半。新的,正陷入一种喜悦的未知。因为未知,我们才有了继续下去的希望。
曾经的年,是母亲在洋洋大雪中抱着我去逐次挑选新衣,说一些祝福的话,包来一碗滚烫的元宵。而今,却是我牵着母亲的手,在寒风阵阵的街头慢慢行走,内心希望她长命百岁,口中却不发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