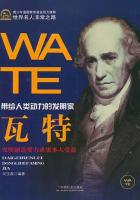这年8月,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一文,连载两天;对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此语之值,在其所以为今古之界者而定。若谓古人之言之外,别有所谓今人之言者,崭然离立,两不相混,则适之之说,乃大滑稽而不可通。”接着批评白话文学者说:“今为适之之学者……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今白话文之所以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者,其弊即在为文资料,全以一时手口所能相应召集者为归。此外别无工夫。”最后感慨地说:“呜呼!以鄙辈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愚窃以为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矣运动方式之谈,流毒乃若是也。”此文发表时,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9月27日,双方都认识的朋友潘大道游西湖,走访胡适。见面时转达章的意见说:行严(章的字号)说你许久没有做文章了,这回他给你出了题目,你总不能不作文章答他了。胡适问什么题目,潘答,就是《评新文化运动》一文。胡很风趣地对潘说:请你告诉行严,他的文章不值一驳,我只好交白卷了。”潘问“不值一驳”这四个字可以告诉他吗?胡很干脆回道:请务必达到。后来胡适休养中到过上海;10月8日,“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请章士钊与陈独秀、胡适吃饭。胡适当面告诉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那篇文章不值一驳。章听了表示满不在乎的样子。宴后,汪对胡说:“行严真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他居然没有生气。”胡说,他是装作不生气,其实他的文章处处是悻悻然和我生气。骂我们作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这岂是“雅量”的表现吗?又说:我们观察章士钊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能隐忍一时,终不免有诟骂的一天。话虽如此说,但他对章的态度还是很佩服的。在日记里,他说:“行严确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但他的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gentleman(绅士)。”两年后他二人又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相遇。饭后一起照了张相片。相片印成后,章题白话诗一首送给胡适,并致函云:“适之吾兄左右,相片四张,账已算过,请勿烦心。惟其中二人合拍一张,弟有题词;兄阅之后,毋捧腹。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章诗云: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循章所请,用古文作诗一首回答他,诗云: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我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这时由于北京执政府善后会议的召开,他二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议,在政治见解上有共同之点,敌对情绪有所缓和,故有此唱和之诗作。后来情况变化,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宣称“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而且放肆地攻击白话文,说什么“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胡适又写了《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他说:“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对章进行了说理斗争。但章还不服气,又作了《答适之》一文,针对上述论点进行辩论,但也是有气无力,强弩之末,未能穿鲁缟者也。说明古文派的力量到此时已是回光返照,成不了气候了。
同年8月10至14日,中国科学社第八次年会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召开,签到者有胡明复、胡敦复、翁文灏、曹惠祥、叶元龙、何炳松、柳诒徵等同仁30余人。来宾有浙督卢永祥等人。马君武为特邀社员,汪精卫、胡适、杨杏佛等以社员的资格皆有演讲。在这次会上胡适与汪精卫第一次见面。据叶元龙回忆说:开会那天汪到会场以后,第一句话是问哪位是胡适之先生?当时只见一位面貌清秀,态度和蔼,蓄了短须的青年起来打招呼,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胡适之。从此以后,他们便开始认识了。会上先由社长任鸿隽致开会词。马君武的讲题为“科学与朱儒”,汪精卫讲“个人对科学之概念”,其他如胡明复、翁文灏等皆有专题报告,胡适因在病中,好友任鸿隽没有勉强他作专题演讲,只是在闭幕那天作应酬式的发言。不过他在会议休息的星期天,即8月12日被邀到浙江暑期学校去讲演,讲题为“科学的人生观”。他在开场白里说,这个题目前后共讲过五次了,不敢自信,所以至今还不敢发表。第一次1921年夏,在暨南学校讲。去年又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笔记共有7份,由原笔记者、法专、晨报记者三处转来要求修改发表,但都被我压下了不敢发表。今年看了科学与玄学战争的许多文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稍稍有所修正。今天在浙江暑期学校讲,力求明显浅近,不能不砍落一切枝叶,专注重我所认为今日必不可不有的几个要点来说一说。山中无书,深感不便。我希望将来有细细修正的机会。接着开讲本题。他说:什么叫做科学的人生观?这问题的范围很广,从来就有唯物的和唯心的种种解释,为哲学上悬而未决的大问题,现在无暇细论。我所要讲的是把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用来作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应该知道:科学的精神,就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就是科学的方法。杜威说:“假如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如物理化学等一齐毁灭都不打紧;只要他的方法存在,仍然是可以产生科学的。”可见科学方法的重要,于是他讲了五个特点:(1)特殊的,不是笼统的。换言之,就是这个那个的具体问题,不是包医百病的抽象问题。(2)疑问的,不是盲从的。就是对于无论甚么问题,都要问“为什么是这样?”不要“人云亦云”。(3)假设的,不是武断的。就是自己有所主张,只能说假定如此,大概如此;不能说一定如此。(4)试验的,不是固执的。就是假定之后,再用种种试验来证明;错了,马上废掉不用。(5)实行的,不是空谈的。末了最为重要,就是证明之后,还要能够见之实行。以上所说的五种,都是科学方法的特点。下面举例说明。(从略)上述为胡适讲演记录稿之一,从中可看出当时的情况及其所讲的大概内容。后来,1930年他曾在苏州青年会讲过,又有所修正。同年正式发表于范祥善所编《现代科学评论集》一书里。这次他把科学方法五点改为四点,略记如下:(一)是怀疑,有了怀疑态度,就不会上当。(二)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三)证据,就是拿证据来。(四)真理,朝夕去求真理,是尽一点责任。明知赛跑,只有一个人第一,我们还要去跑,不是为我为私,是为大家。发明不是为发财,是为人类。综上所述,可见胡适宣扬的科学人生观,其内容变来变去,还是在讲杜威的实验哲学,真是万变不离其宗。当然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不过怀疑一切,否定理论的作用是错误的。
科学会开完后,任鸿隽、陈衡哲等又到烟霞洞陪胡适玩了几天。在此前后,徐志摩、瞿秋白、高梦旦、汪精卫、马君武、朱经农等人也都到胡适住地访谈过,共度暑假倒也热闹一时。不过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秋天来了又各自忙着回去工作。胡适于10月4日下山,次日到上海。这时,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操纵国会爬上总统的“宝座”,全国震惊,纷纷进行口诛笔伐。胡适刚到,他说,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上海一般朋友都不愿我此时回来,大家谈论的结果,都劝我暂时不回北京。于是与任叔永夫妇、朱经农、徐新六等社员商议,《努力周报》暂停,仍继续出副刊《读书杂志》。并称,停办之事非我本意,但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因此在《努力周报》上登出“胡适启事”,略谓:顷来上海,再受医生的诊察,医生仍不许我多做工,只好决定《努力》暂停,将来拟办《努力月刊》云云。后因形势变化,内部意见分歧,这份月刊终未出笼,胡适感到遗憾。
胡适回到上海后,应“亚东”汪孟邹之请,为该社即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文集作序。与此同时,汪也请了陈独秀,他二人分别到编辑所去写。此事在汪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载。汪说:“他们都真有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指陈)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从上可见,他二人性格、作风之大不相同;一个是细致,一个是粗犷,各有所长。因为观点不一致,所以他们又发生了争论。先是陈在序言的后面对胡适等提了一个问题,意思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只能选择一个,看你是站在哪一边。他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胡看过陈的序言后,写了一封《答陈独秀先生》信,他说,“独秀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一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解成‘经济的’,因此,他责备在君不应该把欧战的责任归到那班非科学的政治家与教育家的身上。”其实他们的争论,是把物质与精神,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对立起来,故各持一端。胡适强调精神与上层建筑;陈则强调了唯物与基础一面,本质上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因为立场不同,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陈又有《答适之》一文。他说:“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作用。”又说:“适之颇专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胡适看了陈的来信后,也不想再继续争论下去了,于是写信给“亚东”的编辑章希吕,申述自己的看法,最后说:“仲甫的答书,近于强辩;末段竟是诬人,使我失望。”可见他二人的思想分歧是越来越大了。原来是一致批判“玄学”鬼的,现在是同室操戈了。
胡适在作完上述文章时,又接到北京梁启超的来信,问他能否回北京参加他们发起的戴东原生日200年纪念会。胡于11月13日回信说:“手书敬悉,戴东原生日纪念我很想参加,日内即动身离上海,在南京尚有小勾留,约廿日可抵北京了。”戴震是安徽人,清代的大学者。胡适一直很崇拜他,这样一个盛会自然不愿放过,所以他没有耽搁多久,便启程了;过南京时,在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其中特别赞扬南菁书院黄以周提出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格言。并认为书院的精神重自修,这很值得后人学习。胡在此稍事停留,遂于同年12月下旬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