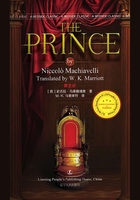这样的条件,她却不相信,这若是一场赌,她已知晓输的结局,又岂会自寻死路。“且不说皇上如今还活着,便是皇上驾崩,这江山也不会是你的,你拿什么来给我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可能实现的诺言,你许来哄谁?”
永瑢抬眸冷冷的瞥一眼容韵,略显严厉的斥责道:“诅咒皇阿玛,你可是活腻了?”
容韵无所谓的一笑,淡淡的反问:“谁不会死?如此恐惧死,是要表白你的懦弱吗?更何况……”她不屑的轻哼一声,敛了笑意,起身走到西面,冷然的声音传来:“你觉得我会怕死?”
永瑢微微扣起手指,眸色暗沉的盯着容韵。如此聪灵敏慧的女子,若是不能为他所用,依照他的习惯,定然是早日除掉的。只是,偏巧是她,他又如何能下手?
容韵注意到墙上还挂了个玉琵琶,伸手取下来,懒得再与他纠缠这些勾心斗角的烦人之事,想起上次以古筝弹奏《琵琶语》终是失了大半的韵味,那样哀伤婉转的曲子,也必得这琵琶信手拈来徐徐弹,才合适。
轻轻扣动琵琶,青翠叮咚的音色,明显是极好的。她自幼酷爱琵琶,所以这琵琶上的造诣远比古琴要好的多。一首下来,如山涧溪水潺潺而过,流水行云式的顺畅,却又自有高山流水的跌宕起伏。
最后一个凄清哀婉的收音,永瑢忍不住低声叫好:“这曲子的韵味总算出来了。”容韵将琵琶挂回原处,站起来抖抖裙摆,才低声道:“你这样的人,不该为皇位而拼命的,如今这般是为了什么?”
永瑢微微一愣,才低头一笑,淡然问道:“我几时说过要皇位?”看见容韵诧异的目光,他轻轻咳了一声,认真道:“今日所为只为江山社稷。”
容韵盯着他的眼睛探究了半晌,也着实看不出什么贪婪的意味,只有些无欲无求的淡然,以及已然掌控一切的霸气。“你改变不了什么,这天下注定不是你的,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为何如此肯定?你似乎已知晓未来?”永瑢微微蹙起眉头,奇异的反问。容韵张了张口,欲言又止,有些话说出来也不见得有人信,泄漏天机,会造成的后果,她也未必承担的起,所以,她终究只是淡淡道:“话我已说到,听不听随便你。”
永瑢见她不肯说,也便不再追问,无奈的长叹一声道:“我只是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天下,从未想过要登上皇位,总有一日,你会明白。”容韵疑惑不解的看了他一眼,也不再说话了。
之后这段时日,容韵就一直跟在永瑢身边,多数时间,是以书童身份出现,十五阿哥也暗中派人来找过她,询问她打探到的消息,容韵竟不知为何,没有真正说出有用的消息,只是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已引得十五阿哥不悦,她却总觉得,永瑢那样的男人,是不能背叛出卖的。
大约过了一个月,忽然有一天,永瑢自外面回来,带着两个人。容韵在看见那两个人的瞬间,惊得目瞪口呆,半天反应不过来。自从灭门之后,便未曾再见面的翠翠,看见她也是惊喜的泪流满面。
然而,容韵并没有太多心思与她叙旧,而是拧紧了眉头看着翠翠所搀扶着的女子。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她还可以、被称之为人的话,二十来岁的女子,容貌是极为清丽脱俗的,然而,那双眼睛,仿佛身处地狱底层的炼狱一般,惊恐,绝望,挣扎,迷茫,矛盾,怯懦……太多复杂的情绪都融合在她的眼睛里,而她的目光是无焦距的,如凋零的枯叶一般,四处游荡,被大风不断摧残。
“这是莫兰姑娘,是妈妈从一个苗人那里买来的,被关起来,过得简直不是人的日子,是六阿哥机缘巧合救回来的。”翠翠见容韵一直盯着那女子看,便叹息着解释。
容韵听见莫兰这个名字,只觉得内心似是被什么重物击中,窒息的闷闷的痛起来,这种痛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和姿态,肆虐她整个身体。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容韵脚下踉跄险些站不稳,一边的永瑢眼疾手快,身影一闪过去稳稳扶住她,扭头对一边要过来的翠翠道:“扶莫兰姑娘回去休息。”
“可是,小姐她……”翠翠还在担忧自家主子的身体,永瑢已伸臂拥住容韵,冷冷道:“她有我。”翠翠是何等机灵的丫头,一看这情况便知他们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也便不再多说,小心翼翼的扶着莫兰去客房休息了。
待翠翠走远,容韵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推开永瑢,大步后退,脸色煞白的瞪着他,紧紧咬着唇。
“当初即能想出这样的法子,你就该料到会有今日,何苦这样折磨自己?”永瑢也不生气,只淡淡的看着她,略带的叹息的问,他走到一丛白菊前,掐去一朵,细细的将花瓣都碾碎了,静静看着它们零落在地,才缓缓道:“此花不落,如何期待来年,这是自然定律,非你我能违抗。”
“化作春泥更护花……”容韵忽而失控的低声笑起来,带着凄艳与绝望,看着那淡然从容的男人,却又忍不住不甘的质问:“你自己明明可以想到比这个更完美一步的法子,为何非得逼着我说出来?”
永瑢自花丛之中冷冷回眸,犀利的望着她,薄怒道:“难道你还不知自己面对多少危险?我没时间也没心思护你一生,和珅更不可能,自己不强大起来,来日 你要如何过?”他走到她面前,一眨不眨的盯着她的眼睛,残忍道:“容韵,这是你的命,你已经没有选择。”
相识以来,他向来是寡言少语的人,这样长的一段话,对于他而言,已是罕见,而这种起伏波动的情绪,大约那帮手下见了,会惊呆的。容韵愣愣的看鬼一般盯着他看半晌,忽然双手掩面,回身朝自己的院子匆匆跑去。
永瑢并未追去,只是幽幽的盯着地上方才被他碾碎的花瓣,目光中露出悲悯哀伤的情绪来,若有来生,他期望能够生在寻常百姓家,那么,便可用尽一生,做那守护她的春泥,就算一世凋零,也是好的。
“化作春泥更护花……化作春泥、更护花。”轻轻念叨着,头一次听见这样的字句,却是深刻的触动心脏,嘴角浮起一个轻怜慵懒的笑意,他大掌轻率,也转身走远,而他手掌抚过之处,偏偏落花缤纷乱飞,迷了几只蝴蝶的眼睛,扑闪着翅膀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