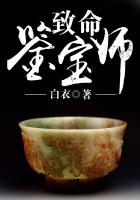“庭远先别走,”刘局气喘吁吁的跑来,“我有事问你。”
“有这个必要吗?”他双手一摊,冷冷的说,“房子,车子,拍卖也好,赔偿也好,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不要了可以吗?刘叔叔,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他的关系还没到同流合污的地步。”
“事情有点奇怪……”刘局欲解释。
“不好意思,”他生疏而客气的回绝道,“我的公司出了点事情,我得赶去处理。”
“庭远,”刘局打断他,好似下了很大决心,“我只问你一句,你真的不认识邱翎峰,也不知道他是谁?”
“不认识,”他有些不耐的说,“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从闵娴雅嘴里得知的,我跟他无任何交集和往来,这个回答可以吗?”
刘局不可思议的看着他,他轻轻的说了走了,正欲转身离去。
“令堂似乎跟他关系不一般。”刘局对着他的背影说。
他眉头一皱,脸色刹那间全黑,这句话好似晴天霹雳,轰得人措手不及,如果至今一切都在隐忍的范围中,那么这句话他绝不能容忍。
他在一秒之内转身,声音提高数度,有些失控的呵斥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家母已经过世多年,如果你再用这种毫无根据的话污蔑我的母亲,我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的。”
刘局递给他几张照片,“这是刚刚从令堂房间搜出来的,因为常年无人居住,照片有些受潮,照片上这个男人,就是邱翎峰。”
他一张一张的翻看,越看越慌乱,越看越不可思议,他多希望自己得了精神妄想,这些都是他的幻觉,然而那一张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全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庭远,邱翎峰一口咬定给你爸送过钱,很可能是污蔑,”刘局拍拍他的肩膀,“你的母亲很可能跟他有暧昧关系,甚至你的母亲跳楼,可能也和他有关。”
他不可置信的丢了照片,仿佛那些照片是一块块烫手的烙铁,他一边摇头一边后退,“这怎么可能,你开什么玩笑,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
“庭远,你听我说……。”
“我不听,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胡说八道!”他粗暴的打断他的话,“立刻道歉,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庭远你冷静点,”刘局知道一直对母亲怀有深深思念的他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于是尝试着拍拍他的肩膀,垂下眼帘,“你想想看,以你外公当年的势力和财富,为何对于女儿的死毫无怨怼,若我的女儿因为丈夫出轨而跳楼,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他的,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和反应。”
他拂下他的手,厌恶的与他保持距离,依然不可置信的摇摇头。
转身打了一辆出租飞也似的逃离这个地方。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人徘徊在马路边,冰冷的雪花落在他的脸颊,他没有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存在呼吸心跳。
一辈子的恨,凝结成炙热的火球,熊熊燃烧之后爆炸成碎片,体无完肤的痛。
脑海中回想起刚才的一幕一幕。
“先生,你要去哪里?”出租车司机关切的询问着一脸惨白的他和魂不守舍的模样。
他说,“去西城路那边,我要去找一个人。”
“喔,西城路好啊,”司机絮絮叨叨的安慰他,“那里环境清幽绿化也搞得好,最近房价也大涨,买那里的人都成百万富翁了……”
他对司机的话置若罔闻,好似疯了一样,凭借着记忆中寻觅着一处有着腊梅花香的楼房。
多年前八卦杂志上刊登的花边新闻他记得很清楚,虽然多年不曾考证过。
“谁啊?”一身睡衣的女主人打开门,看着他半响,“你是……”
“我是温庭远,温延明的儿子,”他简短的介绍自己,试探着问,“你不会陌生吧?”
女主人连连点头,“是温书记的儿子,我当然不会陌生的,请进。”
“不了,我就问一句,你跟我父亲是什么关系?”他打断她的话,简明扼要的问。
女主人愣了半响,抿了抿嘴唇。
“十多年前城北的矿井塌方,我是众多遇难者家属之一,”她自我介绍,“温书记关心我们,常常带人上门拜访嘘寒问暖的,又是送生活补助,又是送赔偿款,我们所有的家属都得到了很多的赔偿,那时我带着孩子,生活很困难,经常找你的父亲借钱,就是这样。。”
“是么?”他冷冷的看着她。
“你以为我是骗你的么?”妇女见他一脸疑惑,转身饱了一个木盒子,“这些都是我当年的借据,不止是我,还有很多旷工家属找他借过钱,温书记很慷慨,几乎不会拒绝我们,这几年条件好了,我曾上门找过他还钱,他也不要,说自己工作忙没有花钱的地方。”
他这才知道,他曾说的自己会做一个为百姓全心全意服务的好官,并不是他所认为的空口白话。
妇女以为他是为了父亲犯事而来,于是安慰着他,“温书记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别担心,我们已经团结起来要去北京上访,这件事已经推选出人办理,我们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人民的好官保出来,我们全城的老百姓都支持他。”
他却转身,颓然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