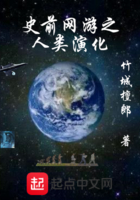我是肖肖。
从小,我奶奶就说我像老鼠,因为不管她把好吃的藏哪旮旯儿,我都能轻易地找到。我妈也说我像老鼠,因为我白天嗜睡委靡不振,一到晚上就精神抖擞。后来我大学时的男朋友也说我像老鼠,因为我吃东西的时候,抓食物的速度和嘴巴动的频率比别人快很多倍。
凡是在雷电交加暴雨如注的晚上,我就会趴在被窝里幻想我那关于老鼠的身世之谜。而且只有这样恶劣的天气,才能给我的身世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只手握大权德高望重的母老鼠精,在万鼠的翘首期盼下,生下了一窝,不是,是一只鼠公主。鼠公主聪慧机智思维敏捷有勇有谋动作利索,这些特质表现在外出觅食时的准确性和防备灭鼠器的警觉性。这么优秀的鼠才,当然在鼠界颇受鼠辈们的瞩目和赞赏……
我做这样的梦,无非也就是弥补一下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落魄。我在人堆里混不出个人模狗样,总允许我意淫下在鼠辈里的牛掰地位吧?
我吧,大学毕业也好几个年头了,换了N多份工作,至今没有一份是稳定的。跟一姐妹在城西租了间20世纪90年代初建的老公寓,两室一厅,一人一间。
这姐妹叫谭文,我大学舍友。她跟我有点区别,她是整一无业游民。不同的是她有个中年男人包养她,动不动就给她卡上汇个三万五万,完了还要叮嘱她“千万不要省,别亏待了自己。”
我跟她后面也有沾光的份啊,比如当我吃不上方便面的时候,她会非常慷慨地从楼下小卖部给我抱一箱回来。当我在外面连坐公交的钱都没有的时候,可以直接打车到楼下,让她下楼付钱给司机。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她挺过意不去的。有阵子,我尽量不想去麻烦她。不料这娘们居然跟我发飙,“肖肖!怎么着?不把我当姐妹啊,跟我还客气?!你要跟我见外,我们就散伙!”她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她的这句话,居然助长了我对她以后持续的不间断的战略搜刮。日后好几次,她都哀声怨道后悔莫及恨不得时光倒流收回她意气用事之下抛出的那豪言壮语。
我常问她,“那个中年男人还想包养人不?你看我行不行?”
她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个遍,“看在咱们姐妹情深的分上,我回头帮你问问。”
“好好~记着多夸我两句啊。”
“这个……看心情吧。”
“我打不死你!死婆娘!”
对了,包养谭文的人是她老爹。
一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跟谭文都是里面穿个睡衣睡裤,外面套个长羽绒服,哆哆嗦嗦地下楼去路边的夜宵摊吃烧烤。
点完菜,我们坐定后,我冲着老板喊:“老板,先给我们来两瓶啤酒。”
“什么?这么冷的天还喝啤酒?”谭文瞪大眼睛看着我。
“那你还要喝白的不成?”
“行行行,就啤酒。”
我最喜欢冬天在路边吃烧烤喝啤酒的感觉了,怎一个惬意了得。不去想用炭烤过的东西是不是致癌,吃夜宵会不会不健康,小摊贩的东西干不干净,喝啤酒有没有啤酒肚,在路边吃东西文不文雅……
谭文虽然家境富裕,但是用她的话说,她爸就是一暴发户,她就是一暴发户的女儿,没啥形象和格调要注重。
正当我在尽情地啃烤玉米的时候,我口袋里那该死的手机响了。
“文文,帮我拿下手机。”我起身把放手机的那侧口袋凑到她面前,同时两只手依然抱着玉米在啃。如想见当时具体形象生动的景象,请参考老鼠啃玉米。
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说:“是你初恋。”便按了接听键,把手机放到我耳边。
她说的我的初恋,就是清晓。
清晓,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我的初恋。高中时代,我俩以上课偷偷传纸条为前期思想准备和酝酿,之后展开了老师家长深恶痛绝严厉打压的早恋运动。而后,此运动由于革命者的意志和信仰不够坚定而在萌芽状态就被迫中断。之所以称之为“萌芽”,是因为作为这场运动的革命者,我跟清晓,从头到尾连亲历“战场”的机会都没等得到,哪怕牵一牵小手打个小啵都没有,更别提那伟大崇高的“献身”了。
之后,我俩成了比朋友还要好一点的朋友,一直到现在。他有个谈了六年的女朋友,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听说在另一个城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当女主播。
“喂~找我什么事儿?”
“你现在在哪呢?”
“在我家楼下吃夜宵。怎么了?”
“好,我们马上到。你等着啊。”
“什么?!现在?还有谁?”
“我,方远,还有我一个大学同学。好了,我挂了。”
“清晓和方远一会儿来这。”我告诉谭文。
谭文耸耸肩,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她已经习惯了我那群朋友不请自来。有一次半夜三四点,他俩满身酒气摇摇晃晃地来到我们家,吐得我们客厅一地的秽物,害得我跟谭文收拾到天亮。他俩可好,吐完之后,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谭文身上有很多我很欣赏的东西。她真实,包容,低调,坦荡,不虚荣。她从来表里如一,不八卦,不背后说人闲话。她包容我的大大咧咧丢三落四,包容我生活中的许多不良习惯,甚至包容我朋友的“胡作非为”。她有着买各种奢侈品的能力,但从来都不追逐。她可以从容淡定地拎个五十块的包跟她那帮富小姐朋友们一起逛完LV逛香奈儿。
她把她爸给她的大部分钱都存了起来。她说她随时都做好了她爸破产的准备。她常挂嘴边的话是:两万块的包不能带给我任何安全感,但是两万块的存折就不一样。
“我们就穿成这样?”谭文指指我的衣服。
我这才意识到我俩还都是穿的睡衣加羽绒服,“哎呀,我都忘了。走走走,上楼换。”
我们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我被人叫住了。“肖肖~我们来了~”天呐,我一听这语气,就知道清晓肯定喝过酒了。
我转身望去,清晓已经站在车门旁,一只手扶着他那辆二手的第六代银色雅阁,一只手对着我不停地挥舞。
“算了,换不了了,就这样吧。”我对谭文说完,便双手插在外套口袋向他们走去。
随即看到方远也从副驾驶室下来,接着后座也下来一人,距离太远,看不清脸,只感觉体积是比较占空间的那种。
我走到清晓面前,“走,跟我们一起吃吧。”闻到了清晓满身的酒味和烟味。
“行~来来,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田大山!”他招呼那人过来。
“你好。我叫肖肖。”我伸出手。
“你好。幸会幸会,久闻你大名了,今天才有机会见你真身。”他也伸出手,眼睛迅速扫了一下我全身。我肯定:他看到了我羽绒服下露出的半截蓝色睡裤。
这时候我也看清了他的脸,五官被脸上又白又嫩的肉挤得差点没被憋死的样子,眼睛鼻子嘴巴个个都显得特憋屈。以至他笑着跟我握手的时候,我一直在研究他脸上的五官能不能自如地跟上他情绪的表达和情感的流露。事实证明,完全不能。
当然,我这样形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似乎很不礼貌,但这确实是田大山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把他们领到我跟谭文坐的那桌。
“这是我大学同学,谭文。”我向田大山介绍。
“你好。我叫田大山。”田大山自我介绍道。
谭文对他微微点了下头,淡淡地回了声:“你好。”
“你们还要吃点什么,我帮你们点。”我问他们仨。
“不用了,我们刚吃完。”方远说。
“那你们来干吗?!”我白了他一眼。
“老板,给我们来一箱啤酒。”清晓抬起胳膊对老板招手。
“你不要命啦,已经喝了这么多,还喝?你怎么开车回去啊?!”我把清晓胳膊摁了下去。
“没事没事,我少喝点,你们多喝点。”
“你们俩怎么穿成这样就下来?”方远看着我和谭文笑。
“就下楼吃个夜宵,没必要梳妆打扮吧,黑灯瞎火的,谁看得见。”我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方远这小子,属于被迫奉子成婚一族,现在有个一岁半的女儿。当年我还在一广告公司勤勤恳恳埋头写策划案,一个加班的午夜,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结婚了,下个周末。我听到这个消息,震惊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当然除了震惊,我更多的是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