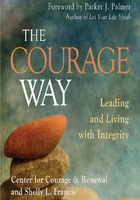第二日清早,天色尚昏蒙,恩同便听见外头一片嘈杂之声。
她蹙眉,忍着腰部酸痛想要起身查看究竟之时,房门被从外大力推开,一个穿青衫的修长人影快步走了进来。
当暮隐看清恩同的表情,急忙奔到床前,探手搁在她额头,只觉触手冰凉,并非感染风寒,便问:“恩同,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么?”
恩同尽力忍住痛楚,笑了笑,说,“腰好酸。”
暮隐赶紧坐在床边,将她搂在自己怀中,不满地说:“定是你昨晚不顾身体,步行来王宫才会如此。宅子里备有马车,你却不使唤。”
恩同坐直身体,深看着他,说,“若是我用了马车,管事的必定会将我来王宫一事告诉你。”
“难道你出来竟不许我知道么?”暮隐挑起眉。
“这件事是不许的,否则你会阻止我。”她淡淡地说。
暮隐眉间的褶皱更深:“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事?需要如此保密。”
恩同刚想说话,有一道柔和的声音先于她响起。他们太专注于彼此,以致未能发觉王后到来。
她说:“是那个宫女的事。听说你给她取了个名字。皎月,听起来好过从前的。”
暮隐赶紧起身对红玉行礼,说,“王后的意思,是说恩同昨晚前来王宫并彻夜未归,是与皎月有关?”
“没错。”恩同忽然开口:“我并不需要她在身旁,所以来恳请师父收回旨意。”
“那么,”暮隐转身看向恩同,“王兄答应了么?”
恩同摇头:“师父昨日忙于国事,我尚未得见。”
“于是你便在王宫中住下,定要等到王兄,将皎月赶出宅子才肯罢休?”
任谁,都可听出暮隐声音中潜藏的怒意。
恩同闭了闭眼,平缓骤然跳乱的心脏,再睁开时,只剩一片清澈的安静,若仔细辨别,尚能在她清澈眼中寻到极力压制的悲伤颜色。“是的。”她说。
“我不懂。”暮隐摇头,“皎月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坚持这样做?难道就因为她给我送了一餐饭么?”
恩同仿佛陌路般看着他。要她怎样说出口,她怀疑皎月来意不善,更重要,是她看出他对皎月有了痴迷,不愿皎月这样的女子分薄他对她的爱。想到这里,恩同悚然心惊,原来她已如此在乎他,竟作出妒妇一般可鄙的行为。她不是该全心全意爱慕着师父吗,会与暮隐成婚,多半是因情势所逼而他又喜爱她。
她敛下眼,努力回想废隐山上凝望师父挺拔背影的时光,却只有模糊的一片苍白,又在这苍茫的白之中,渐渐生出清晰的面目,有分明轮廓、一双如桃花潋滟的眼,微带着邪气的笑容,身形颀长、喜穿青衫……一切想与凝望,只属于暮隐。
“随你。皎月留或不留,但凭你做主。”恩同听到自己说,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另一个时空,虚渺得令人恐惧。
室内静默良久。
是暮隐先开口,“这些家事,回去再做决定不迟。”
于是恩同便跟在暮隐身后,坐上他驶来的马车,离开王宫。
马车行出不远,恩同忽然心有所感,掀开帘幕向后望,见高高的宫墙之下站着两个人。是师父与王后红玉,他们比肩携手,仿佛这世间最深情的一对璧人。
恩同放下帘幕,将他们身影隔绝在外,闭上眼,努力思索师父昨日的避而不见与此刻现身究竟意味着什么——皎月是师父派来的人,以他缜密心思绝无可能不知皎月在怡王宅中种种行事,然而明里暗里,她从未见到皎月受到责难与阻挠,难道皎月刻意亲近暮隐,是出自师父授意?
她的心因想到此处而跳乱了一下,脑海中那些原本各自断裂的线索却渐至清晰:临下山前匆促一瞥的家杂乱无章,原以为那些黑衣人寻不到自己泄愤,现在想来有极大可能是在寻找某样东西;后来在竹林偷袭自己的黑衣人既能在暮隐手中假死逃命,武功定然不弱,可见对自己并未狠下杀手,此番用意该是留活口。还有,来到惊鸿城之时师父对暮隐说过的话,‘若你办妥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我便正式封赏你’,隔日,暮隐便在朝堂之上受封怡王。师父再怎样看重自己,也不至如此程度……恩同的小腹突然袭来一阵抽痛,她知是自己耗费精力太多,便停下思考,静静调匀内息。
他们回到宅中不久,便有人来传惜夫人的话,要恩同前去相见。本已疲累非常的恩同只得换上得体装束,往惜夫人居住的院落而去。
恩同到得惜夫人房内,后者便挥手令服侍的丫鬟们退下,再来眉开眼笑地看着她,细细询问近些时日身子如何,又说怀孕一事确实辛苦,要她多忍着些,待孩子生下来便可无忧。惜夫人如此殷切叮咛,令恩同颇有些不适,却也只能沉默聆听。
“来,过来母亲身边。”惜夫人拍着身下的软榻,示意恩同靠近些。
恩同便走到软榻边坐下。
惜夫人笑着握住她一只手,说:“女人家怀孕的时候,情绪总有些波动,我会告诉暮隐多忍耐些,免得惹你气恼。”顿了顿,又说,“我听那些多嘴的下人说,昨儿个晚上你和暮隐在书房吵了一架?”
恩同不语,只在暗地里冷笑,啰嗦了这样久,总算转入正题。
“暮隐是什么性子,你这为人妻的总该比我这老太婆清楚吧。他就是那么个风流浪荡的德行,不管我怎样苦心教诲仍是不肯悔改,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本以为给他娶了你这么个好姑母亲,该收敛些了,谁知道来了个貌美的宫女,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一天到晚找机会往人家跟前凑,把咱们王族的脸都丢尽了!”
惜夫人说到这里,一只手抚上胸口,似乎因怒气而呼吸不顺。
恩同便劝她平顺心情,不必因小事动气。
好一会儿,惜夫人继续说:“无论如何,暮隐总归是怡王的尊贵身份,又是你的至亲丈夫,就算不顾身份,你也得顾及夫妻情分不是,要我说,他想怎么样,就随他去吧。男人的心,从来都是不定的。”
恩同笑了笑,“母亲有话不妨直说。”
虽已习惯了恩同冷然性情,惜夫人仍是一愣,不由得暗暗诅咒一声,才重新挂起微笑,说道:“我的意思很简单。既然暮隐喜欢那个宫女,不如就将她收为夫人。你们夫妻二人从此就不必因她而吵闹,丢了怡王脸面。”
恩同真恨不得自己在瞬间眼盲耳聋,不必面对惜夫人微笑底下的不怀好意,亦不必听闻暮隐将要娶皎月为妻。然而她只能乖顺地点头,说:“全凭母亲做主。”
在这诺大宅邸中,从前她尚有暮隐的专注,而今他与从未喜爱自己的惜夫人一样,站到了她的世界之外。恩同不知自己是怎样向惜夫人告退,回到遥望楼卧房中的,放眼望去,只觉处处冰冷陌生,仿佛从未来过。正在此时,她感到腹中胎儿动了一下,立时惊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很快,胎儿又动了一下,她赶忙将手放在小腹,那里却安静了下来。恩同等了许久,却不再有跳动迹象,她心中着急,眼泪竟落了下来。
丫鬟阡陌走进房时,见到的便是恩同低头垂泪的模样,她眼光一闪,急忙上前,“怡王妃,您怎么了?可是出了什么事?”
恩同抬起满是泪痕的苍白脸孔,哽咽地说:“没什么。”
久候不至的胎动于此时再次出现,恩同便叫了出来,“是孩子在动!”
“恭喜怡王妃,看来小公子健康得很。您不必为此担忧。”
恩同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却因衬着斑驳泪痕而显得委屈到极处。
第二日,恩同刚起床便听说暮隐带同皎月外出打猎,也许三天归来,也许更久。
这话是翎羽从管事的那儿听来再转述给恩同的。
恩同彷如不闻,只说,“去厨房看看早点做好没,我肚子有些饿了。”
待翎羽端了早点回来,恩同便坐下来静静地吃,豆沙包就着茶水,一口一口吞下去,像在吞咽未曾流出的眼泪。她心中明白暮隐是要以此举表明定要迎娶皎月的态度,这其中自然不会缺了惜夫人的怂恿,说不定打猎一事就是她给出的主意。可她已无力去争求什么,对于从未善待过自己的命运,她选择束手就擒。
暮隐直至第五天头上才归来。第一件事是探望惜夫人,而后才回到遥望楼。
其时天色已晚,恩同用过晚饭,正点着一支蜡烛在桌旁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