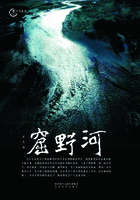包爷不断旋转自己的脖子以适应被自己不断调转的地图方位,他从抽屉里把指南针掏了出来。只见他锁定位置后,又在上面比划了一会儿,手指竟然还掐算了几圈。突然他把手拍在地图上说:“这才对!”随后又突然说,“不对不对,反了,怎么反了?”我赶忙凑过去,他试图解释又似乎不知道怎么向我这个白痴解释,直接把墙上的一张星相图摘下来摆在地图上方,之后上北下南地跟我解释一通,我才大概听明白。原来,那四个物件沿着临近经纬线构成的那把短刀形状,在我说的这个日子、时间段,按照天象推测,短刀形状的坐标图的“刀把”一端正直指天狼星所在的位置。之所以是刀把直指天狼星,而不是刀尖直指天狼星,按照包爷的推测是,当年匈奴敬畏天狼星,并无意与其为敌,相反更希望得到它的庇护。冒顿走后,他寄希望于天狼星能给他的子孙以守候,便有意安排将自己墓穴的“刀把”一端交由天狼星,由天狼星指引,刀锋利刃直指疆域之外。
我听得有些玄乎,但我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包爷定是信了我的话。趁着热乎劲儿,我适时开口道:“我们这边都是穷小子,准备了家什后,就没啥银子了。这大老远的,总不能赤脚跑去吧,所以,包爷那悍马能不能借我用用……”见他似乎没啥明显的反应,一副装聋作哑的态度,我忙继续说,“东西出来后,全部由包爷这边出手。”
即使我把底牌都放出来了,他还是没怎么答理我。他的心思似乎正被这地图和木牌吸引着,听我说了这么一堆也只是敷衍一笑。
包爷又在那地图和木牌上研究了一阵,直起身后,他挑着眼睛在我脸上看着,看得我心里头有些发毛。包爷咧开嘴角冲我“嘿嘿”一笑,说道:“臭小子,你有事瞒我。”
也不知是因为自己说谎心虚,还是因为包爷这老东西太过老辣,听他这么一说,我顿觉脸蛋儿上火烧火燎地烫了起来。我有意装出没被他猜中,嘻嘻哈哈地笑着说:“包爷您净说笑,我能瞒您啥。再说,也瞒不住呀!”
包爷似乎在确认之前的话,问道:“那什么高人和你讲的,墓地是在这个比例尺地图里显示不出来的低山丘陵里?”
我记得方才这么讲过,虽然已经意识到包爷可能从中发现了漏洞,但还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表现出一副笃定的样子。
包爷又是“嘿嘿”一笑:“你小子呀,和包爷耍心眼儿!”随后他把地图铺在我面前,和我闲扯了几句地理知识,又是比例尺又是地质地貌的,我也听得不太懂,笑着说教我地理的那些狗屁老师都是吃屎的。
随后包爷又一面在地图上比划,一面解释说:“假设我之前猜测得没错,让刀把直指天狼星,这个刀把要在这个位置,向地下深入大约20米。这不是瞎说,我在一个古物件上见过相关记载,只是说得比这含蓄。”他转而说道,“和包爷说实话。”
我前后想了想,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倒不如索性把整件事讲给他听。
我讲这些的时候,还有意照顾包爷的情绪,生怕他听完觉得我是在瞎掰。可包爷非但没表现出任何疑问或者诧异,反倒越听越兴奋。
我说完大概情况后总结道:“包爷你看,这悍马借我们用用?”包爷竟然拍着我肩膀说:“小印,你这命都快没了,你说包爷我能袖手旁观吗?甭说那一台破车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借你拿去用了!”
我一听这话,问道:“怎么,包爷的意思是?”
包爷笑道:“咱一起走一趟!怎么,不欢迎我这老骨头?”我还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包爷爽快地说道,“开我的车过去,我另外再拿出5万块,买装备、一路花销都从里面出。”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美极了,转到门外给欧阳打电话,和他商量了一下,他正和郑纲在一起,已经把事情原委和郑纲聊了,郑纲虽然并不是很相信这是真的,但他却很有兴趣陪我们走一趟,就当是出去透透气了。对于包爷的参加,他们俩没有异议,一切听我安排。
随后我们四人碰在了一起,准备先开一个临时的小会议。我本来还有些担心,怕郑纲和包爷这俩强悍的陌生人会起冲突,但这俩人竟然相聊甚欢。我们定在当天晚上上路,包爷和郑纲各自回家简单准备去了,晚上约在欧阳的健身馆里集合。
我对户外的装备不太熟悉,这些主要由欧阳来处理。例如帐篷、背包、坐标仪、睡袋、炊具、备用粮食、刀、小急救箱之类,欧阳准备了一堆。
有欧阳在,我省心多了。我只顾着把短刀用欧阳拿来的贴身软背包装好,用硬纸卡片记下木牌上的坐标以备不时之需,并把木牌、假手机、圆盘这几样重要的东西和短刀放在了一起。坐标仪我担心会随时用到,就随着其他东西放在我身上的大包里。欧阳又给我们准备了“假枪”,万一遇上什么强悍的对手,兴许能救命用。我和欧阳本来想把计划做得周全一点,但一时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我除了猫在电脑前查内蒙古那边的各种资料,就是和他闲扯。偶尔会在网上和“花瓶”闲聊一会儿,以缓解近日来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
夜色铺展开来,我们坐着包爷那豪华的大悍马上路了。
我们出发时是晚上9点左右,第二天清晨5点多就到了指定地点——欧阳在锡林郭勒的朋友家楼下。因为事先没有电话约定具体时间,到那儿后,欧阳硬是打电话把那哥们儿从被窝里叫了起来。我们上楼时,那哥们儿的媳妇还没起床。赶了一夜路,因为轮班开车倒都不至于太困,但一路上谁也没吃干粮,肚子应该都有些饿了。那哥们儿去卧室把他媳妇揪起来,让我们大吃了一顿手扒肉,我又喝了两大碗马奶酒。我们几个只有郑纲不喝酒,说是沾酒就醉,因为不太熟识,也不好硬劝。虽然今天我们只是想去探探路子,但为了避人耳目,还是要等到晚上再出发比较安全。大伙儿大致计算了下车程,在那哥们儿家逗留了多半天,之后才继续赶路。
我们要找的地方,应该在锡林郭勒盟行政区域内的正镶白旗附近。
从那哥们儿家楼上下来,我们正准备上路,可包爷这车说什么也打不着火。油箱里的油来前加得满满的,估计是哪个小部件出了毛病。后来想起这事,总觉得是附着在“天脐”上的匈奴王密咒给予我们的警示。在这么个地方,悍马零件一时半会儿肯定是配不到了。我心里大为郁闷,早知道这样,干脆让欧阳开着他那个破越野了。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让欧阳的哥们儿临时借了辆小车先送我们到正镶白旗,帮我们安排好了招待所后,再开着车返回家跪搓衣板去。那哥们儿临走还不忘提醒我们:“你们玩归玩,可别乱逛,据几个酒友说正镶白旗再偏南方向有一块天然草场,之前来过一些外国人,乔装成来旅游的,但都开着大车,一看也太不像。据当地人说,活着回去的不到一半,另一半都不知道死在哪儿了。”我一听有些好奇,问他具体位置在哪儿,他却不好意思地挠头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喝酒打屁时闲扯的谈资罢了。
出发前我简单了解过,这正镶白旗历史悠久,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是游牧部落活动的地区。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地方挺神秘,有历史的地方都神秘。
到招待所后,我们暂时安顿了下来。
我把地图摊开,又把那个地理坐标指示仪器拿出来,确定了此时所在的具体位置。之后,我量了一下距离目的地的大概长度,按照地图比例尺计算,目的地离我们现在的径直距离怎么也有100千米左右。这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用什么交通工具,着实有点棘手。欧阳的那哥们儿也走了,就算没走,他也是人生地不熟,因为之前他是在北京办假证的,去年认识了这里的一个女人,才在这里暂时安定了下来。说实话,身处异地,又是富有诸多神秘传说的异地,我的心一直悬着。要是在荒郊野外过夜,再遇上什么野狼啊、异域怪物啊之类的,我们这些小命岂不是难保了?刚进招待所的时候,我留意到吧台上立着“24小时低价导游”的牌子,雇一个导游领着我们过去,应该能省不少力。
他们几个在屋子里检查装备,我噔噔噔下楼去找导游,边走边摸了摸背在衣服里面的小背包,临出门前欧阳就叮嘱过我,这东西随时都要带在身上。
我到前台花了100块钱雇了一个当地的土导游,又被前台的胖女人要了20块钱的“介绍费”。胖女人让我在一旁等一会儿,她粗声大气地打了一个电话。不消五分钟,就见一个穿着蒙古族服饰的中年小个子男人走了进来。胖女人抓了块奶酪扔在嘴里,用鼻孔喷出:“就是他了。”我打量了一下,看样子是个老实人,属于那种当地常住百姓为了谋生计赚外快的类型。彼此招呼后,我把他叫到一旁,借口说我们一个伙伴的前妻是唱戏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伙伴最恨的就是前妻唱戏时穿的民族服装,曾经让他癫狂,土导游现在穿成这样,有可能引发他的精神病。我说要麻烦他去换一套普通的衣服来,实际上我是不想我们的出行因为他的服饰而变得太过惹眼。他说他家住在星耀镇上的永明村,挺远的,他这就要回家去换。我一听,直接塞给他200块钱,让他赶紧去最近的店里迅速买一身衣服,买好后到招待所来找我们。
上楼后,我刚推开房门,就被一股蛮力给扯了进去,随后满是老茧的大手便捂住了我的嘴,我正要挣扎却听欧阳把食指搭在嘴边嘘了一声,小声提醒我道:“有尾巴。”
见我老实下来,捂着我嘴巴的大手才拿开,原来捂我的是郑纲。此时郑纲把耳朵贴在墙上,我心里正琢磨着是不是那个导游跟了过来,可没等我质疑,欧阳却低声说:“是个女的,你上楼时,郑纲就觉察到有人步调与你一致。”
这时,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刻意放轻脚步的意思,当我们都以为是郑纲太过敏感,纷纷放松了警惕时,那脚步声竟然在门外停了下来。
刚放松下来的几个人,再一次紧张起来,郑纲最为迅猛,直接闪身到了门旁。
这时外面竟然响起了笃笃声,好像是穿着高跟鞋跺脚的声音。我和欧阳面面相觑,这状况似乎有点离奇。方才还是正常的板鞋摩擦地面的声音,这会儿怎么变成了高跟鞋的声音?
就在接下来的瞬间,我们听见啪的一声,房门应声被外面的人踹开,几乎与此同时,郑纲就地一个翻身,一把抱住了踢门尚未来得及收回去的一条雪白的大腿。
白腿的主人“妈呀”一声应声倒地,愣是摔了一个大屁蹲。随着她倒地,粉色裙摆下面的红色小内裤便进入我的眼,同时我也看清了那人的脸蛋儿。
郑纲顺手闪出匕首,正翻身要向那人脖子上架去,被我连声阻止:“自己人!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