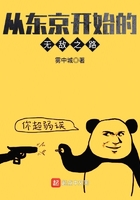我们都叫他妖。很多叫他妖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妖是画家,他的笔名就叫妖。妖是我们上海街上有史以来第一位画家。我们上海街有1500米长,出过流氓,出过教师工程师,也出过官员。这个官员现在任我们玫瑰市的副市长,不过,他早就不回我们上海街住了。他家里的老房子旧城改造后由他的一个兄弟继承,好像他也从不来看望他的兄弟。他兄弟说,他忙啊!他有办不完的事,喝不完的酒。旁边那人插话说,还有弄不完的女人吧?他兄弟白了那人一眼,说,滚。有本事你也当市长去呀。
当然我们不想过多去谈论我们的副市长,他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妖呢,这个名字我叫了四十年了,好像我一能说话就叫他妖了,我们差不多同龄。无论我在哪里上学,我都忘不了他。妖,妖,妖,我的耳朵里时常响起他的大名。除了在外求学的四年,我基本上住在上海街。旧城改造之后,上海街相当现代化了,我们都住上了楼房。妖家里的老房是全街上最大的,所以得到的补偿也是最大。他的房子在六七楼,是复式楼。画家通常需要大房子,在大房子里他们才能有作画的活动空间。妖的房子大,画作多,可是据说,他的画并不值钱,或者换个说法,他的画几乎没人要。傻子都能看出来,他的画能有人要吗?色彩灰暗,主题不明。有一回我在外面应酬,桌上有位画家,据说是市里的名画家。他的画,玫瑰市里所有地产大亨政府官员以及收藏爱好者都收藏有。看他那派头,一定过得很滋润。完全不像妖。妖除了有一套父母留下的大房子,日子过得十分清贫。他是有工作的,但是他没有好好表现,心思都放在画画上了,单位领导很不喜欢他,经常给他穿小鞋。
有一次领导大怒说,画画也就算了,你能不能把画画得漂亮些,我们拿回家挂在墙上也能美化环境啊。可你,什么破画,收破烂的都嫌脏。妖被激怒了,把领导打得鼻青脸肿,然后操了一顿娘后回家了。他不上班,银行卡里却总有每月按时打来的基本工资。靠着这点工资,妖生存着画着。关于这一点,我也同意他领导的观点。画家作画不美,哪有市场。画家是人类的美丽使者,他们应该捕捉到人世间最美的东西,然后把它传递给人们。妖时不时地邀我去他家看画,我是不懂画的,但是美不美我还是看得出的。你看看,妖的画,黑乎乎的脏兮兮的,什么意思?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说,以后你不要再叫我来欣赏你的画,你的画我不喜欢。妖并没有生气,他轻轻地笑着,拍拍我的肩。他说,你因为不懂画,因为我们是穿开裆长大的发小,我不会生你的气。你说的画的那种美,我也能做得到。妖打开一个柜子,从里拿出一些画来。这是些山水画,很美;也还有人物画,男子健康女子美丽。
可是,画家,他说,同样有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职责。人间本来是美好的,事实上人类很多情况下借口创造美好,却最大程度地破坏美好。他把这些充满着阳光般美丽的画作收起来。我看到他放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两幅画作。应该画的是同一地方,对,想起来了,是方庄。方庄原来在野外,现在那里是人们周末的娱乐地。前一周末我还去过,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早先那条小河已经断流,现在流着的是生活污水。妖这两幅摄影作品一般的作品,确实令人为方庄曾有过的纯净感到惋惜。妖说,要是这两张作品由你挑选你肯定会挑早年的方庄。我说,没错,因为她很美,令人向往。妖说,那么我和那些粉饰太平的画家相比,我不是更优秀吗?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画是艺术品,艺术总是高于生活的。艺术正因为它的缥缈,甚至虚无才为人类所追求。他最“雷人”的画是一幅城街图,所有的高楼大厦都是变形的,行人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像个怪物,有的则外露着内脏。我说,你这样的画怎么能受到读者的喜爱?他们要是买你这些画回家挂着,会天天做噩梦。
在饭桌上我坐在名画家的右侧,我们聊得比较投入。我对他说,我认识妖,我们是街友,自小一起长大。名画家说,哦。我说,你如何评价妖的作品?名画家说,妖是有才华的,但是他剑走偏锋。妖的画比较阴暗,说明他内心也是阴暗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有心里阳光了,他笔下的画才会阳光艳丽。我说,也许你们把这个世界看得过于美好呢?或者你们不敢面对现实,都在以自欺欺人的方式逃避社会呢?名画家吃惊地看着我,然后说,画家就是画家,不是杂文家时评家,也不是政治家。捕捉美,是画家的基本生存方式。但是如何捕捉美表现美,那就是一个人的艺术修养问题了。
提起妖,特别是我刺激了名画家后,他就把脸转向他的那个邻居。那个邻居是个马屁精,他将名画家从头赞美到脚。马屁精也可能是画家,好像刚才主人介绍过的。这一桌人除了主人,他们我都第一次认识,所以一时也记不住。这一群人都是文艺家,现在,他们开始大谈特谈艺术。我是学工科的,缺乏艺术修养。他们说的那些名人画作,我听得云里雾里。他们把敬酒的目标全对准名画家。名画家也回敬他们,最后名画家敬了一圈,就是没敬我。与这帮自以为是的人同桌吃饭,真的没意思。我提前告辞。主人说,怎么就走?主人很抱歉。主人对我如此看重,当然是有求于我。我拂袖而去,出了门我对送出来的主人说,以后不要把我和这帮什么狗屁画家、作家、诗人们搞在一起。主人说,是,是,是。
走出酒店,我脑子闪出了妖。从小到大我还没像今晚一样感觉妖可爱。小时候的妖死痞烂贱,还常偷居阿婆家的东西吃。回到上海街上,我爬上妖他们的楼。见敲门的是我妖大感意外。我的确没有主动去过他家,每次都是他极力相邀。童年伙伴们很少有与妖来往的,除了对他小时候的印象很坏,就是都认为,妖是一个窝囊的画家,是一个根本称不上画家的画家。
妖正在画着一个系列画,他没工夫搭理我。我就站在他身后看。这个系列中的这组画,应该是穿越我们玫瑰市的城市河,对,就是她。妖都写明了。
十数天后,妖把画着城市河的组画挂到上海街上去。这一组大约有二十来张。城市河在他笔下丑陋不堪,还有两岸的新建筑相互掐着。小时候,城市河两岸多宽啊,绿树小岛,还有荆棘丛林遍布,充满了野趣。现在都被房地产老板开发了,他们为能拿到沿江的土地明争暗斗,动用一切伎俩和才智。在争白宝岛这块地皮上,天宇房产公司败给了宏宇公司。可天宇公司最后却令人刮目相看地拿了到邻近城市河的白虎公园那块地。白虎公园要建楼盘了,报上久不久地有一整版广告告诉市民,快去抢购啊。广告这么说。这些房地产商美其名曰建设美好的家园,其实他们是最大的环境破坏者。以上这些话是妖说的,妖比较爱读书看报。对了,名画家那晚还说了,报纸上的东西怎么能信?现在的书上哪有什么值得读的东西?从他的话里就可以推测,他是不读书看报的,他只爱不停地作画,但他希望别人看他的书。他出过许许多多画册,写过许许多多美术理论文章,他希望每个活着的人都去买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