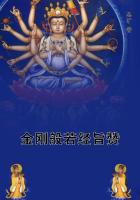东来累了,那种骨子里的累。他背靠竹竿坐下,两只光脚板搁在热乎乎的尿里,和着尿泥。他开始仔细观察身处的环境,四周空旷寂静,除了黑,还是黑。只要没坟就好,其他没什么好怕的。他又往竹竿上靠了靠,心里有了坚实的感觉。他仰起脑袋,眯缝眼睛瞅着灯泡,把眼前的黑夜想象成白天。他想象得出,如果是白天,如果再过几个月,这儿有多热闹。大人们忙于秋收,他们也很忙,忙着抓沟沟汊汊里的鱼,忙着挖开田埂,抓老鼠,抓蛇。他和黄毛都不怕蛇,有一次,他们逮到了一条草头蛇,他和黄毛轮换,提着蛇尾巴,大摇大摆在野地里走了好几圈。一路上,弟弟远远跟随他们,女人们看到他们手里的蛇,免不得尖叫一声。他们越发得意,弟弟也高兴得满脸通红。东来两手抱着膝盖,在想象中,慢慢勾下头,头垂到两腿之间,猛然一挣,他抬起头,两眼茫然。在这茫然里,东来看到脚脖子边,一段细细的丝线闪着光亮。
那是一根细铁线,东来认得这东西,是用来打老鼠的。铁线和电线相连,老鼠到田里糟蹋粮食,撞上了,就蹦跶不了了。有时候蹦跶不了的也不止老鼠,上个月还听说有人夜里到田边,撞在这铁线上,电死了。东来即刻明白头顶的灯泡派什么用场了。他听说,电死人后,再打老鼠的人家,就会在田边架个灯泡,给过路人提个醒。他湿淋淋的裤腿离铁线不到一拃远!他小心避着铁线,急急忙忙站起,脑海里蜂鸣着人们对上个月那个死者的描述,一张可怕的脸清晰地出现在他面前,上上下下毫无依傍,就那么一张孤独的脸,马青的脸。东来没有喊叫,没有逃跑,又眯起眼睛,抬头看灯泡,灯光也变得狰狞可怖了,朝他伸出尖利的爪子。四围的黑暗不再是寂静的,无数死者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朝他冲过来。东来一手拿着熄灭的电筒,一手拿着脏兮兮的拖鞋,恰似一手持矛一手持盾,两眼圆睁,绝望地站在茫茫夜空下疯狂的田野中。
东来彻底无路可逃了。
……东来是听到父亲的声音醒过来的。爹喊:“东来!”他睁开了一只眼,发现自己竟坐在灯光和黑暗的交界处,睡着了,仍一手电筒一手拖鞋。爹又喊:“东来!东来!”他另一只眼也睁开了。他懵懵懂懂的,怀疑自己是睡过去了,还是死了又活过来了。当爹再喊他时,他确信,他是死了,如今又活了。他不再是几个小时前的那个东来了,这时候他肮脏、衰弱、呆滞,对恐惧麻木不仁。他的两只眼睛空洞无物,灯光或者夜色都没在里面留下一点儿影子。他艰难地站起,面向小山,静着。爹的声音里分明含着愤怒了,喊声从小山传下来:“东来!东来!你死哪了?”他望见瘦瘦的月亮升高了,好似飘在水面的一片白羽毛,格外轻柔、耀眼,地上仍旧一片黢黑。蛙声又响起来了,倍加精神,好似冰凉翠绿的水滴灌进耳朵。他抬起那只攥着电筒的手,用手背擦眼睛,手背沾了热滚滚黏糊糊的泪水。爹的声音继续威严地传过来,他望着笼罩爹的黑暗,又换了另一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