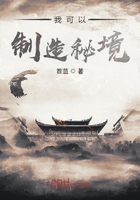所谓“大历十才子”是指在大历、贞元年间一度颇为活跃而成就却不甚高的一批诗人。这十人是谁众说不一,可见所谓“十才子”原是后人所加的笼统的归纳。依《新唐书·卢纶传》之说,则十人为钱起、卢纶、吉中率、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要对此十人的诗风加以总结当然很困难,大约说来,他们的诗一是酬唱应和之作较多,一是多通过描绘自然山水表现个人的心境;艺术上有向六朝尤其是二谢诗风回归的趋向,追求写景之句的清丽秀美、精巧雅致,而意象以偏于幽暗静谧的居多。
十人中钱起与不在此十人之列的郎士元生前颇有声名,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谓当时京中高官出掌地方要职,若无二人作诗送行,则“时论鄙之”。然而他们的诗实无性情。倒是卢纶的边塞诗较具个人特色,其中一部分富于雄浑之气,与盛唐的同类作品相近,如《和张仆射塞下曲》:而《逢病军人》则别有感人之处:
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来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
这是一个生命活力被统治者以国家名义榨取殆尽的士兵,如今哀吟于荒途,饥寒与战争留下的创伤横堵在他归乡的路上。它对社会的冷酷无情是有力的控诉。
顺带可以提到生活年代与上述诸人相仿的张继。他留下作品不多,但《枫桥夜泊》却是唐诗中传诵极广的名篇:
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中以丰富的意象组合成优美而富于含蕴的意境。可以注意到第一、二句各三组意象均是平列式的呈现,完全省略了表示语法关系的词语,从而达到使意象密集化的效果;但由于组合妥帖,读来仍是顺畅自然。
韦应物在大历、贞元间的诗坛上,韦应物(约737—约791)是一位重要诗人。他是长安人,出身贵族,少年时曾任玄宗的宫廷侍从,后任滁州、江州及苏州刺史,一生仕途大抵平顺。他的诗涉及范围颇广,或追忆自己少年时代任快放荡的生活和安史乱前的“盛世”景象,具有浓厚的伤感气息;或反映社会危乱及下层百姓的疾苦,表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他也受佛道思想影响,企慕一种淡泊脱俗、远离尘世的生活,每在诗中抒写向往田园山水的隐逸之趣。而其诗最为人称道的是后一种类型,白居易称“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与元九书》),司空图谓其诗“澄淡精致”(《与李生论诗书》),即由此而言。如《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诗虽是为怀念友人而作,然诗中那位道士孤高峻洁、飘逸无迹的世外生活,实是作者自身的心灵影像。韦氏自称他案牍盈前,却能和山僧一样,“出处似殊致,暄静两皆禅”(《赠琮公》),所以此时的怀人成了对另一个自我的怀恋。《滁州西洞》亦是他的名作: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鹏深树呜。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里所描绘的清幽空寂的自然景象,是从世俗生活的时间之链上解脱出来的孤立境界,它表达了一种幽邃的人生情怀。
韦应物是一位较早明确标榜慕效陶渊明之人格与诗风的诗人。其作品在题目上标明是学陶的就有十余首;同时他又在遣词用字上注意锤炼推敲,结合了大小谢山水诗的精致与明丽。其优秀之作大抵以意境的恬淡澄明、自然秀丽见长。
顾况、李益顾况(?—806以后)字逋翁,是大历年问一个较有特点的诗人。他为人性格刚傲,“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悔之”(《旧日唐书》本传),仕途上屡受挫折。但其诗在表达内心痛苦的同时,较之刘长卿更多几分倔强之气。
顾况豪放不羁的个性,也表现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皇甫浞在《顾况诗集序》里说他的诗“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稍仔细地说,顾况的古体歌行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想象丰富而奇特,而且常带有怪诞的意味;句式、节奏变化多端,如《范山人画山水歌》三、七、六、四言均有而且有时故意地写得不那么流畅,显得跳跃动荡;常夹杂俚俗化的口语,令人读来既亲切又陌生。这些特点当然有承袭前人的地方,但以上诸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诗歌的主观性更强,在当时的诗坛上显得颇为怪异不常。
李益(748—829)字君虞,在大历、贞元年间也是一位有特色的诗人。他少有才名,早年沉沦下僚,又曾五次在边地幕府任职,有漫长的军旅生活经历。五十多岁以后仕途顺达,最终以礼部尚书衔致仕。但其诗歌成就主要是在前期取得的。
李益是中唐最重要的边塞诗人。就气质来说,他的边塞诗虽也有少部分写得雄壮而豪迈的,但更多的是描述战争的惨酷,反映将士的凄苦心情,总体上与盛唐之作有了明显的不同。如《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在相当长的篇幅中以起伏动荡的节奏,诉说了战死者无穷的悲恨,而《夜上受降城闻笛》则以精悍的绝句形式,表现从军者厌战思乡之情: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从这一类诗篇里,可以看到在唐王朝衰乱的过程中,诗人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更为冷静。在李益的《过马嵬》诗中,还可以看到他对杨贵妃之死的清醒而富于正义感的评说: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孟郊、韩愈自德宗贞元后期始,以宪宗元和年间为中心,唐诗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其各方面的特点与初、盛唐诗的差异,更为明显,故诗史上有“元和诗风”之说。不过这一时期实有取向相反的两大诗派,一是孟郊、韩愈等人的奇崛险怪,一是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浅俗明畅。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而不得中,直到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又过了四年才当上溧阳尉,其后又担任过一些其他低微官职,元和九年得暴疾而死,可说是一生穷困潦倒。孟郊要比韩愈年长十七岁,他其实是所谓“韩孟”诗派的先驱。不过他们之间也有区别: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韩愈谓之“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盂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
孟郊诗以辞浅情深的短篇《游子吟》传诵最广,但这显然不是他的主导风格。他的诗首先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异常敏锐的感受和尖锐的方式表达穷寒之士对自身境遇和社会的不公平的愤怨之情。有些诗是从广阔的社会现象着眼的,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但像“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已包含了深刻的心理体验,非泛泛记述民间疾苦者可比。而在述写自身的孤独与悲哀时,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如《秋怀》之二:
秋月颜色水,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
诗表面上只是写秋日的自然景象,但在这里,风、月、露之类不仅是冰凉不可亲的,而且成为侵害生命的力量,周围的一切都带着威胁向人挤压过来。毫无疑问,这是诗人对他的生存环境的感受。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又同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基于此的性格上的敏感分不开。虽然杜甫也描写过自己困窘的生活,但总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对王朝命运的关心。对自我政治才能的期许)能使之有所化解,而这些因素在孟郊那里已经不存在了。
韩愈(768—824)字退之,或以其郡望称为韩昌黎,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贞元八年(792)中进土,贞元十八年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后两度因上书言事遭贬谪,穆宗时历任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要职。韩愈在中唐时期从多种意义上说都是重要的人物。在散文领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强调发挥文章的政治与道德功能,力图重建儒家思想对社会人心的统治;而在诗歌领域,他却以极大的才力把孟郊所开创的那种奇崛的诗风推向远为恣肆险怪、显示出极强悍的个人意志力量的境界,从而给古典诗歌的面貌带来显著改变。两者的趋向不同,但对当代及后世的文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而这种诗、文异趋的现象,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唐以后文学的复杂化。
韩愈身上的这种矛盾,和他的个性有关。他自视甚高,但直到晚年仕途顺达之前,人生经历却多坎坷艰难,而且据其自述,他的身体情况也很差。他一方面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一方面在官场中费力爬升(其《醉留东野》诗尝自嘲以“狡黠”得官),内心所积蓄的压力是很大的,这需要一个宣泄的途径。韩愈自称“多情伴酒杯,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这并非表明轻视诗歌,而是将之保留为从政、卫道之外的私人空间。也正因如此,他的诗写得格外自由;他的丰富的想象力、活跃的性格、激烈的内心冲突,都在诗歌中得到了表现。
至于韩愈诗歌最成功的地方,是以奇异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描绘出具有巨大力量感的、激烈冲荡的意境。司空图说其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而这种渴望着力与力的格斗的艺术趣味,正显示了诗人刚崛而不无乖张的性情。如《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写瀑布是:“是时新晴天井谥,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是:“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贞女峡》写江水是:“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至于《雉带箭》只是写围猎一头野鸡,竟然也紧张无比: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动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在这场围猎中,双方——将军和他所率领的军队与一头野鸡——的力量对比是远远不相称的,作者却仍要写出力与力的冲突,巧妙在于所有的力量不断凝聚,到了最后的瞬间才爆发。所以,尽管不过是杀一头野鸡,这却是一场强大的、决绝的、雷霆万钧的杀戮。这是一首非常感性的诗,诗中“蓄力”的过程是制造心理紧张的过程,这种紧张由于瞬间的宣泄而变为快感。
韩愈写诗好逞奇矜博,喜用生涩语词,好发议论,有的题材选择让人讨厌,都是可以批评的地方。但他是富于创造力的大诗人,有些毛病也是无妨的。宋代一些诗人没有他那样的才华,却去学这些东西,也就难免东施效颦之讥了。
当时在韩愈周围有一批诗人,如卢全、刘叉、贾岛、李贺等,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与韩愈、孟郊有一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声气相通,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李贺、贾岛等在韩愈周围的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李贺(790—816)。他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是皇家谱系很远的宗室,这种出身除了带来一点血统上的自豪,别无利益。因为父名“晋肃”,遂因需避讳而不得考与之谐音的“进士”,只当上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他家境困窘,身体病弱,其貌不扬,却是个敏感而早熟的天才,尤其容易感受到人生的不幸,最终仅二十七岁就怏怏而死。
李贺心中有过豪迈的理想,《南园》诗中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这种豪情畅想只是偶然地闪过,从他内心所感受到的世界的景象冷漠而恐怖、天昏地暗:“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他说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佩兰客”)陷入不幸,是因为“天畏遭衔啮。所以致之然”,也就是说凶恶的力量不仅胜过人,也胜过天。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但那些不幸的人们却也没有彻底被粉碎,他们的悲恨化为永恒的存在,如《秋来》所咏唱的: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总之,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是李贺诗的基调。
美丽的异性是李贺向慕的对象,而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则被李贺想象成一个脱离了时间因而也脱离了死亡之威胁的所在;在有关这两个主题的诗作中,就会较多地呈现或是艳丽或是恍惚迷离的美感。前者如《洛妹真珠》中美女的形象:“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寒鬓斜钗玉燕光,高楼唱月敲悬珰。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花袍白马不归来,浓蛾叠柳香唇醉。”后者如《梦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目光,鸾王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但这些诗中仍是有阴影的。李贺写男女欢爱,总是被什么力量阻隔、破坏;写永恒的仙界,其实是因为不能忘记凡世的一切脆薄易碎。他清楚地知道他追逐的只是美丽的幻影。
贾岛(779—843)字浪仙,早年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应进士试,但一直未中。做过长江主簿等低级官职。他的生活颇为潦倒,诗中诉穷说愁之处甚多。不过中唐诗中这种情况很普遍,这和诗歌本身的变化也有关。
贾岛虽然和韩愈的关系颇密近,但诗风已经相去较远。从诗体说,他喜好并擅长五律,而五律的一般特点是均衡、平稳、精致;他的诗歌题材大抵出于日常生活经验范围,很少想人非非;他的诗歌语言也并不是很怪特。贾岛爱好写诗,自称“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那么他的特点在哪里呢?韩愈曾称其诗为“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相对韩愈一派的怪异诗风而言,可以说是如此;但这也绝非孟浩然那一路的自然平淡。贾岛作诗主要的特点是爱好苦吟,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在一些很琐细的地方寻求到诗歌的素材,加以精心锤炼,造成新巧但也并不怪诞的诗句;他在一首诗里最用心的地方也就是中间对仗的两联。像“独鹤耸寒骨,高杉韵细飔”(《秋夜仰怀钱孟二公琴客会》)可说较偏于尖新,而“雪来松更绿,霜降月弥辉”(《谢令狐相公赐衣九事》)则稍为自然,但都不是不经意所得。贾岛最得意的一联乃《送无可上人》中的“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他特意作注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其刻苦与自重可见。前一句写孤独者在潭水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后一句写疲惫的孤独者倚树小憩,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怅然无依的气氛。两句的确对偶工巧,但要说怎样了不起实也不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