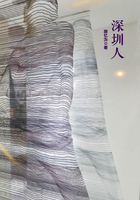安徽出大官,包拯曹操朱元璋,安徽也出穷人,比如张小张。
张小张今年虚岁二十实岁十八,张小张在厦门去鼓浪屿的轮渡上,轮渡上都是人,轮渡在海上。天乌乌,要落雨,空气凉丝丝的,腥得人的毛孔一个一个醒过来,海水不蓝,近的有点青,远的像黄泥汤,轮渡犁过去,船舷边上都是浪,白花花的,海水多呀,都挤到天边去了。张小张知道大海很大,可当他看到这么多的水时,还是猛吃了一惊,望着不远处的小岛,嘴巴大起来。
一个小老头左手拿着地图右手指着小岛,早起的小鸟般放声尖叫:你看你看,小金门!才一海里!两个世界啊,才一海里!!
小张的心蹦到嗓门眼,啊,暗叫一声。
小老头的头发白苍苍的,不远处的小岛绿油油的。
张小张在淮河边上跑来跑去,淮河里都是水,颜色让人起疑心,一边挤挤搡搡一边翻白眼。张小张手里握着一张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村里村外的走亲戚。可他一张口,亲戚的脸就变了颜色。二叔抓着他的手说,真替你高兴啊,只可惜这段时间手头太紧,要不,等圈里那口猪崽大了,卖个好价再借给你?邻村四姑家的院门甚至在他的影子一探入村口就合上了,小张扬了嗓子喊:“姑!”——没人应,屋顶上,炊烟正蛇着腰往天上跑。小张知道,陈校长家的门肯定大开着,陈校长肯定准备好了一个大信封,里面都是钱,挺刮刮的百元大钞纸,粉红,像猪里脊,听生物老师说,人肉就像猪肉,人最像猪,猪是人最亲的亲戚。可张小张不可能去找陈校长,不可能。小张累了,小张坐在四姑家的院门口翻来覆去地看通知书,小张想,要是上面写的是清华或者北大有多好!那样县里和镇里的主要领导就会赶集似的挤到家里来,不停手地掏出一个个大红信封,一次又一次地解决“贫困学生的上学问题”,而且还要上电视,大家一块儿说车轱辘话。可惜啊,就差那么两分!自己当时怎么就晕了头,那么简单的题都能写错!肯定是饿昏了!小张一生自己的气,小肚子就胀起来。
小张想要尿,小张睁开了眼,小张愣了好一会。小张就坐在离日光岩风景区门口不远的一棵大树下,树下除了脚边一小块扇形地面是干的外到处湿淋淋,看来,刚下过一场不小的雨。小张擦擦嘴角的涎水,仰脸望望头顶的树,树叶圆圆的肥肥的,在微风里心满意足地上上下下,不知是什么树,一束阳光穿过树叶扎到脚面来,小张的心缩了一下。
陈校长是小张他们村小学的校长,陈校长生了一对金鱼眼,泡泡的。陈校长是诗人,有门派,小张记得很清楚,陈校长说,叫新死亡,当时小张吓一跳,瞪大了眼瞅陈校长,好像陈校长一不小心把身子蹬直了。陈校长人长得不怎样,可校长阿姨很漂亮,比陈校长的字还漂亮,校长阿姨这几年不在家,听说她在南方的一个城里上夜班,衣服穿得少少的,身上喷得香香的,陈校长家新盖了大瓦房。人家一边说一边挤眉弄眼的笑。小张的学费一直是陈校长出的,村里像小张这样的孩子不仅一两个,陈校长家有钱。
小张有时会想起自己的妈妈,一想起眼睛就湿湿的。可是妈妈的眉眼越来越模糊了,有时闭上了眼也想不清楚。有妈的日子真好!有妈的日子不会饿肚子。那年妈妈生小妹,太使劲了,一口气没接上来人就硬了,奶奶说,女人的命不值钱。小张的爸爸到广东去打工,在私人小工厂,一去三四年,回来时没带回什么来,手指倒是少了三四根,两眼有点直,整日坐在门槛上捏着剩下的手指,数天上的云。
三年前,夏天,在陈校长家,知了舍了命地在树上叫,陈校长说,这是你的学费,到了一中,好好读,钱不够,尽管说。小张中考考了全县第二名。小张说,我不读了。陈校长说,为什么?小张不说话。这还能为什么?!小张怎能用阿姨上夜班的钱读书!小张的裤子在夜里湿过了几回,知道什么叫上夜班了,知道后,他揪着自己的头发使劲撞墙,撞得墙皮噗啦噗啦往下掉。
两人僵在屋里。屋外的知了大概也感到气氛不对,不吱声了。就这时,门外一个男人挣破了嗓子:“我拿什么针灸!我情愿溅雪疯猴!”那声音起点高,再朝上一点就不像人声,像杀猪,像狼吃了枪子,一下就把空气撕裂了。
那人是小张的堂哥。小张家的亲戚都会读书,但都穷,堂哥也不例外,他从上高一开始花的就都是陈校长的钱。堂哥上的是重点大学,不过校名不叫北大、清华或者复旦,而且他学的是哲学。堂哥说,哲学就是研究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堂哥这年毕业了,他拿了一大叠的材料在北京城里冲来冲去的找工作,可是,没人乐意接收他,有人还拍了桌子:“谁需要你研究人为什么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他听了神色大变,连回家的路都认不得了,还是陈校长前前后后坐了几天的火车,才把他运回了村里。
现在小张知道堂哥唱的不是什么“针灸”了,堂哥唱的是“我拿什么拯救,我情愿见血封喉!”小张还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个姓孙的,只是一直没弄明白这姓孙的到底是公是母。
堂哥认不得陈校长了。陈校长望着堂哥越走越远的背影,两只泡泡眼都化成了水。陈校长别过脸说,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自己,别做亏心事。
小张踩着堂哥的脚印走到日头底,阳光烤得小张的后背滋滋滋地响。陈校长冲到门口抻长了脖子喊:你是头犟驴子!你遇事要三思,要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