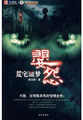当我灰头土脸地踅回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想不用说,我的父母一定急坏了,我为此有些恶毒的快意,我只是个小学五年级的男生,受了这么大的伤害,似乎只有父母也跟着我一道痛苦,才能安慰我那幼小的心。我走进黑夜中的生活区,然后就看到了那枚闪闪烁烁的烟头,它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分外惹眼。我被它吸引着来到了那根单杠前,于是,这样的一幕在夜色下浮现:有一样物体,貌似一床棉被,两头齐平地挂在单杠上。我把它首先想成棉被是有根据的——天气好的时候,学校里的家属们经常把自家的棉被搭在单杠上晾晒。但是显然,棉被不会叼着支烟。你一定也猜出来了,不错,这个两头齐平挂在单杠上的,正是司马教授。我的脑袋依然昏沉,但还是感到一阵激动,我想奇迹总是发生在黑暗中,他老人家终于把自己折成了一只马扎啊!我听到他问我:
是毛亮吗?
我答应了一声,贴近了认真地端详他,他有多么惬意啊,嘴上叼着烟,身体在夜风中不易觉察地轻轻摆动,他像一床棉被,但是比棉被更柔软,确切地说,他更像一把拉面——我母亲在家里拉面时,总是用一根筷子挑起拉好的面条,然后下到沸腾的水中。我刚刚经历了身体上严重的挫折,现在目睹这样一个出神入化的身躯,感到了无比的惊诧,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司马教授如愿以偿地悬挂在单杠上,在这个夜晚,他的喜悦溢于言表,尽管他曾经向我宣告过“古典诗歌是没用的”,但是,此刻他还是得意地对着夜空吟颂出了如下的诗句:
六十余岁妄学诗
功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笑寒灯下
始是金丹换骨时
那天夜里,受到他的感染,处在挨打后遗症中、脑子像一团糨糊一样的我,也不由得浮想联翩,许多毫不搭界的诗句纷至沓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西风误……其中最离谱的两句是:
仗义半是屠狗辈
负心都是读书人
然而我们的古典诗歌多么莫名其妙啊,似乎哪一句都能对应着此情此景。和古典诗歌同样莫名其妙的,还有我们的身体。今天我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柔术师了,我能够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身体拧成一根大麻花,至于马扎什么的,简直是轻而易举,有时候我吃饭都是把头从胯下钻出来边玩边吃,当我在舞台上旁枝斜逸地表演时,观众们一定会觉得非常之莫名其妙。我的职业让我的母亲很失望,我连一个物理讲师都没弄到手,然而我心安理得,因为我的身体可以被我随心所欲地做主。如果要追溯我职业的发端,我会向你回忆那个夜晚——那时我晃了晃脑袋,里面喧嚣的诗句像头皮屑一样地纷纷撒落,然后我默默地走过去,贴着司马先生,神魂颠倒地把自己挂在了单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