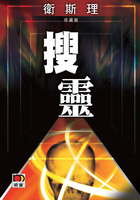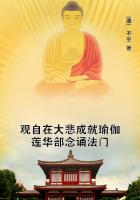我不得不说,世人都瞎眼,才招致我嫁不出去,当然,我指的是男人,男人们瞎了眼。
在我二十来岁时,准确一点说是十八吧,花一样的年纪呀,干脆就说我就是一朵花,他妈的就是花瓣短了点,颜色黑了点,守宿舍楼门的半大老太太竟然像只猫一样从值班房里的窗子里跳出来,但也许是从门里。跳出来后伸出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大声指着一牌子说: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看过去,一块白漆过的大木牌子,上书:男生止步。
当时我穿着石磨蓝的牛仔裤,一双跑鞋,上身着白衬衣外面挂着军装样式的马甲,浑身全是口袋。我感觉这样穿非常“滋”,口袋们一个都不是摆设,随便哪个口袋里都能放开东西,我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当然,我喜欢的购买的好买东西都不实用,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了个实用主义者,胸无大志、鼠目寸光,说白了很恶俗很让人讨厌,但是,并不是所有时间都这样。
我就穿着这件实用的马甲,朝着那个半大老太太一笑,不是回眸,而是回身,结果她真从这一笑中活活看出妩媚来,将我放了进去。
这是我严肃地看待男、女的开始,感觉男生不上女生楼,真的是严肃的事情。大白天也不能上去。那时候不是现在,不知道一切龌龊的事情都可以唐而皇之地在朗朗白日下进行,我那时单纯,没现在这么复杂,不知道社会、人性的不确定和复杂。我真得感谢这个半大老太太,她是我严肃看街男、女问题的启蒙者,她当天穿着蓝白条的汗衫,后面换着个小髻。义正辞严地在我面前伸出了她伟大的手臂,这只手臂像只大容量核能推进器,将我“思春”的心思一下子提升到了外太空。
我二十岁以前,对男人的感觉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八九岁,当然,正常的应该是五六岁,或六七岁吧,因为我很晚熟,往不好听了说是很痴呆。这个阶段中除了偶尔看到小鸡鸡心生出多着一块肉不大方便的念头,就想不起什么来了,我还想过如果长大了,像大人一样骑自行车,那他们这块肉将放到哪里,如果垫在底下,会不会压肿压烂,危及生命,想了好长时间,没见哪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丢命,才不再想了。这个阶段,可以说成男女方面无意识、无差别阶段吧。我看到好多资料,说性别意识,性意识很小就有了,那抱歉,不是我标新立异,或者,我真的很白痴,这个阶段除了上述的一点没落下别的。第二个阶段是八九岁到十五岁吧,反正我说的这些时间,年岁,都是约指,因为我是个健忘的人,除了别人欠我钱,别的事情都很容易忘记。这个阶段我挺烦男生的,最突出的感觉是力气小,打不过他们,久而久之,先是敬而远之,后来就由失败产生惧怕又转成讨厌,厌恶,不大和男孩子一起玩了。再后来十五岁致二十来岁吧,我从渐渐好奇到好感,对男孩子们开始感兴趣起来,当然,我的意思是,他们也应该对我感兴趣才对,礼尚往来嘛。可这帮孙子们,一点也不知道德礼仪,白白生在了我们这么个古老的、博大的、闻名于世的(以下略去一百多字,全是形容人应该讲礼貌的,也就是我对他们感兴趣,他们从根子上讲就应该投桃报李的字)礼仪之邦,竟然连这点都不懂。当然,感兴趣也不是全盘接受,有一次,一个男同学来问我题,我给他解着题,给他讲,苦口婆心一大通,无奈他还是没明白,然后我又换了一张白纸,拿笔在上面写出有好多好多英文、罗马文、希腊文等的公式,他还是不明白,急得我抓耳挠腮,抓也不敢狠抓,因为我既然已经对他们感兴趣,就不能使自己破了相。他听不明白,看不明白,当然也不明白我很多很多不可告他的心思,自顾沮丧地转过头,一面挠头皮,我顺着他手里捏着的一枝圆珠笔看下去,竟然看到他脖子后面很靠下的一些头发,那些头发算不得正式的头发,就像灌木算不得真正的大树一样,但这些黑乎乎的毛发长在那里,让我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天哪,他竟然比怪物好看不到哪里,竟然无耻地长出这种东西,我顿时闭上眼睛,再不敢看他脖子后面,后遗症是我很长时间不想给男生讲题,不是我不想帮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有脖子,脖子后面有那么骇人的东西。这种事情我不便,也不敢明说,我怕我一说出来,别人非但不会理解,而会说我变态,流氓之类的。当然,后来我与几个要好的闺密深聊时,她们也有类似的感觉,像讨厌他们嘴里的气闻,害怕他们嘴唇上竟然有小毛毛等等,但那时候没有闺密,当然,有闺密也不敢谈这种东西,怕弄不好被别人说成是“喇叭裤”,“喇叭裤”离我们有些远,比我们大好多岁,但是,我们知道他(她)们,小青年们烫起头发,叼起烟卷,穿着劣质的尼龙丝袜和白颜色坡高跟挂鞋,感觉自己“吊”的很,大姑娘们(那时候我们小,所以感觉她们又时髦又高大丰满)也冷烫热烫地将头发卷起,有全卷的有只卷留海的,穿一种踢里踏拉的“蝙蝠衫”,擦口红,臭美得不行,她们任由男喇叭裤们将手搭在肩上或干脆搂她们的腰,浪笑着,从街头骚到街尾。所以,我不敢说这些,但这些东西憋在心里,很让我痛苦,很让我对刚开始有好感的男生们失望,竟然开始感觉他们是些怪物,脖子前面突然突起一块东西,捏着公鸭嗓子,一开口就弄你八身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