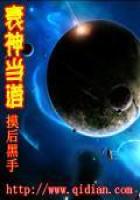该找姬谈一谈了,我对这件事情非常迫切。
大约在隔壁发生争吵的五六天后,我才看到了姬的身影。那天我在二楼边整理伯父的有关资料,边留意往窗外看,忽然看见姬急匆匆地进了隔壁的大门。我下楼先拣了一会儿豆芽菜,然后装摸做样地出了门(妻子那时已经反感我去隔壁)。刚走到姬的门口,突然,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跪在姬的面前,象癫痫病人一样流着口水、浑身哆哆嗦嗦地祈求道:“就抽一次,我就抽一次……”姬流着眼泪、双手在他的额头上抚摸着。从他的神态上不难看出,是一个大烟鬼。这种人由罄粟所陪伴,在腾云吐雾中度日月,怎么能够赢得姬的芳心,我百思不得其解。姬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百元钞票扔了过去,然后摆了摆手。烟鬼转悲为喜,抓起来连爬带滚往出跑,出门后撞在了我的身上,我往起拉他的时候,知道他比我的亨特重不了多少。
我显然来得不是时候,姬表情极不自然地和我打招呼。她递给我一杯茶后,坐在一旁低头捏手,一副要接受审判的样子。
“他救过我的命,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姬显然是在解释刚才的一幕。
我把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的这些让人无法理解、又非常痛心的事情和盘托出,想期望有一个满意的解释,结果她用长时间的哭泣做为回答,哭泣声中夹杂着几个字:“我没有办法”。对,看来是没有办法。一个美丽的少女被一群男人们纠缠和争风吃醋,弄得无所适从,没有办法,是符合情理的。
从那以后,我多次找姬,一本正经地为她灌输了许多真、善、美和有关做人的道理。尽管我现在懊悔当时是迂腐至极,但那时候确实是认真的、真诚的。
我在向姬传经布道的时候,没有少了给她接济开支,也为她离开歌厅那个是非之地和寻找别的工作承担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我满腔热忱地为姬灌输人生哲理的那段日子里,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天正吃晚饭,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自称姓展的男人恶狠狠地喊着我的名字,他不容分辨,硬说我把他的秘书姬小姐拐走了有一年多。我告诉他说一定是搞错了,对方不但不理睬,还说了许多威胁性的话。我扔掉电话后妻子追问,我说打错了。这事儿在我的脑子里还是留下了一个阴影。找姬的电话,我刚来不久就接到过,以后也时有,我多半是解释清楚就完事,威胁性的电话,这是第一次出现。
在这之后的一个黄昏,毛毛细雨下个不停,这洋的天气在南方的雨季还算是最好的。南方的雨简直就和北方的风一样,令人厌恶至极。我一个人低头行进在微雨中的脂粉河畔,时而想象伯母当年顺水而下的辛酸情景,一会儿又琢磨着河水上游的才子佳人生活。这时身后一辆轿车呼啸而来,带着狰狞的恶叫和凶猛的泥水停到了我的身边,两名肩宽腰圆的男人拦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个倒提着一只打开的酒瓶。
“是你拐走了这个婊子?”其中一个向我展示了一张五寸大小的彩照,上边少女姬正亲昵地坐在一位狗熊模样的男人怀里。
“是…不是…这是…”我半天反应不过来。
“看看,让你死个明白。”另一个男人从包里拿出一张条子在我面前晃动,我拿过来一看,是有大夫和姬签名的人流病休通知书。
“不是,没有,误会,我没…没有带铃铛”。我当时已经傻了眼。
“带铃铛的我们还不找呢。”其中一个夺过条子
“呸”的一声往我脸上吐了一口睡昧,而后伸手一掌砍在了我的脑门上。屋里的妻子和两个帮工听到争吵声也跑了出来,身后跟着咆哮的亨特。就在这一瞬间,那只没盖的酒瓶子从空中闪过一条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我的额头上,一股热流哗啦而下,这个让人伤心的世界,远远地从我的知觉中离去了。
关于那次劫难中我的狼狈形象,妻子后来和两名帮工给我描述过多次,最具共性的说法是,我一米八的身躯在细雨中,被两只熊掌似的大手推来搡去,随着一声绝望的惨叫,我便象一堵墙一样倒在了血泊之中。从医院康复出来后,我多次在我倒下去的地方徘徊过,也在靠近当时现场的那颗桑树前长时间发过呆。那上面有我残留的血迹。我痛苦不堪,我伤心极了:你们这些咬文嚼字,为别人指点迷津的人啊,自己却不知不觉地掉进陷井而任人宰割。这个世界上最天真、最纯情的人啊!其实最幼稚。为了铭记那一次血的教训,我从那颗桑树上折下一截染着血迹的枝条,带回了北方,插在我家客厅墙上的一只花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