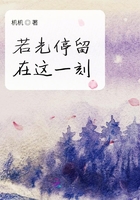按月轮是轮不下去了,尤其是二伯家连续轮了两个大月后,二婶就给爷爷撤了泼。大伯就给二伯和爹又传了话,让爷爷按天轮着吃。
吃不肥就跑瘦了。爹很怅然地说。
一天早晨我出门撤尿,忽然看到爷爷又来到了门口。
今儿个不是轮到二伯家了吗,爷爷你咋又来咧?
爷爷我老糊涂了,走错门了。爷爷显得很沮丧,摇了摇头就又转身走了。
爹闻声出来,看见爷爷已经爬上了对面的山坡,爹张开嘴巴想叫什么,终于还是没有喊出声。
转眼到了1960年,日子就更艰难了。
爷爷每次来吃饭,如能带上几只坏洋芋,爹的脸上就展刮一些,这一点我能看得出来。
种洋芋的田地,已经被人翻得底朝天了,爷爷就去掏地老鼠(田鼠)洞。爷爷掏地老鼠洞时很可笑,他肩上扛着长杆烟锅,迈着罗圈腿在地里乱走,只要一脚陷进坑里,爷爷就会蹲在地上,就会把长杆烟锅伸进洞里去掏藏在里边的洋芋。我喜欢跟在爷爷后边学他走路的样子,实在走不动了,就“唉哟——地老鼠咬住我的脚了”地叫喊,爷爷就会折回来拉起我,哄着我走,给我许愿说回家把最大最好的洋芋烤了让我吃。后来这一招不灵了。一次我眉头一皱就喊“狼来了”,爷爷一听,转身就连爬带滚地扑了过来,一把把我抱在了怀里,然后慌慌张张地把我拉回了家。
后来爷爷就再不带我掏地老鼠洞了。我怎么求,他也不答应。
爷爷你骑着金驴走州过县的,还怕狼吗?一天晚上我忍不住问他。
怕。爷爷很怕狼。
爷爷你打过狼吗?
打过。它们太多了,爷爷没打得过。
爷爷说当时他是靠了一面墙的,一群狼轮着扑上来,爷爷挥着木棒把它们打退了。可狼们一起扑上来,爷爷就招架不住了,狼就把身后的两个娃娃给叼走了。
叼走的两个娃娃是谁呀?
是你的一个叔和一个姑。
那爷爷你为啥不去夺回来呀?
爷爷不能动,一动身后的三个娃娃就又得让狼叼走。
那身后的三个娃娃是谁呀?
是你大伯二伯和你爹。
我说我那个叔和姑活着就好了。爷爷叹息着说,活着的话能给你爹省上几顿饭了。
爷爷每次来,妹妹都眼巴巴地盯着看有没有带坏洋芋来。妹妹如果看到爷爷手上有坏洋芋,不管上面的泥土伤疤,夺过去就往嘴里塞。1960年的日头啊,真是非常的诱惑人,妹妹看不到爷爷手上的坏洋芋时,就去看那红红的日头。妹妹两只圆圆的眼睛,瞅着日头发呆,瞅着瞅着就身子发软,当看到日头不停地变大,一直淹没了整个天空时,妹妹的身躯就像被割断的麦草,轻轻地扑倒在地。爷爷并不惊慌,他俯下身子,只有两颗门牙的嘴巴,对着妹妹的小嘴往里边吐唾沫。爷爷吭呀哼呀地又吐又喂了半天,转过身来说狗蛋娃,你来给你妹喂点唾沫星子吧。我说我嘴里又干又粘的,吐不出来。爷爷就说你想你在吃羊肉泡馍就吐出来了。我说爷爷你忘了,我没吃过羊肉泡馍。爷爷就说那你就想你在吃白面锅盔(大饼)。我说爷爷我小时候吃过的,现在忘了。爷爷就说那就想着吃烤洋芋吧,又大又白的那种,烤得皮子又硬又黄,两手一掰开,一股香气就扑进了鼻子。
爷爷说到这里,我嘴里的口水就流成了河。
没过多久,掘地三尺也找不到半块坏洋芋了,村里人开始吃草籽和苜蓿秆子。妹妹吃了拉不下屎来,憋得几天几夜地哭叫。村里有人说榆树皮做成面,吃进肚里不结块,爷爷听了,提起斧子就要去砍树。
这可不得了了。
爷爷要砍的榆树是留给他做棺材用的。榆树长得慢,还不够一个棺材料,大伯每年开春都要用手指和胳膊量一量粗细长短,说是最快还得长上五六年。
爷爷要剥榆树皮,没有人劝得住,连大伯都没有喝唬住。没有办法,全家人就去下了跪。伯父和爹求爷爷说,日子太穷了,现在砍了树,我们凑不起棺材啊!爷爷说,有几寸烂板板子,做个匣匣子就行了,要不就挖个土坑坑子埋了,孙子孙女的,还要续香火呢。
爷爷剥下榆树皮后,又大块小块的搭配成了一样多的三份,喊大伯二伯和爹去拿。还罗嗦说,晒干了用石磨子磨成面,煮成稀饭让几个娃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