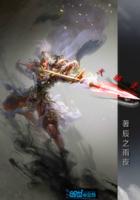男人转向魏明明,从手里的公文包中取出一叠文件,盯着文件看了一会儿才递给她。“是这样,”男人的表情没了先前的平和,压下声音说,“在一次小范围暴动中,您丈夫不幸被流弹击中脑部……”
“击中脑部?”魏明明把厚厚的文件捏皱,下巴微微颤抖着说,“成植物人了?”
“不,”男人吸了口气道,“他……不幸牺牲。”
“不幸牺牲!”魏明明叫起来,她用几乎要把男人推倒的力度扑到他身上,抓住他的衣领说,“你骗我!布什还没宣布开战,仗还没打起来,他怎么会牺牲!什么暴动,什么流弹,你通通都是放屁!”
“夫人,请冷静。”男人为难地抬起双手道,“请看一眼那份文件,我们已经追封您丈夫为美国人,而你也被批准获得绿卡,获得永久居留权!”
“去你妈的绿卡!去你妈的永久居留权!一定是你们,是你们把他推到最危险的地方,是你们!是你们害死了他!”魏明明嘶声力竭,对着男人疯了似的拳打脚踢。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白可立刻上前拉住她。魏明明胡乱挥舞的双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打到她脸上,她躲闪不过,忍着疼对杵在一旁的男人喊道:“先生,请你离开!”
魏明明的挣扎丝毫没有减弱。男人踌躇了半晌,庄重地向她行了一个军礼后,转身离去,步伐沉重。
魏明明直视着男人离开的方向,眼睛里要滴出血来,却掉不出一滴泪。
白可实在没力气了,松开手。魏明明立刻无骨般瘫坐到地上,不哭也不叫。
“明明姐,”白可用力晃着她道,“明明姐你哭出来吧。”
“呵呵。”魏明明不哭反笑,笑得白可心里发毛,“他做了三十多年‘爷们儿’,最后尽然连战场都没上就死了,呵呵,追封为美国人,真可笑,谁他妈稀罕!”
“明明姐……”白可恨自己嘴笨,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安慰她。
“呵呵呵呵……”魏明明自顾自地大笑,笑得喘不过气,捂着胸口说,“你走吧,走吧,你走了我就哭出来了。”
“真的?那我走。”在白可的记忆里,哭不出来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她不能抽她耳光,只好走。
“走吧……”魏明明抱住膝盖,声音沙哑,隐隐地透出冷笑。
从仓库出来,天依旧是蓝,路依旧是远。她想起他的话:这个国家不会因为他们这些小人物的生死而有任何改变。可无常的宿命,不会因为他们是小人物就对他们开恩,反而更加来势凶猛。
“嘭!”
不远处一声巨响。
正在沉思的白可和坐在窗边的唐一路同时被惊起。
白可只隐约看到一点火光,大小不一的石块呈散射状落在她身边,幸好没有砸中她。
同时刻,唐一路从楼里冲出来四下观望。目力所及,到处都是奔逃的人。
她想到他,那声音似乎是来自前方。
他也在担心着她,她应该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不安笼罩上死亡的阴影。随处可见的彩灯,此刻却异常刺眼。四散的人群相互推搡,道路上满是炸碎的玻璃和石头。眼前的景象在巨大的恐惧下突然变得陌生,她无法辨清回家的路。
“白可!白可!”唐一路一遍一遍唤着她的名字。心里直在质问着苍天,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只不过让她出去一趟,只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
推开一个又一个惊慌失措的脸,在警车刺耳的鸣笛声中,在催泪的滚滚烟雾中,他听不清,也睁不开眼睛。第一次,他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恨意。
那条并没有橡树的橡树街,此刻充斥着震惊和慌乱。在这个交替的时代,这个和平的时代,罕见的冲突正在上演,然而没有人会为之欢呼。催泪的浓烟妄图催醒人们的理智。人们在痛哭流涕中发现,理智原来是一件让人悲哀的事。
可是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从小她就是很容易迷路的孩子,妈妈曾告诉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原处等待。
她的静止在四处奔窜的人流中,非常突兀。身上火红的大衣是特意为了盛大的节日而准备的。此刻,却成了她坚定的标志。她想象自己是至高点上的一面红旗,她的追随者,她的信仰者,她的唐一路,一定正冲破敌人的千军万马向着此地前进。
风向改变,不远处街道上的烟雾慢慢向这里渗出,它的触手追赶着逃散的人群。
而她依旧选择站立不动,直到眼睛止不住流泪。
“白可!”
熟悉的声音。
她知道他来了,可是她睁不开眼睛。
“一路!”她大声叫出来。
唐一路隐约听到她的声音,但更多的是人群的叫嚷声。
游民和飞车党趁着混乱砸坏附近的店铺,激进的种族歧视者四处搜寻中东人,对他们施加暴力,连长得像中东人的也不放过。
可这些与他有什么关系,他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只想找到那个迷路的傻瓜,带着她离开。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他对她喊。
他们相隔不过十米。
“一路。”她不安地又唤了一声他的名字。
顺着声音的方位,他一手捂着眼睛,一手向前探去。
距离被缩短到一半,他就要找到她了。
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政府死了!”这声音他记得,是早上在教堂里演讲的那个男人。
凄厉的一声吼引爆了所有恐惧,人们像漂浮在急流的水面上的球,激烈地碰撞。
从后而来的冲击力把他推到在地,他试图爬起来却一次次失败。不断有人从他身旁经过,不断踩到他的衣服或是他的手。他悲哀地认识到,在关键时刻自己是这么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