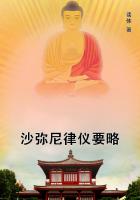一座长满了绿色柏树的大山横亘在驼队的前面,驼队停下来了。拉成一线的一列接一列的驼列都静静地等待着,凭着经验大伙儿都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牛二板骑着马向后边走过来。“掌柜子们、伙计们……咱们已经到了乌兰穆图山口,卡伦上的军官正在查验货主的执照和运货凭条;待会儿还要抽查货驮子,记着——我们是在为俄国人运货,货主是……”牛二板一路走一路向驼夫们安顿着,时紧时松的风使牛二板的话已经连不成句子了,他只听见最后的半句:“……再问什么,你们一律回答不知道!”
“九年,卧下驼,让骆驼歇一会儿。过卡子的事麻烦着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稍格!_稍格!”
海九年看见前边的驼列在戚二掌柜的指挥下都卧倒了。驼队的前前后后响起了驼夫吆喝骆驼的声音。
二斗子走到九年这儿来了,从腰带上抽出烟袋、烟荷包丢在地上,在被无数的驼掌塌磁实的雪地上一屁股坐下来。“他妈的,整整一天了我这张嘴还没和谁说句话呢。都干得要冒火啦!我就知道这一程不大对劲儿,一天一夜不歇气儿的走……。”
俩个人香喷喷地抽着烟说起话来。
“九哥,乌兰穆图这地方你知道吗?”
“听说过。”
“这是通往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卡子。从山口穿过去用不了一个时辰就到俄罗斯的地界了。……这地界经常出事!”
“你来过?”
“嗨!……还说什么来过没来过的话,都象是走平地似的啦。”二斗子向周围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咱们的驼队这会儿做得是什么营生吗?”
“是什么?”
“是走私!”
“哦……,我说呢,”
“行啦,这事儿你心里明白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驼队起动了。果真象二斗子说的那样,也就是一个时辰的样子,驼队便穿过了乌兰穆图山口。这是九年生平第一次双脚站在外国的图地上。虽说是只隔着一道萨彦岭,山两边的自然景观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他眼前展开的是陌生的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景色,连绵的雪原放射出蓝色的光芒,被大雪覆盖的道路上奔跑着马拉的雪橇。峭利的风里边有一种特别的苦涩的味道。
又赶了两天的路,来到一座城镇。驼队开进了一个拿对劈开的圆木围起来的大院。一座向阳的很大的房子,房基很高,墙壁也都是用木头钉起来的;按装着明亮的玻璃,房顶的一角伸出一个烟囱,冒着淡蓝色的清烟。骆驼在院子里卧成了一大片,驼夫都蹲在地上抽烟,等候着。
屋门前的木头台阶轰轰隆隆响着,胡德全、随队的王掌柜和在乌兰穆图山口才出现的那个俄国人陪俄国货主走到院子里来了,挨着个查看货驮。驼夫们都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等候着。
“茶货没有受潮吧?”年轻的经理一边向前走着一边用俄语问道。
“怎么会呢……这一点您尽管放心!”一直跟在经理旁的王掌柜说。
年轻经经理站住了,把手伸出去,眼睛看着一个货驮子,说:“拿刀来。”
旁边那个俄国人从身上抽出一把食肉刀交在经理的手里。经理接过刀顺势在货驮子上划了几下,划开一个口子。经理把一块砖茶那到鼻子跟前闻了闻。“怎么样?”王掌柜用俄语问。
“坶,不错!”
年轻的俄国经理不再往前走了,放开目光打量着卧满院子的骆驼,简单地命令说:“卸货吧!”
年轻的经理转身离去。
胡德全吆喝着:“掌柜子们、伙计们,动手吧!快点。……”
响起了一片吭哧声、木头驮架的咯吱声。
这里是俄国的边境城市沙必乃达巴汉。晚上驼队就在离城郊二十里的的地方搭起了房子。一片由南向北倾斜着的山坡地,许多积雪盖不住的骆驼刺、干枯的蒿草、荩条延着平坦的山坡地铺展出去,密密层层的一眼往不到尽头。驼队要在这里放场两个月,让在数千里长途跋涉中耗尽了体力的骆驼恢复膘情。驼夫们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同时借机会把各自的稍驼的货卖出去。
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早上,海九年与王锅头、二斗子、戚二掌柜相跟着牵了自己的稍驼出发了。运货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他们要深入到沙必乃达巴汉以北二百里的地方做他们各自的小买卖了,与那里的专们狩猎的西迫利亚当地人以物易物换取皮毛和药材。这样他们比在沙必市把货物卖给俄国的商人获利至少要高出一倍。四个人牵着骆驼顺着大道走着。
一支小小的马队追上了他们。是一群俄国上流社会的人出来打猎游玩的,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猎枪,闪着黄色光亮的子弹带在胸前斜打着十字。马蹄踏着道路上的积雪从海九年他们的身边跑过去了。大概跑出有十几丈的距离马队停下来了,其中的一个拨转了马头独自向九年他们跑过来。王锅头率先停下了,大家等候着。
原来是那个年轻的俄国经理。今天他换了一身装束,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软羔皮高顶暖帽,穿一件光面的水獭皮大氅。坐下骑着一匹云青走马。
“你们的骆驼驮的好象是大黄?”
马蹄隆隆响着,狩猎的马队从他们的身边跑过去。但是在不远处那位年轻经理的马嘶叫着打着一个旋子站住了,云青马驮着主人又返了回来。“你的货驮子里装的是什么货?”
年轻的俄国经理拿马鞭指着海九年的骆驼问。
“是大黄。”海九年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但是年轻的俄国经理显然并无恶意,他下了马,凑到九年的货驮子跟前闻叻闻,问道:
“我能看看你的大黄吗?”
“当然……可以。我的大黄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五台大黄!”“真的吗?我正想找来自中国的五台大黄呢”年轻的经理说“那么,请你把货包打开一下。”
海九年动手要解货驮子了,一扭脸他的目光正好与年轻的经理遭遇在了一起——他立刻呆住了。笼罩在他的记忆上空的迷雾迅速散开,乌里亚斯台草原景色在他的脑海里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八月的河边的草地上遍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米契柯与他骑着马向杵立在不远处的山岗上的古代土堡跑过去。……海九年的舌头缓缓地转动着,用几乎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说:“米契柯……”
但是对方已经听清了他的话。年轻的俄国经理睁大了眼睛,疑惑的目光在海九年的身上来回扫着:这个陌生的中国驼夫结实的身材高出他足足有半个脑袋,满着冰霜的胡子使的他难以辩出年龄;身上的破旧白茬老羊皮袄在大襟上挂破了好几个口子,头上戴着一顶披肩的狗皮风帽;……只有一双闪着笑意的棕色眼睛使他觉得熟悉,似乎在那里见过。
“你是谁?”
海九年苦笑着,没有立刻回答。目光中流露出又兴奋又有些失望的神情,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向对方解释这一切,干裂的虚肿的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
“你当真认不出我了吗?”海九年用俄语说,“六年前……,在乌里亚斯台……骑马!登古堡……”
“让我想想,……对,我肯定认识你——等等!你的眼睛我太熟悉啦。不要告诉我,让我自己想出来……”
海九年等待着。笑着。
“难道说你是……元龙吗?”米契柯眼睛一点点地睁开来,瞳仁闪出欢愉的灰蓝色亮光。
“是我……,米契柯!”
“奥——上帝!”米契柯惊叫起来,扑上去把海九年紧紧抱住了。两只手在海九年的背上使劲拍着。后来米契柯抓着海九年的肩膀,仔细端详着他的脸说:“我们又见面啦!可是,你的样子变化真是太大了。你要是不说出来,我真的不敢认你呢……”“可是你还是老样子,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你在做什么?”
海九年摊开两手,目光指着卧在身边的骆驼和卸下来的货驮子回答:“我是一个驼夫。我就做这些事……”
“你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向不少人打听过你。”
“一言难尽……,”
海九年向两边看了看把话打住了——周围是许多张被他俩的举动弄得惊呆了的脸。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说话呢?走——回屋里去,为了庆贺老朋友重逢,应该喝一杯!”
屋子里暖洋洋的,火在离海九年不远弟炉子里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满满的一瓶子伏特加喝已经下去了,海九年身上冒汗了,挂在鼻子尖上的细碎汗珠闪出水灵灵的白光;消融的冰霜把他的浓密的落腮胡子浸湿了,从胡子尖滴下来的水把光面的羊皮坎肩弄湿了一大片。
“把坎肩也脱掉吧。”
米契柯一边提议说,一边把又一瓶酒打开给九年额杯子里咕咕嘟嘟倒满酒。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又见面了!……”
海九年把脱掉的破羊皮坎肩随手丢在地板上,兀自感慨着。“不错,这一切真的象梦境似的难以让人相信。我从军队复役期满一回到公司就打听你的消息。大盛魁和我们公司的业务来往比过去更多了,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的人,你离开大盛魁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我是被开除出来的。”
“我知道。是为了一件泄露秘密的事情。这件事与我们康达科夫公司有关。”
“我没有做那事!我是被陷害的。”
“我当然相信你,……不说这件事了吧,来!——我们接着喝酒。”
他们自由自在地谈着,话题忽东忽南忽西忽北;共同感慨着时光之匆匆。现在米契柯已经做了康达科夫公司的总经理,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全部的业务。米契柯还是爱马,特别喜欢走马。他心爱的云青走马是他拿整整一链骆驼的海象皮换回来的,价值两千两汉堡银。
两个老朋友边喝边聊,后来九年的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喝酒却喝的越来越多,脸色变的象纸一样的苍白——这一点非常奇怪,别人酒喝多了总是脸红——结果他年终于喝醉了,瘫软的身体就象被抽去了骨头似的从椅子上滑下去,同时就睡着了。
他问海九年:“后来你又到过乌里亚斯台吗?”
“再没去。”
“一会儿我们去骑马。我这里现在养着五匹好马,都是走马。对啦,你还记得桑布道尔基吗?就是那个沙王府的驯马手。我的这些走马都是桑布道尔基调驯出来的。”
“当然不会忘记啦。”
“很可惜,那样一个强壮的驯马手残废了。”
“怎么回事?”
“是调驯一匹生格子马的时候受的伤——恰巧被马蹄子踏在了脖子上,把颈骨弄断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哦……,想不到桑布的下场比我还惨。”
“去年我到乌里亚斯台见着桑布道尔基啦,本来我是找沙王想买一匹走马,结果恰巧遇见达尔玛赶着勒勒车从王府的院子里走出来。桑布道尔基一动不动地在勒勒车上躺着,……”
“就是那个王府里的使唤丫头吗?”
“是她。沙王把她送给桑布做妻子了。”
“达尔玛还很小呢!”
“是的,她只有十六岁。王爷还送给他们一对牛、两皮马、和二十七只羊——王爷叫做‘三九‘羊群,是一个吉利的数字。”“这么说达尔玛和桑布离开王府了吗?”
“离开了,沙王对桑布说:‘你进王府整整十八年,为我调驯出了无数匹名马良骥,你的功老就连佛爷也是知道的;现在你残废了,不能再为我做事了,我把王府里最漂亮的丫头赏给你做妻子,再送你一对牛一对马和‘三九‘羊群,你走吧——带着属于你的妻子和畜群,去过象云彩一样的自由自在的日子吧!记住,只要是在我的领地之内,你终生的赋役都将免去。……”
海九年觉得心里非常的压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米契柯的话又把他带回到乌里亚斯台那座美丽的草原小城,包围着小城的那绿茵茵的草原。桑布道尔基的不幸让他不由的又想到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