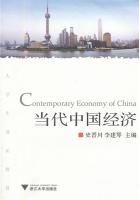自1984年和1985年飞乐音响与延中实业相继发行上市后,1985年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以下简称“爱使”)成立,旋即向社会发行了股票。这家当时总资产109.8万元,个人股只有5500股(面值50元)的公司,在上市公司里是袖珍型的,但在以后的庄家眼里,这只股票如同“爱情天使”般美丽。
1987年对于上海证券的发行部门来说,是个一相情愿的“股份年”。1月,上海“老八股”中的“航空母舰”--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真空”)成立,并于当月12日开始发行面值100元的股票,总盘子为2亿元,个人股占20%。这只股票因为盘子大而被视为上海的龙头股,上市后交易量一般都占整个股市的50%,价位最高时,股票市值占“老八股”总和的84%。3月,上海浦东的一家乡镇企业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以下简称“申华”)向社会发行了6995股面值100元的个人股股票。9月,飞乐音响的母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飞乐”)成立,发行21.01万股面值100元的股票,飞乐音响公司的董事长秦其斌出任飞乐股份公司总经理。两家“飞乐”都隶属于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飞乐音响主营商业,飞乐股份主营工业。上海股民把母公司称为“大飞”,把子公司称为“小飞”。
当1987年这三只股票上市以后,上海股市已基本形成,规模和数量也超过了深圳股市。上海管理层在1987年11月2日适时推出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股价指数--静安股价指数。不过在冷冷清清的股市中,这个指数实质并不具有市场意义,当时管理层也只好不对外公布,仅仅作为专家与证券从业人员的内部参考,直到1989年12月,才正式向外公布。
1988年,一家名牌商场股票发行并上市了,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园”)向社会发行了6.5万股面值100元的股票,在以后的“老八股”中,这是走势最为坚挺、唯一一只没有跌破面值的股票,在1989年的历史低谷中,它顽强地在101元守住了,上海股民对它的钟情来自于老上海对城隍庙的钟情,他们亲切地把它称为“老庙”。
上海发行股票的热情,当然也来自于股份制改革的全面展开。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地都在发行股票,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已达6000多家,累计发行金额超过35亿人民币,遍及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河北、河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地。上海作为致力于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城市,自然不会放慢股票发行的速度。
在发行股票的同时,上海在1988年又相继成立了三家证券公司,即上海海通证券公司、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上海振兴证券公司(后改名为上海财政证券公司)。这些证券公司纷纷设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柜台。
管理层一相情愿地认为,虽然上海人均存款比不上开放了十年的深圳,但上海当时有1300万市民,而可供流通的股票才60多万,平均每20人才一股,要把股市炒起来不费吹灰之力。股价的死寂,交易的萎缩,只不过是因为国家替股票定了价,而不是真正的股票交易,只要一放开股价,市场马上就会热闹非凡。1987年秋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决定放开证券交易价格,即按委托人意愿随行就市,真正股票交易的市场完全确立了。
现在一切都已就绪,就等股民热情入市的春风了。
但春风并没有扑面而来。上海市民当时对股票的冷漠和无视让管理层看不懂,也让那些懂股票的老股民感到失望和厌倦。自1987年秋天放开股价后,股价仅有两次小小的上扬。第一次是1987年11月到1988年1月,此时临近1987年年度分红,静安指数曾上摸115点,随即又回到100点上下;第二次是1988年12月到1989年2月,也是临近1988年的发放股息红利,静安指数接近120点。
静安指数两次上扬10%~20%的幅度,完全是根据分红多少而定的,有些股票的涨幅还比不上派息的利润。以飞乐音响为例,50元面值的股票,1986年每股税后利润10.62元,1987年8.49元,1988年和1989年都是9.38元,赢利分别为21.3%、16.9%和18.7%。由此可以看出,股价的涨幅完全与利润吻合。在上海大多数股民眼里,股票与债券毫无差别。
虽然上海上市公司的获利不及深发展,不能像深发展那样导致示范效应,但上海上市公司的业绩仍然是骄人的。100元面值的股票,电真空1987年每股获利17.5元,1988年和1989年均为18.75元;豫园发行股票的当年,每股赢利是22元;大飞乐1988年每股利润高达26.66元。50元面值的股票,延中1986年每股利润8.13元,1987、1988、1989年连续三年均为7.5元;爱使1987年每股利润是8.44元,1988和1989年都达到了9.28元。然而业绩在股市里起到的唯一作用是,赢利多少股价就上涨多少,分红完,股价立即跌回原地,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精明”得太公平了。
不过再精明的上海股民也没法阻止股价下跌。自1987年放开股份后,下跌的次数多于上涨,1988年受“抢购风”影响,静安指数回落到105点;1989年4月受经济形势影响,静安指数跌破100点,此后一直运行于100点以下。从1989年9月24日到11月19日,静安指数跌到了历史性底部,最低为83点,直到1990年5月,才爬出100点。在100点以下,静安指数整整运行了一年多。
在如此低迷的市场里,从1984年底到1988年,上海股民那种深夜排队抢购新股的场面消失了,投资热情消失了,他们经过长期的等待,等来的却是死寂的市场,他们的耐心被消磨干净了。有一个故事很说明问题,沪市的“老八股”之一申华实业发行后还未上市,看到当时的股市(柜台交易)如此冷清,有不少人认定股票没意思,找到当时申华实业的董事长瞿建国,缠着闹着要退股票。瞿建国无奈之下只好动员妻子凑钱买下部分别人退回的公司股票。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即使不是原始股,只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买入申华股票,放到现在的成本价大概是每股一角多钱;把申华(即现在的华晨)股票十年来分红派息进行复权的话,实际价位超过1500元,更何况瞿建国买入的是原始股,无怪乎后来在他名下的申华股票市值达到2000多万元。这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当时上海股票无人问津的局面。
为避免重现深圳股票发不掉的尴尬局面,自1988年豫园商场发行后,管理层再也没有推出新股。没有新股,可老股还需要配股,那时股票发行还没溢价,所谓配股就是按面值增发新股。1989年上海电真空公司第三次增发新股,计划发行2200万元,可实际认购只有400多万元,1/5都不到,上海股民不再需要这种不争气的东西了。这个在全国来说最懂股票的地方,对股市失望与厌倦了。从排队认购到无人问津,上海股市走过的是和深圳股市截然相反的艰难之路。
与此同时,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遭遇了成立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得不放弃地价与租金昂贵的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小房子,搬到了偏僻冷落的西康路101号。西康路营业厅也只有两张长椅可供股民坐,每天来此交易的都是一些老面孔。交易方式很简单,两人在长凳上谈好价钱,然后到柜台上办理过户手续,一天下来,最多也只有几笔成交。没有股民热情的上海股市形同虚设,在风雨飘摇中奄奄待毙。
“北伐”:教一教“上海巴子”
深圳在1979年成为特区以后,经过10年的开放,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所以深圳人在内心有一种自豪感。就像上海人把外地人叫做“巴子”一样,深圳人把内地人统统叫做“北佬”,自然他们也不会把尚未开放的上海放在眼里,上海人在他们眼里也是“巴子”。
“去教一教‘上海巴子’怎么炒股票!”1990年,当深圳炒股狂潮掀起时,深圳股民中就有人情绪激昂地发出号召。5月初,一些买不到股票的深圳人开始“北伐”了。这支南方炒股大军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他们来到上海,悄悄进场收购电真空。1991年4月深圳证券部门向股民们发出了1200多份问卷,在回收的1060份问卷中,在最愿意投资的上海股票一栏,电真空排在了第一位。深圳股民懂得“擒贼先擒王”,习惯炒龙头股,他们把对深发展的情结移到了电真空上。而在上海人眼里,电真空是最讨厌的,不仅股本大,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增发新股,每发一次新股就使本来低迷的股市更加低迷。
1990年5月初南方炒股大军小股部队到达上海时,上海的龙头股电真空的股价正在面值以下运行,100元面值的股票当时最低的交易价是91.50元,按现在拆细来算,0.92元都不到。南方先遣军首先介入电真空,大肆收购,他们并不是看中其价位低,而是看中其龙头地位。在南方资金的介入下,5月底静安指数终于攀上了100点。当失望已极的上海股民习惯性地认为这次上升表现无非是即将中期派息,撞上100点准回头时,深圳的“北伐军”现身说法地向他们展示了股价一去不回头的惊人表演。
6月底,静安指数110点,7月23日,静安指数创出历史最高点123点。不是年底分红,怎么会创历史新高?面对这种景象,不仅上海股民愕然不已,上海管理层也吃惊非小。7月26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赶紧推出涨跌停板制度,即每天的涨跌幅为3%。
此时的深圳正在扫荡猖獗到几乎令城市瘫痪的黑市交易,大量被扫荡出来的股民,大包小包地扛着现金,浩浩荡荡地北上了。一支规模惊人的“北伐”大军汹涌而来。上海七只股票的股价顿时如受惊之马,脱缰而去。8月中旬静安指数200点,9月底300点。总共60万股都不到的上海股市,在南方军团庞大资金的冲击之下被扫荡一空。那气势真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一些在6月份以130元抛掉电真空的股民再也买不到股票了,100元面值的豫园股票,在每天3%涨停板的管制下,仅仅2个多月就爬上了400元,等目瞪口呆的上海股民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场内已经“有行无市”,他们必须到场外才能把抛掉的股票补回来,场内挂着400元的豫园,场外黑市价已突破1000元。
龙头股电真空这次真正展示了龙头的风范,从面值以下的92元一路飞扬,直破500元。“小飞”和“大飞”双双飞上了天,一个跑到382元,一个突破400元。申华和延中分别站在329元和242元的高处。长着翅膀的小“爱使”不是飞不高,而是流通盘太小,常常没有成交,所以有行无市地挂在206元,若不是每天3%的涨停板,真不知跑到什么价位,这还仅仅是场内价。
从场内的成交量也可看出南方资金的凶悍,从每天成交3万~4万元突然放大到500万~600万元,6月份的月成交量突破了3个亿。
这次上海人的精明被彻底淹没在深圳年轻移民的热血疯狂之中。但精明的上海人毕竟具有旧上海的金融底蕴,和南方军团相比,上海的股民或许只能以老年军团称之,他们没有年轻人的冲动与热血,可他们的确更懂股票,只是一时间被来势凶猛的南方军团打懵了。
南方军团教会了上海股民什么?是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供求关系。1990年9月,延中增发新股,尽管再三声明只有老股东才有优先购股权,但代理发行的申银证券公司门口人潮涌动,并非延中股东的股民也匆匆赶来,希望分一杯羹,道路被严重阻塞,公安干警大批出动,疏散人群。上海人又钟情股票了,因为那时的股票实在太少了。
从仓库保管员到国库券大王
1990年8月22日,正当深圳黑市第二次猖獗起来,而上海股价在南方军团的攻击下节节攀升时,突然传出一则令人惊奇的消息。世界证券业的权威性报纸,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麦健陆采访了上海的一位股民“杨百万”。这次在上海金谷园餐厅的采访,使“杨百万”成为知名人物。不久后麦健陆再次对杨百万进行采访,两个月内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两篇对他的专访,在英文标题《一个成了百万富翁的杨》下面,还刊登了他的照片。那副有点像中国内地老实巴交农民的憨憨神情,仿佛在说:“天下英雄本无主,今天轮到我坐庄。”
过了几个月,即1990年的12月16日,在“杨百万”设于上海海宁路的私人证券投资办公室,美国广播公司的驻京记者赵爱素也对他进行了采访。随后,美国之音、NHK、BBC、NEWSWEEK、CNN、加拿大电视台等众多的外国著名媒体都对“杨百万”进行了采访报道。台湾一家电视台花了几天时间,拍了一部关于他的专题片。外国的一些社会名流,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副总裁、波兰总统经济顾问等,也纷纷造访这位在中国股市里一夜间变成百万富翁的传奇人物。国内的媒体也紧紧跟上,纷纷报道。“杨百万”的名声犹如当时的上海股价,一飞冲天。请他去讲课的各地证券公司络绎不绝,沈阳财经学院则聘请他为该院的教授。
这个家喻户晓象征着中国股市第一批大户的“杨百万”,到底是何许人也?难道真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神话?
“杨百万”的真名叫杨怀定,20世纪80年代初,是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保管员,工作勤恳,恪尽职守,曾因一年为仓库增收节支30多万元而获得过嘉奖,冶金部的《冶金报》还登载过他的先进事迹。如果不是一次意外,他可能永远是工人队伍中的优秀一员。
意外发生在1988年的春节前夕,杨怀定保管的仓库失窃铜锭一吨多,价值近万元。事也凑巧,此时他的妻子在浦东承包了一家电线厂,为此厂方怀疑他“监守自盗”,于是公安局打电话要杨怀定去谈谈情况,到了公安局,把他“请”进拘留所谈。这对一位优秀工作者来说,当然打击很大。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审查与责难之后,失窃的第6天,窃贼再次潜入仓库作案时被当场抓获。可还了清白的仓库保管员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在他“平反昭雪”的那天,他的第一篇经济方面的文章《用活资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发表,这更让他百感交汇,心潮起伏。当晚他提笔写下了辞职报告,并和一张公安局破获这次盗窃事件的剪报一起,交给了厂方。辞职后的杨怀定一头钻进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报纸,靠报纸上得来的信息走南闯北,帮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推销电线,他推销掉的电线达几千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