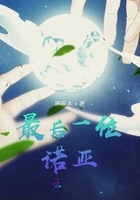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噩梦,女厨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我开始向她求饶,她只管摇头,我越是求她,我所求的事越使我觉得宝贵,同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也越大;最后我站着不走,求她饶恕我,她不听,拽着我继续向前走,我吓唬她说父母会为我报仇的,她就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她是全能的,我紧紧抓住路旁商店的门,抱住墙角的石头不放,她不原谅我,我就不肯再走一步。我拽住她的裙子往回拽,她要想迈开步子也不容易,但她还是拽着我向前走,一边走一边说,她非要把这一切告诉老师不可。时间不早了,雅各布教堂上的钟敲八点了,学校的铃声也响了起来,其他孩子开始向学校跑去,我一向最害怕迟到了,于是我和女厨也一起向着学校猛跑,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嘀咕:"她肯定会报告老师的,不,她不会报告的"--的确,她没有报告老师,她从来也没有向老师告过我的状。但是,她一直都有可能去告状,而且这种可能变得越来越大,她老是说:"昨天,我没有报告老师,今天我非告不可。"她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可能性的。有时候,她被我气得在大街上直跺脚,有个贩煤的女商人偶尔会站在旁边看热闹。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桩趣事。一方面,它反映了一段可怖的童年经历,这种经历中常常有一个人处在权力中心,向其他人发号施令,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童年的阴影往往会伴随这些人走过一生。另一方面,它反映出卡夫卡很可能是一个被宠坏的、难管教的孩子,必须靠一双强有力的手才能把他制服。他大概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因为即使从家到学校的路程不远,也一定要有专人护送他上学。再换一种角度,我们会发现它体现出复杂的阶级和种族矛盾。女厨无疑是一个捷克人,她同许多捷克人一样,在富裕的、说德语的犹太人家中帮工,而年幼的弗朗兹卡夫卡则是这户人家的命根子。贩煤的女商人尽管只是在附近旁观,但她很可能注意并理解了这一点。也许两个女人之间曾经有过会心的对视,而弗朗兹卡夫卡那时还是个孩子,对这些可能毫不在意。
当赫尔曼卡夫卡来到布拉格经营自己的事业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作为一个来自外省、来自捷克农村的移民,他本来应该是捷克人。但在那个时期,波希米亚地区尤其是布拉格的政治和种族冲突十分严重,因此这就涉及到向哪个国家效忠的问题。赫尔曼原本信奉犹太教,但他注意到,只有同那些富裕的、说德语的犹太精英(他们在布拉格的商业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站在一起,他才可能有远大的前程,因此他渐渐变得对犹太教不太热心(这一点后来受到了弗朗兹卡夫卡的谴责)。赫尔曼给家中的六个孩子全都起了德语名字,并把他们送进了德语学校,根本不考虑捷克学校--当时只有百分之十的犹太孩子上捷克学校--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孩子所属的阶层也就确定了。
19世纪末,奥地利所属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包括布拉格市在内,经历着一场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由此引发了局势的变动,各种冲突不时诉诸于武装斗争。在当时,波希米亚是这一地区的工业基地,当地的产业工人通过组建工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无产阶级群体。一股泛德国民族主义情绪逐渐苏醒,相反的,捷克民族主义情绪也日趋高涨。两大派别之间的冲突十分频繁,冲突发生后往往需要动用奥地利军队才能恢复社会秩序。卡夫卡年轻时,布拉格直接隶属于维也纳。反犹太主义在青年捷克党内盛行,成了捷克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当时的工人清一色都是捷克人,而他们的老板又都是犹太人,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
在法律上,奥地利帝国逐步减轻了对境内犹太居民的限制,一大批犹太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赫尔曼卡夫卡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捷克语的犹太人曾经发起过一场运动,赫尔曼卡夫卡也参加了,加入了海因里希巷的犹太教堂董事会,这个董事会首次倡导在布拉格犹太教堂中用捷克语做礼拜。但是,不久之后,赫尔曼就投身于说德语的犹太人群体当中了。尽管如此,在1897年11月爆发的布拉格反犹太主义暴乱中,他的店铺仍然躲过了一劫,原因是暴民认为他是捷克人,没有把他当作攻击目标。关于此事流传着一个不足为信的说法,据说当时暴民们曾在旧城区的卡夫卡店铺外有过片刻的踌躇,这时有人大喊:"不要动卡夫卡的铺子,他是捷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