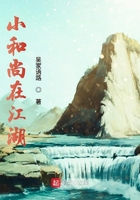“谁说的!”邵良辰微一用力,将身上的铁链全数震断,怒道,“这些人无礼至极,可是功夫不错,能和我走二十几招的龙门派弟子还真少见,你是谁?”
邵良辰酒意微醺,说出的话大大咧咧,完全没见到任飞云不住的向他使眼色。那黑衣首领惨笑一声,道:“我是谁?只是一个欠了人情,只怕这辈子也还不完的可怜虫。”说完,看着吴老刀微微点了点头,喜笑颜开,随后左掌一错,使出摩云手的“力拔乾坤”,空气中微微颤动,只见他的左手聚集起一股霸道的劲力往右手上抓去。
黑衣首领一咬牙,硬生生将自己的右手卸下来,痛的在地上嚎叫不已。其余的人众也纷纷拿刀自残,切下自己的手指。场面血腥,令任飞云,邵良辰瞠目结舌。
吴老刀封住黑衣首领的几处大穴,冷冷道:“此事作罢,滚吧。”黑衣首领如获大赦,带着受伤的属下灰溜溜的消失在夜色之中。
吴老刀恭敬的说:“让任先生见笑了,我主人治下一向严谨,对于犯错的手下采用这种教训的办法,也是让他们听从号令,以免的下次不再出错。”
邵良辰道:“这种惩罚手段倒是新鲜,除非他有三头六臂,否则怕是不够用啊!”
任飞云道:“走吧!”
吴老刀一声呼啸,一顶华丽的软轿从不远处的巷角冒出来,任飞云嘱咐邵良辰小心为上,转身上轿,随着吴老刀到了留欢楼。
任飞云见留欢楼门庭冷落,几个粉头有气无力的甩着膀子,见着任飞云,哭天喊地,撒起娇来。
“怎么了?”任飞云捏着一个叫盈盈的女孩的脸蛋,柔声问道。
盈盈抱怨道:“都是他们,愣是将今晚所有的客人都赶走了,这让我们喝西北风么?”
吴老刀冷眼旁观,咕哝一声,欲言又止。他给了这家老鸨不少银子,谁知道那老鸨有没有妥善安置姑娘?
楼上鼓乐的声音响彻河间前门大街,虽已是深夜,但河间向来不太平,这等烟花场所的嬉笑怒骂周围的百姓早已见怪不怪。当任飞云挽着众美女正要上楼,街角又来了一座软轿,式样和排场倒是和任飞云起先坐的那架不相上下。
轿子一落地,一股淡雅的莲香从轿子中散出来。随后从楼中出来四个美貌的丫头,掀起轿帘。一个白净娉婷的少女坐在其中。
只见这女子约莫十五六岁,体态风流,婀娜多姿,虽不似西门无双那样国色天香,却也有小家碧玉的清新脱俗。这女子给人一种很安静,很自然的感觉。
那女子向任飞云盈盈下拜,极有礼貌的缓移莲步,在四个丫头的搀扶下进了留欢楼。
女子逛妓院,今天真稀奇,任飞云跟在女子的后面,也上了楼。
铁面人依旧戴着他的面具,正兴高采烈的和一些河间的江湖名士举杯畅饮,这些人无不战战兢兢,汗流浃背,似乎相当畏惧铁面人。这些人中,也只有毛勒神情自然,还时不时的说些笑话暖场。
铁面人一见任飞云到了,快步走上来,拉着他的手,道:“几天不见,小友的功夫又长进了,不过瞧你这样子,却是不怎么好啊。”
任飞云道:“此事不提也罢,我倒是想问,认识你这么久了,你始终戴着副又丑又怪的面具,夏天不透风,冬天冻死人,你不难受么?”
铁面人抚掌大笑,从未有人对他这么说话,这任飞云胆大包天,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行为,让在场的许多人摇头叹气。
铁面人的声音变得阴冷,道:“若是寻常人这么对我说话,你可知道他的下场?”
任飞云自从见到他起就知道这铁面人武功深不可测,而且下手毒辣,从不留情,但始终相处时日很短,这人究竟是谁,有什么脾性,任飞云一概不知。
铁面人指着一脸白须的焦公赞道:“焦老头,你给我这位小友介绍介绍我是谁?”
焦公赞一听,立即魂飞天外,立马跪下,那天豪迈的性子登时不在。“这……这位袁先生乃是,乃是当今天下,最了不得的人物,为人急公好义,侠肝……”
“你是不想活了?老子要你如实说来,谁要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铁面人厉声吼道,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焦公赞的后脑勺,随时一掌毙下。
焦公赞急忙道:“是是是,阁下名叫袁无义,江湖人称嗔残道人。”说了这些之后便不敢再说了。
“你也配活这么长的时间?当真是江湖中的一个奇迹。不过也还算老实,滚吧,从这门滚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焦公赞如获大赦,连滚带爬冲出留欢楼,脚下轻功步法稳健如飞,巴不得生的一双翅膀,立马离开这不详之地。
任飞云暗暗好笑。
这叫袁无义的铁面人说道:“你晓得了吧,老子叫袁无义,无情无义,我行我素。谁要是挡我的路,便是死路一条。”
说罢,他向这些人横扫一眼。众人连连称是,点头哈腰,面如土色。
“毛勒,你过来。”袁无义挥了挥手,将毛勒叫到跟前。
“义父。任兄。”毛勒向袁无义和任飞云深深鞠了一躬,为人诚恳,完全不像是当日酒馆中庸庸碌碌,气派嚣张的摸样。
任飞云心念一动。
“我也不必介绍了,你们两个怕是早就熟识了,毛勒这小子捡了块宝,适才还向我提起这件事,后来才知道,竟然是我的任小友。呵呵,真是缘分,人世界什么事情为什么都这样巧合?”袁无义洋洋洒洒,气象庄严,在这个主厅中,他的话就是权威,他好像就是这里最强的存在。
袁无义奚落道:“飞云小友,我是个说话实实在在的人,今天竟然都是朋友,那我就实话与你说了。”
袁无义指着此时的毛勒,道:“别看这小子平时装的暗弱不堪,实则绵里藏针,一肚子坏水。这小子自知才干不如你,便想出了以你为幌子,吸引连万里与孙见霄的攻势,自己暗地里纠集人马,试图全盘通吃。”
任飞云自然是个精细人,却也丝毫没看出来,此时一想,暗笑自己当时确实天真,恐怕也是因为自知命不久矣,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也就不想去理会。
“谁知道你日后的作风实在令我这义子出乎意料,你简直是他见过最厉害的经营人才,你将盐引牢牢抓在手里,甚至用了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就将云阳的规模发展的空前繁荣。”袁无义缓缓说来,倒像是闲话家常。
“那毛兄下一步要怎么办呢?”任飞云好奇的问道。
毛勒微微一笑,说道:“自然是除掉你,和效忠你的所有人,我不能让我父亲交给我的一切落在别人手里,虽然我很感激你,但那不代表我会放过你。”
毛勒表情真诚,不像作伪,任飞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无奈与自责。
“其实这一切也都是宿命,我没有才干,本不想继承父亲给我的一切,但这都是父亲的心血啊,父亲膝下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云阳!是父亲一生的梦,一生的追求,我决不能让它毁在我的手里。”毛勒神情激动,“任兄你确实是我钦佩的一个人,你赈济灾民,壮大云阳,使得上下一心,外抗连城、苏杭这两个我最憎恨的敌人。但我却不得不使用先父遗下的‘中州契约’,请来我义父杀死你,因为相比其余两家,你的威胁确是最大的。”
任飞云犹如被一桶冷水当头浇下,他苦笑两声,怒道:“谁稀罕你的云阳,老子本就命不久长,若是要你拿去就是,何必耍这些鬼花招?朱胜才一干人却是好人,你也要赶尽杀绝?”
任飞云怒目而视,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你真是可悲!”说罢就要出去。
袁无义将任飞云拦住,任飞云怒道:“怎么?你要杀我?那就动手吧,大高手!”
“生气啦?你可真不禁逗。”袁无义语气中满是温和,好像在哄一个生气的孩子。
任飞云道:“一群神经病,你将他的计划说给我听到底是为什么?讥讽我?奚落我?你我见面不过两次,萍水相逢,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袁无义看着任飞云的脸,颤抖的说:“萍水相逢?不,你我认识何止一两天,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的母亲是谁,你两岁我就抱过你,你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尊敬人。我岂容得这无能的小子来伤害你。他配么?”
任飞云心头仿佛被重重打了一拳,一切仿佛都混乱了,认识?我和这个人?他是谁?
“你……是谁?知道我的什么事?”任飞云抓着袁无义的手,言语激动,“我是谁?我母亲是谁?为什么我会不记得十岁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我从哪里来?”
袁无义看着任飞云,试图让他冷静下来,看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怒道:“你们全都滚出去,我让你们进来再进来。”
随着这些人一一出去,袁无义道:“叔叔现在就将你的身世告诉你。”
任飞云跪在地上,神智变得恍然,眉头一皱,点了点头。
“在告诉你的身世之前,先告诉叔叔赵丹青在见到你之后和你说了什么,或者给了你什么东西没有,这十分要紧。”
任飞云正要说出口。突然,心中一片冰清,雪兰袈裟的毒素在此时发作,他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
茫茫的雪山之上,又是同样的场景。很冷,这里鸟兽绝迹,严寒刺骨,似乎世间的一切在这里毫无踪影。时间在这里停逝,空间在这里漫无目的的变得飘渺。突然,一阵铃铛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伴随着歌声,好熟悉的歌声。
一个眉目和任飞云极为相似的女子,那是她的背影,温暖,母性的温暖。一时间,任飞云热泪盈眶。娘!他想伸出手,抓住他的母亲,可是积雪很深,路很窄。他的手变得很小,步履缓慢,他回到了十岁之时。
他哭喊着,大叫着,母亲的身影越走越远,只有那悠扬的歌声和清脆的铃铛,以及心间无尽的痛苦。
接着便是战火纷飞,尸山血海,他在痛苦的边缘爬到一处静谧的地方。
这里,一个瘦弱的小孩将一个肮脏的馒头掰成两半,“老子叫沈义和,天下的穷孩子都是一家,这半个馒头便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