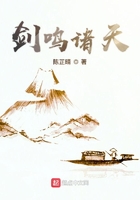一连七天,他站在那不远处的山巅上,吹响那曲《凤凰引》。准确说,他花了七天的时间 ,将一首曲子完成。他说过,她是这世上第二个听见这首曲子的人,而他是第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听到。所以他要将之完成,吹完给她听。
曲子完成的时候,世界蓦然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一点一点呼啸的寒风凝聚变成肃杀。冰雪过后,天空被打开,映照的却是五彩的颜色,一如她割破手心时候,幻化出来的凤凰一样的艳丽,鲜血,以及生命的味道。
“这就是引凤。
“都怪你,为什么要立那样的誓言。
“我只以为我会一直恨你,你也会一直恨我,那么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简简单单的活着。
“我终究还是记住了你,并且放不下了。我背弃了我的诺言,但是却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可以去杀了你。
“可是你又何必记住我呢?
“我们记得了对方,便只有杀了对方,然后自杀。因为我们害怕忘记。你做到了,可是我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啊!”
那涣然而逝的容颜,现今还清晰地保留着。仿佛并不曾失去,因为那一首歌一首曲的缘故。纵然不会有人知道。
此生与君共,莫道君不知,不求偕白头,只愿死生同。
此生与君共,不忍君离别,瑶山路太远,携手相与渡。
凤凰绕飞,五彩的霞光,影在溘然长逝的时间身上,又匆匆从指间流走,散碎了满地。
往前走,山渐渐变得高了,没入云端,仍旧孤独的站立。
山上草木葱郁,依山体绵延层叠而下,冲开一道道幽深的涧谷。山脚东南面有家茶肆,是专供这一带往来行人口渴歇脚之用,但店家只提供茶水,从不供给饮食,若要止宿,须得上二里外的客栈。
茶肆依山而建,沿山一字拉开,成为一条长长的廊子,两列茶桌也一字而成,中间留出一条长长的过道。
南宫婉卿在茶肆里坐下,自一个月前,她拣了那张靠窗的桌子,一连一个多月,每天,这张桌子便见不到第二个人的身影。从窗扉过屋檐望出去,恰恰把这一面山全看在眼里,山顶的云雾,近前的露水,那些深深浅浅的,一件件都看得仔细。
桌子上只留下她一个人的影子,每天如此,早上来,晚上离开,一坐就到了傍晚山阴。要过来一杯清水,一大块银子,只在那里坐着,却忘了要茶。穿过屋檐,一直望着,也一直坐着,想是在等人,却总不见人来,不知望着什么。
这下倒让店小二高兴不过来了,跑得比平时快了好几倍,水壶都被提得发光了。一杯清水就值大块银子,天底下再没有这样便宜的人了。每每见她这样望,禁不住好奇起来,对他来说,眼前的这个人就是用乱丝缠住了的迷,翻尽肝肠,也解不得半点头绪。俯下身子,斜眼向上望去,以为有什么好看的新鲜,只见到檐头挂了张蜘蛛网,中间破了个大洞,却不见得蜘蛛。这叫他大失所望,再不做第二次张望的举动了,但还是很殷勤的招呼着。
昨夜下了一场雨,山里不同于城市,清爽的空气里杂带了一丝腐烂后的甜腥味,空气落下来,停在草叶上变成露水,露水渐分散成雾,雾又飘散在空气里。透过雾看前面的山,就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了。
婉卿坐在桌旁,端起水,环顾了眼四周,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坐了四个人,两个须髯大汉,一黑一黄,一个青巾书生模样,手里摇着一把扇子,另外一个是少妇,穿着红艳艳的上衣,脸上妖媚丛生。四人围着一张桌子喝茶,没有人发出半句声音,眼睛四处转溜,似乎是各不相识的,小心翼翼的防备。只剩下旁边桌子上还伏着一个男子,半醉半醒,身软无力。时间还很早,坐在这里的人,多是早行的路人,通常他们是各行各的道,彼此不相关。
婉卿将水送至嘴边,忽然听到那四人小声的嘀咕,声音虽低,但已足够听得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