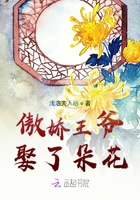胡子和秃子在巴黎有一个发小,叫蛋蛋,蛋蛋如今是巴黎最牛的华人艺术家之一。
蛋蛋请胡子和秃子去他郊区的家,地铁都快开到地狱了—就那么远!
胡子:来你这儿,感觉巴黎比中国还大。
秃子:我觉得比从中国去美国还远,不是说你丫发了吗?
蛋蛋:这里是高尚社区,发了的主儿都住这儿。
蛋蛋住在仓库里,就像798的那些大厂房。
蛋蛋妈妈特地给他们炸了花生米,还拌了黄瓜。那黄瓜比倭瓜还粗。
哪儿的黄瓜都没有北京的好吃。蛋蛋妈妈说。
小酒喝上了,大天儿聊起来。
大志他妈咋样了?
我们给送回他爸那儿了,好像俩人要复婚。
想再生一大志?
相依为命吧。
估计这回真能白头偕老了。
天命。
咱别说这事儿了。
好,喝酒,喝酒。
哎,听说国内摇滚乐现在火了?
你听谁说的?
媳妇儿回去看过两场,说都爆满,而且小孩儿巨多。
火个屁啊,星星之火都算不上。战场主要还是在酒吧,倒是有几个新的LIVE HOUSE还不错。市场还没出来,估计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有些新乐队也还行,基本上全世界有什么,中国都有了。
那你还不转行啊?
不转了,它不火,我倒觉得还有意思,边缘才有力量,如果像英美那样主流就毁了。
这才是屁话!音乐的力量在于表达,听的人越多,才越有力量,才能影响别人,才能传达思想。
影响别人干吗,自己高兴就得了。
我真不理解,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学会说真话。
我也觉得,我也和丫说过无数次了。你说披头士、滚石牛逼,人家多畅销啊,畅销才有影响力,畅销也没影响人家的思想性啊。
丫有时候太轴了,要不就是生锈了。
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孺子没法教,朽木你咋雕?
去你大爷的。
这话听着有点儿娘娘腔,现在女的才说去你大爷的呢。
那男的说什么?
男的现在基本都不吭声儿了。
三个酒杯撞到一起。
蛋蛋妈妈走过来,坐下。
你们都结婚了吧?
没,没敢。
老大不小的,家里不着急啊?
我妈好像也不太希望我结婚。
为什么?
觉得我不适合吧。
他妈是怕他糟践人家闺女儿。
别当着阿姨面儿胡说,影响不好。
阿姨没事儿,就是你们真得抓紧,别太挑了。
他们哪儿还有的挑啊,他们都是被人家挑剩下的。
你闭嘴。那你们有女朋友吗?
没。
没正式的?
什么叫正式的?
就是处对象的那种。
那不正式的是什么?
妈,你别问了,他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就是要问,你们哥儿仨一起长大的,你有老婆孩子了,别在这儿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对,蛋蛋一贯如此,要不是我们来巴黎找他,他肯定不会理我们。如今他是有儿子的人了,不一样了。
胡说,蛋蛋可不是这种人。
阿姨您不知道,他就是这种人。前一段儿燕子回国,他都不让她找我们。
他那是怕你们两个小混蛋把他媳妇儿给戗了,在巴黎找个媳妇儿不容易。
阿姨您别当真,我们开个玩笑。
我从来就没跟你们认过真,否则还不得把我气死。给我倒杯酒。
您还能喝啊?
你们仨绑一块儿的量,也就是我的瓶子口。
蛋蛋妈妈原来是北京卷烟厂的工程师,酒量大得惊人。蛋蛋小时候就老跟人说,原来千杯不醉不是神话,我妈就行。
蛋蛋妈妈倒了酒就站起身。
你们哥儿仨好好聊吧,老没见了。
转身走了。
你妈真知趣儿。
我妈懒得搭理你们。
她现在还那么能喝?
酒腻子。她不能看见酒,一看见好酒就拿走藏床底下。
英雄的母亲啊!
母亲英雄儿混蛋。
蛋蛋,混蛋的蛋。
燕子回来了。
燕子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狐媚,燕子像一朵芙蓉刚出水。
燕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哪样啊?
样儿大了。
滚!
这一声“滚”竟然吹气如兰。
胡子难道这么快就想玲子了?又来个吹气如兰的!
真的好清纯,不像我们认识的你了。
像一个穿短裙扎辫子的高中女生。
怎么脸还红了?奇迹!
燕子的脸像燃烧的庄稼地,呼啦啦就红了,红得像情窦初开的少女,少女般无邪。
真是怪了,蛋蛋给你吃了什么药,把一个天生辣妹变成了乖乖女。乖乖!
燕子用手去扑打胡子和秃子,柳条一般轻盈,竟好似拿腔拿调一般,又毫不做作。
岁月改变人,三十的姑娘一朵花!女大三十变,越变越好看。
蛋蛋已经把整个脸变成一个笑容,笑得已经没法儿再笑了,那叫一个幸福!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蛋蛋的脸蛋儿上!原来这世界上真有幸福啊?!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希望,只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希望,都还在那白茫茫、空旷旷的田野上。田野好寂寞,寂寞也如歌。
因为看到了幸福,于是伤感突如其来。
伤感在胡子和秃子心中是深刻的,深深刻在心上的。两个走南闯北历尽风霜的老混混,心底结满寒冰。泪水逐渐涌上眼眶,眼眶顿成泪湖,湖水清
且涟,荡漾着落日的孤独和晚霞的余晖。那个可以铭刻在心又可以终身厮守的爱人在哪里?悲情也似水,滚滚长江东逝水。他们真的需要一个终身厮守不离不弃的爱人吗?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倦鸟知返,他们早已疲惫不堪,但依然乐此不疲。人啊,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
胡子和秃子突然间一起发出一声轻叹,那声音虽然浅淡,但意味深长,直逼得苍山倒立沧海横流。那两声轻叹,吐出了无限哀怨,就像一个小女子的自怨自怜,有着无尽的缠绵悱恻。有时候男人比女人更脆弱,如果女人是张纸,那么男人是比纸还薄的纸,男人甚至无法被书写,男人是一种轻薄的声音而已。
我喜欢摇滚乐,但可悲的是我竟然只属于它,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不属于任何人。说摇滚乐是我一生的情人挺酷的,但谁他妈想要这么个永远愤世嫉俗的情人啊?!我有那么多记名和不记名的情人,可没有一个真正属于我,我无法接受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成为我的爱人,她们无法替代摇滚乐。其实我知道,摇滚乐是可以替代的。
没有什么是不能替代的,除了爸妈。
还有老婆。
燕子已经完全地缩进蛋蛋的胸怀,蛋蛋的胸怀看上去十分广阔。
在高谈阔饮和无限的怀旧中,几个朋友终于喝高了,高到可以摸着天,抓只老鹰当下酒菜。
蛋蛋,你如今行了,还记得你和燕子好,是我们俩做的局吗?
什么?
燕子你不知道,当初是我们哥儿仨挖的坑,引诱你跳井的。
怎么回事儿?
别听他们胡扯。
谁他妈胡扯,你给燕子讲讲。
秃子给燕子讲故事,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燕子本来是软软的一个朋友,因性格泼辣却国色天香,被她的闺蜜们称做“朝天娇”。
燕子的性格里除了泼辣,还携带着极强的刚直成分,而且极易冲动,完全和她的娇美容颜不配合。秃子、胡子、辫子很快就和燕子打成一片,号称“四子”,但他们仨谁也没对燕子动过心,他们觉得燕子是上天派来挡在他们和软软中间的一道屏障,一道锦绣屏障,既然他们无法取悦软软,那么透过一道美丽的纱帘与软软对望也是好的。一般来讲,男人绝不会轻易放弃眼前的美女,更不会对眼前的美女熟视无睹,但因为软软在这几个男人心目中的地位实在太特殊、太神圣了,以至于一叶障目,他们几乎忽视了燕子的无边美貌。这对燕子很不公平,而软软对他们又哪儿有公平可言呢?直到有一次在郭林家常菜聚会,蛋蛋第一次见到燕子,立刻惊为天人,把那哥儿几个都说傻了。蛋蛋说:谁家的果实如此丰满?北京城第一小尖尖啊!
男人经常会陷在一口井里,看不到别样天。
那天的酒蛋蛋喝得欢天喜地,而秃子、胡子、辫子却喝得格外郁闷,连软软都看出事情不对了。
蛋蛋苦求大家做说客,促成他和燕子。刚醒过闷儿来的哥儿几个,心里八千个不愿意但也没辙,什么叫朋友?有那么多朋友有啥用啊?但朋友还就是朋友,心里七荤八素,嘴里却甜言蜜语全是奉承话。胡子说蛋蛋是梵高,尚躲在深闺无人知,但假以时日终成大锅。秃子说蛋蛋前不见古人,后没有追兵,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旗他一个人扛了。辫子说就一个字丫牛逼。燕子完全被忽悠了,目光都闪烁了。于是换座位,蛋蛋如愿以偿地牵了燕子的手。
那天晚上喝得那叫一个大,一口痰比湖大,一滴酒比海深,一寸目光杀死满地蚂蚁。蛋蛋既然已经牵了燕子的手,也就完全放开了,他喝得比谁都大,大过他的曾祖父他妈的曾祖父。他想撒尿就往门外跑,然后转身,冲着餐厅的大玻璃,掏出宝物一通儿狂射,直看得所有食客目瞪口呆,把新近女友燕子的脸当墩布擦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秃子、胡子、辫子和软软在大惊失色后突然狰狞地放声大笑,似武林豪杰,冲天酒气一扫而光。
燕子乐了,蛋蛋乐了,胡子和秃子也乐了,巴黎的郊区乐翻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