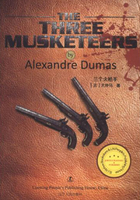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高志航赶到笕桥航校机场时,学员已经排成三队,坐在小凳上了。
高志航来到学员们面前站好,他往下边看了几眼,这才清理了一下嗓子说:“今天的射击课,我拿到室外来上。很多学员可能不认识我,本人叫高志航,字子恒,吉林通化人,以前是东北军的。如果再介绍下去,可能会让大家失望——我的右腿比左腿短了将近一公分,是个瘸子。”
学员们纷纷探头看,特别是藤野轮宽、李桂丹、阎海文和沈以琴这几个人,脸上露出惊诧的神情。高志航对着下边大声说:“如果有人想看,我可以展示给你们看。”下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喊叫起来:“想看。”这人的声音刚落,又有几个人跟着喊起来。
高志航脱了皮靴,只穿袜子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他说:“我知道你们怎么想,就凭我这条残腿,别说当教官,当飞行员都不够格。但我告诉你,只要我上了飞机,我就不是我了。我用翅膀飞,不是用腿走路。”高志航说完穿上皮靴,又站到学员面前,开始讲课。
“今天的课,讲空中的机动性。这是一切战术和技术的基石,你这个搞不懂,到了天上只能挨打。我总结出的八字秘诀是:观察、决定、攻击、脱离。有关战斗转弯、转弯空间、转弯圆环等,前面老师讲过,这里不说了,有关方位角、角速度、转弯半径的计算、如何摆脱和利用地心引力,我也不说了。我今天就讲一条原则:在一对一的空战中,要努力保持进攻状态。具体说,飞机上的机枪是在机头上,所以你的机屁股最好不要朝向别人的机头,而是相反,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机头对准别人的机屁股。”高志航在身边的小黑板上画了个图,他指着图上后边的那架飞机,“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祝贺你,你基本上胜券在握。”
高志航讲到这里,下边有人唧喳私语着。他冲着声音响起的地方说:“有谁怀疑这条原则吗?”这时李桂丹站起来说:“高教官,这个道理好懂,但做不到,你敢保证你的机屁股不被别人咬住吗?”
高志航看着李桂丹,坦诚地说:“不敢。干我们这一行,就像一辈子都要下矿井的矿工,他绝对不敢说每天都会活着回来。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其中的任何两个人打赌,你最多只能咬住我20秒钟,也就是说,不等你瞄准射击,我就会脱身,反咬住你的屁股。有人敢赌吗?”
李桂丹往前走了两步,问高志航赌什么,高志航把手摊在胸前说:“随你的便。”藤野轮宽也站了起来,边走边说:“我也算一份,我们赌咱们三个人的表吧。”高志航问:“你们两个什么表?”李桂丹说他的是块怀表,藤野轮宽说他的是西铁城。高志航笑了笑说:“那我吃亏了,我这块帝陀表是瑞士名牌,还是在法国买的。”
三个人说定了,学员们都来了精神,想目睹这三个飞行队中的高手一决高下的场面,于是纷纷从座上站起来,有的人在小声地猜测起他们打赌的结果来。
在众人的注目下,三架战机相继滑过跑道。高志航驾机在云层里搜索。李桂丹突然从高处俯冲而下,高志航迅疾爬高,两个人的飞行轨迹成剪刀差,追逐行进。高志航的战机几次出现在李桂丹的后面,他在空中对李桂丹喊道:“你已经被我击落两次了。”李桂丹却不服输,他一个鹞子大翻身,突然出现在高志航的机尾。他也朝高志航喊道:“这一次你逃不掉了!”
高志航被李桂丹死死咬住,渐而逼近着。突然,高志航向横侧来了个滚翻,把处在高速状态中的李桂丹甩去了前面。等李桂丹拉起战机时,发现高志航鬼魂一般在自己的身后抖擞机翅。
李桂丹一脸沮丧地离开了,向远方滑去。这时藤野轮宽的战机出现了。学员们都兴奋起来,高呼着,看着两架战机在空中搏斗。它们忽上忽下,忽聚忽散,翻云覆雨,演绎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追逐战。
三架战机降落后,高志航、李桂丹和藤野轮宽三个人来到队伍面前。学员们把他们三个人围在中间,李桂丹宣布这次打赌的结果,他说我和藤野教官都输了。高志航立即摆了摆手,补充道:“公平地说,我和藤野教官应该是平手,因为我三次咬住他,都让他逃掉了。”藤野轮宽却低着头说:“不,还是我输了,高教官多给了我两次机会。这要是空战,我第一个回合就应该被击落了。”
在众人的哄叫声中,藤野轮宽摘下自己的手表,给了高志航。李桂丹也很不情愿地掏出他的那块怀表。高志航看了李桂丹一眼,说:“什么破表,我不要。”高志航又摘下自己的手表,把藤野的表戴上,把自己的这块递了过去。藤野轮宽推辞说:“这不行,愿赌服输嘛。”高志航的手固执地伸着,说:“打赌只是个形式,我们互相留个纪念吧。”
藤野轮宽犹豫了一下,还是欣然地收下了高志航的表。他像其他学员一样,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地听完高志航的全部课程。
晚上下班后,高志航走进家门,就大吵小嚷地喊起来:“亲爱的,我今天和日本王牌交手了。”他喊叫了两次,没听到有人应声,便扒着里屋门往里看一眼,见航空总署两名军官正在客厅和葛莉儿谈话,一下愣在那儿了。
“高教官,我们奉总署的指令,找你夫人调查一些情况。”为首的军官说。
高志航迈进门槛,急着问:“哪方面的情况?”另一个军官对葛莉儿说:“对不起,你能回避一下吗?”葛莉儿回到卧室,那个军官对高志航说:“其实很简单,我们想知道你夫人此前的经历。”高志航疑惑地看着那个军官,说:“这很重要吗?”两个军官交换了一下眼色,为首军官说:“我们出去谈吧。”他们来到门外,为首的军官说:“高教官,你可能不知道,总署有一条特别规定,飞行员不能娶外籍夫人。”
“我现在是教官,不是飞行员。航校有好几位外籍教官,更不要说他们的夫人。”高志航满不在乎地回答。
军官摇着头说:“你和他们不同,他们是临时聘来的,不受总署规定的制约。你能保证今后不再驾机吗?”
“我闹不明白,你们可以聘外籍教官,我就不能娶外国女人?再说我是在东北军结的婚,那个时候总署的规定管不着我。”高志航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那个军官很认可也很同情地说:“你可以钻的空子也就是这个了,祝你好运。”
待总署军官走后,葛莉儿抱孩子跑出来,她急切地问:“他们和你说什么?”高志航只淡淡地回答道:“没什么,是例行调查。”葛莉儿观察着高志航的神色,有些担心地说:“不对,你好像有事瞒着我。”
“他们觉得很好奇,问我为什么娶了个俄国媳妇。”高志航进一步解释着。
葛莉儿听后信以为真,孩子般地问:“你怎么说的?”高志航只好强作欢颜地说:“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葛莉儿竟然笑得花枝乱颤,说:“我们真是心有灵犀,我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问谁是我们的媒人,我说上帝。”
事情虽然被暂时搁置起来,但高志航的心一直悬着,他尽力抽出更多的时间陪着葛莉儿,他们也确实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在高志航一家刚刚团聚不久,周至柔来视察笕桥航校了。他在毛邦初的陪同下走进会议室,早就坐好的军官们纷纷起立。
周至柔永远保持着他特有的笑意坐在主席台上,他向下边轻柔地挥了挥手说:“坐吧。我这次来,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明年的10月31日,是蒋委员长五十华诞。国府大员几次开会研讨,准备做一篇大文章,那就是借助我们空军的航空表演,在全国搞一次祝寿活动。帖子已经发出去了,世界几个空军强国,像美国、苏联、德国、意大利、英国等,都很感兴趣,要派王牌飞行员来参加我们的祝寿表演。最有意思的是,日本人虽然没接到我们的帖子,也想来,我们一口回绝了。想来祝寿的国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来想展示他们的实力,二来嘛,想掏我们的腰包,买他们的飞机。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比较一下世界各国的飞机,也好做日后军购的参考。这样一来,我们委员长的心事重了,前天深夜在他的官邸召见了我,上来就说,‘发给各国的帖子,可是以我蒋中正的名义。’诸位,你们明白委员长的心思吗?”周至柔有意把话顿住,目光徐徐扫过会场,视线落在毛邦初身上。他问道:“不知毛总队长有何考虑?”
毛邦初立即站起来,面带激动地说:“本人受命以来,一直夙夜难眠。我和同僚研究了不下十几个方案,窃以为,最为出色的构想,是出动50架飞机,在空中编队飞行,布成两个方阵,四个大字,一个方阵是中正,一个方阵是五十,这个机密不可泄露出去,我想届时一定会给全国同胞一个惊喜。”
周至柔微微点头称赞,说:“难为你一片苦心,只是时下全国一片抗日救亡的声浪,过于铺排,会不会授人以柄,给委员长带来微词?”毛邦初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他压低声音说:“我这个想法私下给委员长透露过,委员长是点了头的。”周至柔哦了一声,脸上的笑意飘走了,立即浮出一种不悦之情来,他扫了毛邦初一眼,声音冰冷而坚硬地说:“此等大事,以后要先报给我和蒋夫人。”毛邦初看到周至柔当众给他脸色看,也有几分尴尬,他扫了一圈在座的各位,见大家都在愣愣地瞅着他,便很不情愿地小声说:“是。”
周至柔拿过跟前的茶碗,轻轻揭开盖子,小心地呷了一口,语气也随着热水温暖了点,他说:“委员长私下也跟我交代过,他更看重各国飞行员的特技飞行表演。”
“我想过,各国来的都是王牌飞行员,我们没有足可匹敌的人选,如果勉强派员参加,技逊一筹,会贻笑大方。与其如此,还不如放弃。”毛邦初边表达自己的想法边观察着周至柔的脸色。
“不妥吧,堂堂中华,泱泱大国,又是东道主,连个特技表演的人都找不出来,西方列强会怎么想我们?日本人会怎么想我们?全国同胞会怎么想我们?最重要的是,委员长会怎么想我们?”周至柔边说边用右手的食指戳点着桌子。
毛邦初盯着周至柔的食指,说:“依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参加?”周至柔的手指停下来,声音也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他强调说:“不是我的意思,是委员长的意思。特技飞行表演是重头戏,不可缺席的。”毛邦初点了点头,唯唯诺诺却又居心叵测地说:“那就请周司令亲自点将吧。”周至柔听后脸色立即沉下来了,猛然站起身,指着毛邦初说:“你是总队长,我点将,要你干什么?”说完拂袖离开会场。毛邦初被摞到那儿,表情僵化,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追出去了。在走廊里,他快步赶上周至柔,笑着说:“长官息怒,卑职对您一向尊崇,决没别的意思。”周至柔停下来,口气也随之温和下来,他抬手拍拍毛邦初的肩膀说:“邦初啊,国难当头,我们都要以社稷为重。你已经贵为将军,做事要有所担当。”
毛邦初有些受宠若惊地点着头,嘴里忙应承着:“那是那是,只是空军缺少这样的人才。”周至柔又重重地在毛邦初的肩膀上拍了两下说:“不要妄自菲薄,北平的航演不是很成功吗?”毛邦初点着头,他在揣摩周至柔的心思并试探着说:“如果必须参演的话,我倒是有个人选,高志航,不知您意下如何?”
“如果我没有看走眼,这个家伙还是可以摆上台面的。”周至柔的脸上立即呈现出喜悦之色,他由衷地夸奖着。
“主任慧眼识珠,只是……”毛邦初欲言又止。
“我听说了,这个高志航是一匹无羁之马,很难驾驭。”周至柔把手放下来,背到身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