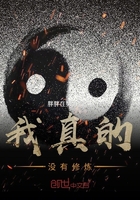但孙倩倩活得是多么简单快乐、是多么平衡而和谐呵。
有一次,不知怎么讲到共产主义这个庞大的话题。我仍然是那样委婉曲折,孙倩倩仍然是那样干脆利落。
她说:当然!我当然相信共产主义和乌托邦!
她很简单平静地说着这句话,脸上的表情也是平衡而和谐的,看不出有任何的虚伪。
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在莉莉姨妈六十三岁生日的这一天,我准备让孙倩倩给她化一个妆。
把一个女人尽可能地变得美,变得更美。把单眼皮变成双眼皮。
把复杂难懂的事变得简单快乐。
这是晴朗而美好的一天,但其实也是稀松平常的一天……稀松平常的一天……隔天晚上,我像平常一样吃了一粒安眠药。将睡未睡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莉莉姨妈。
我说,你睡了吗?
她说,快了,第一粒安眠药是半小时前吃的……
我还没听清楚第二粒安眠药的具体情况就睡了。我睡着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睡着了比醒着还累。有一阵子我母亲偷偷把安眠药换成了一种保健药丸,我睡不着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一会儿想想莉莉姨妈,一会儿想想四舅。这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有时候我也会想到白先生,但一想到白先生就更睡不着了。有几次,我还想到了常德发常伯伯。我老记得他和莉莉姨妈有一天坐在院子里聊天。两个人为一只注射了激素的母鸡长嘘短叹。莉莉姨妈悄悄脱掉了一只高跟鞋,一边晃悠着酸痛的脚一边说:我呵,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世道会变成这样!常德发呢,还是像抱小孩一样把花盆抱在怀里。他的头像拨浪鼓一样不停摇着。后来他告诉她一件事。说他有个老朋友新添了小孙子,那小孩呵经常感冒流鼻涕,老朋友呢怕他疼,不让用纸呵什么的去擦,说用舌头呵!用舌头呵!莉莉姨妈也不接话,一边晃脚一边固执地讲那只母鸡:我说呢,那只母鸡怎么老是生双黄蛋!一天一只双黄蛋,一天一只双黄蛋……
说来也怪,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睡意就来了。开始还是有声音的:做梦也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一只双黄蛋……一只双黄蛋,后来就只有场景和动作了,一个不停晃着头的老头,和一个不停揉着脚的老太……
我经常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抑郁症。
我觉得自己挺像那么回事的。而且我还讳莫如深。不想提到这件事情,不想多谈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也会假装坦然地说起这个--我像不像抑郁症呵,像不像抑郁症呵。然后和旁边的人一笑了之。像个英雄似的。
其实这就是抑郁症的表现了。
但那天晚上我却睡得香甜极了。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而这种奇怪而香甜的睡眠,竟然还延续到了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打来的。
我们约好在一家西餐馆见面。就是我和莉莉姨妈去过的那家西餐馆。
我在靠窗的沙发坐下来以后,他的电话又来了。他让我再等他一会儿,再等那么一小会儿,他说因为上午他去银行办了点事情,然后又去一个老中医那里配了点药--
你知道的,我是个药罐子。他说。
我的这位朋友姓林。于是我就点了一根烟,喝着一杯白水,坐在渐渐阴翳下来的窗口等待着这位林先生。
中午的时候人很少,也没有那种亮闪闪的灯光和好听的鞋跟的声音。有几只蜻蜓飞得低低的,悄无声息地撞在了厚厚的玻璃上。
西餐厅突然显得空旷了起来。
这位林先生,他既不是我的男朋友,也不是我的情人,我们甚至连一点暧昧的感觉都没有。
这是真的。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控制的。我和林先生认识的时候,对感情心灰意冷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说,我们就做一般朋友吧。他也没啥意见。说好呵,一般朋友多好呵。
就这样相处了下来。冷冰冰的,其实也暖洋洋的。
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做什么职业的呵,我怎么觉得你什么都干呵,什么经纪公司,贸易公司,还贩烟贩酒……你会不会也贩人呵。我就这样问他。
他呢,也就嘿嘿嘿地乐着。他在我面前挺放松的。有时候我想,他或许也挺希望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也不是女朋友,也不是情人,连一点点暧昧的感觉都没有。至少是说好了,要一点点都没有。
他平时很忙。我们有一阵见得挺多,后来就少了。有时候两三个月都见不到一次。但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在吃药。总是随身带着很多药瓶子。而且一点也不避忌我。
我就嘲笑他。我说是吧是吧,不是女朋友就肆无忌惮了吧。
他还是嘿嘿嘿地乐着。还介绍给我看都有哪些哪些药,都是治疗什么什么的,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痛风病,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胃肠功能失调……
我装出一副一本正经、并且还很可怜他的样子,我说算了算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有什么病,你就告诉我什么病你现在暂时还没有吧。
他嘿嘿嘿了一下,又嘿嘿嘿了一下。他说,还真没什么病是我没有的,对了--他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前几天医生对我说了,说怀疑我现在因为痔疮严重发作,体内充满了毒素。
我觉得林先生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怀疑这件事情,后来我想了想,觉得这件事情几乎就是肯定的,根本就用不到去怀疑。即便他自身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还没在他的瓶瓶罐罐里增添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他也一定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而且这样一想,我又想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咦,这样说来,其实莉莉姨妈呵,四舅呵,常德发呵,我的父亲母亲呵,我已经去世的外公外婆呵,我的这些亲人们可能都或轻或重的患有这种病症;那秋先生就不用说了,几乎就是抑郁症的代表性人物了;至于白先生,不管他是不是,我只要一想到他,我自己的抑郁症就会愈发严重起来。
我觉得,总有一天,总会有那么一天,抑郁症会像感冒一样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大家每天早上见面,轻松自然地相互问候:嘿,你今天抑郁了吗?
对于林先生的美食主义,我一直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太能吃了。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我和他约会见面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就是找个地方稀里哗啦地大吃一通。有时候甚至连话也很少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而且我和他的口味也是接近的,喜欢刺激的东西,喜欢味重的东西。我们开玩笑说,我们都爱吃那些生离死别的东西。
有时吃得酒饱饭足以后,我就开始嘲笑他,我说,你吃的那些都是开胃药吧。
他也不还击我。餐后的他总有一种怡人的满足感。非常短暂,却也非常真实。他老是说,食物让我快乐。真的。他看着我,有时候也会添上一句:你也让我快乐。有时候他吃得实在太满意了,也就完全不顾忌我的感受了。他什么也不说,沉默着,久久地回味在食物给他带来的甜蜜之中。
那家西餐馆我和他去过好几次。他喜欢那里的鹅肝排和红酒山鸡,我则认为巴黎龙虾是很不错的。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他的刀叉要比筷子用得更好。我说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介绍我的姨妈给你认识,让她看看你用刀叉的样子。我像莉莉姨妈观察我一样地观察着他。刀叉发着银光,亮闪闪的,硬梆梆的。是一种干脆利落犹如凶器一般的美。他用得熟练极了。我真的很少看到用刀叉用得这么好的中国人。那两件凶器一样的东西仿佛都已经长到他骨子里去了。寒光闪过,优雅迷人,熟练得让人赞叹,熟练得让人寒心。
那天中午,就在这家西餐馆里,林先生挥舞着刀叉和我共进了一次午餐。我记得那天的龙虾口味相当不错。但林先生却抱怨了几句,说今天厨师一定开了小差,因为鹅肝排几乎大失水准。
我觉得他的情绪不是很好。饭前就不声不响地吃了好几种药,后来又吃了一次。但这是不是和天气有关系呢,或者本身就是我的错觉呢。蜻蜓还在飞着。没头没脑地飞着。一头撞在这儿,一头撞在那儿。有的一下子就撞昏过去了。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窗外下起了一阵急雨。
天黑极了。没头没脑的。
在几乎全黑的底色中,有银色的、凶器一般的刀叉优雅地挥舞。
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说是在新单位里照的,他新近在里面工作的一个公司。一家合资企业。我拿过来看了看。是一张合影。七、八个人的合影。照片里只有林先生和一个小女孩是中国人,剩下的全是高出他一、两个头的外国同事。那脸上的表情以及形体,让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挪威或者芬兰一带的人。
我们又聊了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