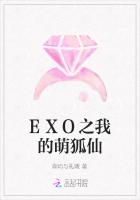从汀江机场出发时,我和汤姆都吻了一下胸口挂着的十字架,暗暗祈祷一番,又将印度平安符挂到座舱上方。这次,我们的飞机上装载着数百箱阿司匹林,随行的还有七个英国医生,他们都是志愿者,据说还曾受到丘吉尔的亲自接见。
C-47在云端穿行,仪表盘上,各种仪表的指针和读数发出蓝色的微光,发动机轻快、柔和的“嗡嗡”声响萦绕在耳边,在我们听来,这种声音是那样的安详美好,那是安全的保障。前后都有几架友机,不疾不徐地翱翔着。我们的左翼和右翼各有两架“飞虎队”的战斗机护航,机头上的鲨鱼图案看上去就像保护神一样,令我们心安。
飞机过了热气腾腾的汀江上空,渐入冷境,周围那种安详的氛围忽而有些冷冽,某些不安定的因子在空中游移着,然而又无从言说。
赵小虎的14号运输机一直在我们的后翼,当我们的飞机穿过一座冰峰的夹层时,忽地,14号通过对讲机传来一阵尖叫:“07!——啊,长天,我看到它了,天啊,我的天!”他的声音有些毛糙,混着“刺刺”的杂音。
我的心一下抽紧了,从后视镜看过去,14号正掠过我们刚刚穿过的冰山,左翼碰到了悬崖,机身剧烈地颤了一下。透过机前窗,我看到了赵小虎模糊的上半身,他的头颅正往上仰着,似乎看到了什么怪异的东西。
我也抬眼看向空中,那里只有几团厚重的铅云簇拥着,幻化成一个巨大的飞机形状,难道他看花了,以为……我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看法,赵小虎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长天,我看到它了,那个毛烘烘的东西!它就躲在乌云里头,我看到它了!”他的声音更加嘶哑。
我重重吞咽下一口唾沫,说:“小虎,冷静!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它,我看到它了!”赵小虎语无伦次,声音在打颤,老是重复那句话。
十来架运输机呼啸着掠过喜马拉雅山脉,进入横断山脉,那里既无地面站又无导航台,是极难飞的一段航程。这天的气候有些古怪,还是上午,便扯上了淡淡的黑幕,似有暴雨将至。我和汤姆换着开飞机,抵达横断山脉时,正值他开。我躺在副驾驶座,双眼半眯,看向空阔寂寥的天幕。
陡地,北面有几个黑点隐现在冷冷的天光下,黑点中夹杂着白点,虽然隔着千余米,但我们还是一眼看出,那是零式日机!四驾护航的P-40振翅呼啸,四条“鲨鱼”两两掩护,义无反顾地扑向敌机!
然而,令我们恐惧的是,那几个黑点之后又涌出几个黑点,敌机至少在八架以上!“飞虎队”队员虽然勇猛,然而敌人两倍于他们,这场空战着实难以拿下!
P-40还未到射程便射出密集的子弹,想以最快的速度击退敌机,那些敌机却不迎战,飞速往后退去,四架敌机也是两两掩护,分别从左右掠开,向P-40的尾部掠去——这是要包抄,将P-40夹在中间!
P-40有些慌了,但他们也是久经沙场的,他们两两咬住一架零式日机,没命地射击(他们受过陈纳德的专门训练,知道两架战斗机配合,无论是掩护友机,还是击落敌机,概率都很高),一架日机左翼被击中,冒着黑烟向下落去。
但日机已经形成前后夹攻的局势,四架P-40在弹雨中翻飞着,像滔天海浪中逃窜的鲨鱼。我们几架运输机都在空中僵持着,不知该进还是退,但第六感告诉我们,我们的死期不远了!
激战了片刻,四架P-40有三架都受了伤,机身升腾着黑烟,机头上的鲨鱼也烟熏火燎的,一副筋疲力尽的架势。运输机的机长已经在短暂的通话中达成协议,准备撤退,汤姆一张脸涨成猪肝色,把握着操控杆,机头打个横,向来路飞掠。
这时,对讲机里一个嘶哑的声音叫道:“不能回头!这些零式飞机都经过改进,速度比C-47快多了!你们赶快抛弃机身的辎重,沿南边的次航道继续前进,过了横断山脉就安全了,那里有执勤的飞虎队员!我们将它们引向北!”这是一架P-40飞行员的警告。
十来架运输机同时增压,以最快的飞行速度绕过前面密集的弹雨,向南侧飞掠。那些日机发现了运输机的企图,分开三架跟上来,对着运输机的机尾,子弹一通狂扫。两架运输机很快着火,猛然向下坠去,只有正副机长跳伞亡命,在空中像飘忽的羽毛,他们的生命也像羽毛一样轻。
“哒哒哒——”一架零式日机里忽然探出一支机关枪,一溜子子弹射向飘飞的降落伞,几个飞行员在空中惨叫几声便死去了,降落伞依旧在飘摇。
我和机舱里的那些英国医生没命地沿着舱门向下扔东西,一匣一匣的阿司匹林滚落下去,那些医生的脸上露出沉痛的表情,这些药可以救活多少前线受伤的战斗英雄啊!四架P-40被击毁了一架,才落下十来米,便在空中轰然爆炸。剩下的三架P-40忽然疯了般,不顾连天的子弹,向南线飞来,机身上都腾着可怕的黑烟,随时都有可能坠毁。
“他们为什么还不跳伞?”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失声叫道。
“跳伞也是死路一条啊!”汤姆眼睛血红。
“那他们这是……”我忽而猜出了什么。
三架P-40以极限的飞行速度,向追击我们的那三架零式日机撞过去!日机也看出来了,忙舍弃了我们,加大马力逃生。一架P-40终于撑不住,向下坠落,另两架继续颤颤巍巍地追击着敌机,机翼上火光冲天,一股铝片燃烧的刺鼻气味在空中弥漫。
一架日机怕是辎重太多,飞行速度落后了一架P-40,然而这架P-40由于损坏严重,速度也在一点一点地下降,即将撞到日机时,左翼竟脱开机身,撕裂开来,机身在空中摇曳一下,急速下降。
那架日机在空中兜一个圈子,似乎很得意的样子。就在这时,最后一架P-40舍弃了追击的日机,向这架日机撞击过来,电光火石之间,那架日机没来得及调整航向,被P-40撞了个正着,“轰——”一声巨响,两架飞机在空中炸成无数的碎片。
经过三架P-40的舍命追击,敌机已经被引到偏北方位,与运输机隔开很大一段空中距离。运输机向南飞行,那里的航道更加艰难,山峰与云层交叠,甚至难以区分开哪里是雪山,哪里是云朵,稍微一走神,便会机毁人亡!
此时该是我上机的时间,汤姆却不敢换我,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盯着机窗外黑沉下去的天,我们在乌云与山峰之间穿梭,像夹缝中生存的寒号鸟。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那些零式日机在云层的投影也越来越大,子弹的“哒哒”声隐约可闻。
“轰——”一架运输机被敌机击中,惊惶中左翼触碰到了山巅的一棵高大的雪松上,跟着跌落雪野,虽然飞机没有爆炸,但里面的人十有八九是死了。一架敌机追上来,在空中盘旋着,子弹对着驾驶舱一通猛扫,又继续追击其他的运输机。
15号运输机传来求救声!他们的运输机被两架日机咬上了,机翼上弹痕累累!然而,这个时刻,每一架运输机都成了砧板上的鱼肉,自身难保,求救又能如何呢?
忽地,15号改了航向,降低了航速,向两座冰峰之间的峰隙闯过去!那个峰隙不过一个半运输机那么大,能够闯过去的概率很小,他们是赌上命了!紧咬着15号的敌机,一架怂了,向后掠开,另一架却追击上去!
“哐当——”15号以中速神奇地穿过了那个峰隙,右翼带出浩大的雪沫石屑,追击而上的那架敌机被扑面而来的风雪沙石迷住了,机头一偏,撞在了山峰上,“轰”然爆炸,铝片在天光中闪着诡异的光芒。
敌机震惊了,火力更加猛烈地射上来,但他们不敢沿着海拔超乎寻常的山峰走,而是在空阔地带盘旋。十来架运输机这时只剩下了七架,都吸取了刚才15号的恐怖经验,在山峰之间飞行,敌机与运输机在峰谷间展开殊死追逐,然而山势越来越平,可钻的峰隙越来越少,萨尔温江已经在望!
如果掠上江空,运输机势必会暴露在敌机的火力之下,机毁人亡!然而如果回头继续周旋,汽油却即将耗尽!我们的汽油不比敌机是有备而来,都是计算好了的,再耗上几个时辰,只能迫降,束手就擒了!
我们的求救信息已经发出去很久,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海拔太高,信号干扰异常严重。
“怎么办?过江?还是绕着山峰,等待救援?”汤姆和那些机长商议。
“死磕了,过江!”几个机长都咬牙切齿地叫着,对讲机里的喘息声被放大了几十倍,很是刺耳,“如果被击中,就跳江!活的可能性到底他妈的大一些,比摔死在石头上好!”
七架运输机又将机舱内残余的东西扔下山去,一架运输机上甚至扔下去了一只副驾驶的座椅!那些敌机很快发现了运输机企图过江的意图,抢先一步飞掠到江空,占据有利的攻击地形。
运输机散开,忽高忽低地飞掠在江面之上,汤姆是个人精,他将运输机贴着江面飞,如果中弹,跳江甚至不用降落伞。敌机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他们轻易不肯开火。一架运输机由于飞得过低,机腹陡然被飞涌的浪头拍到了,机身一个踉跄,在空中翻了个个儿。大概是被浪头吓坏了,飞行员又将飞机爬升了一段距离,然而敌机已经守株待兔般扑了上来,一溜子子弹射进座机舱,机窗上顿时喷溅了一层血点子,运输机的机头向下按落,跃上半空的海豚一样插进一团风浪中!
“嗤——”燃烧中的机翼与江水相接,腾起一股黑烟,座机舱的窗玻璃“哗”然震破了,里面滚出一个血人,他在江面上漂浮了一下,便沉入江中。
汤姆操控着飞机,一面提防着下面的风浪,一面又提防着上空虎视眈眈的敌机。他的一对血红的眼珠子滴溜溜转着,几乎要爆炸了一般。
终于,一架敌机似乎按捺不住,俯冲而下,随之而来的是一溜子子弹,“哐当——”一颗子弹穿过了我们的机窗玻璃,那几个英国医生吓得尖叫起来。
运输机一个倒栽葱,向江面跌去,我忙大叫:“机长,快爬升!”然而汤姆却一动不动,我定睛一看,他后脑勺的头盔上多了个洞,鲜血和一团白糊糊的液体正往外涌着。天,那一颗子弹竟穿过了汤姆的眉心,从后脑勺飞了出来!
当时,我来不及多想,在无边的恐惧中,坐到了汤姆的尸体上,急速一拉操控杆,机头与浪头接触的一刹那,又“龙抬头”了!
我大口大口吞咽着唾沫,嗓子眼里塞满了黏糊糊的东西,双手不敢离开操控杆,仿佛那是我的救命稻草。我从后视镜上看到了汤姆仰面躺下的面容,额心一道血痕划破了他的脸,他的眼角也有血液流出,直灌入耳朵中,惨不忍睹。
一阵大风兴起,江面波澜翻涌,低沉的云似乎要被江水拍打下来,又是一架运输机的机尾被浪涛拍中,跌入江中。日机乘机又是一番扫射,江面有血水在翻涌,不知是人的还是鱼的。
“与其葬身在江里,不如拼了!”一个机长通过对讲机怒吼起来,“我们撞上去!这帮狗娘养的子弹也快耗尽了!”
六架运输机都毫不迟疑地掠过海面,急速爬升,那些日机本想将我们慢慢在江面耗死,想不到我们像飞虎队一样拼了,他们惶恐地后撤,子弹扫射的声音也变得单调,鬼子已经没有几颗子弹了!
六架运输机疯了般追击着那些日机,这一幕我以后回忆起来依旧胆战心惊,因为当时我们的汽油都已到了底,说不定某个时辰就会从空中跌入江心——那里,循着血腥味而来的鳄鱼正张大着嘴巴等着从天而降的美味!
我们追击了不到一分钟,南翼忽而闪现几个黑点,我从后视镜上看到了,直感到从头到脚底都冰冷了!
但对讲机里很快有人欢呼起来:“是飞虎队!援军来了!上帝啊!”
那些敌机也发现了呼啸而来的飞虎队,向横断山脉那边撤退,我们的汽油都差不多耗尽了,不敢再追,急寻着可以迫降的地方。我们最终沿着江滩降落了,六驾运输机像被拍打到岸边的鱼,在江风中颤着。
“飞虎队”来了七驾战斗机,他们根本没有接受到我们的求救信号,而是估算了一下时间,见我们延迟得太久,便猜出出事了,于是飞天而来。他们唯恐敌机还在周边盘旋,等到他们降落时偷袭,于是只降下了三架战斗机,另四架一直在我们头顶滑翔。
战斗机大都是一人驾驶,有副驾驶的很少。三架战斗机上下来了四个人,他们都提着油箱,显然知道我们缺油的困境。几个运输机的机长泪流满面,上前与他们拥抱,我和赵小虎是中国人,有些腼腆地站在冷风中。飞虎队员将几盒饭菜送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就餐,由他们提着油箱去加油。
我正狼吞虎咽着,赵小虎凑了过来,压低声音对我说:“长天,我以为这一次我铁定死了!想不到竟然活了下来,真他妈的奇迹!”
我忽而想起他在飞喜马拉雅山时,时断时续的尖叫,忙问:“小虎,飞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你在空中看到了什么?什么‘毛烘烘’的东西?”
令我惊诧的是,赵小虎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我跟你说过话吗?没有啊!飞喜马拉雅山的那一段时间,一直是机长在开啊!我在打盹!”
我顿时有些毛骨悚然,如果当时不是赵小虎说的,哪会是谁?14号上只有机长和赵小虎啊!可是,那声音明明是小虎发出的啊!难道是我幻听了?或者,小虎他……我艰涩地咽下一口冷饭,胸口一阵发堵。
忽地,那些坐在地上吃饭的机长和副机长都站起了身,我和赵小虎也抬头去看,一个飞虎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