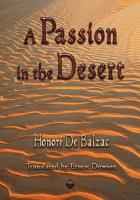有一个五月里的周末,忽然下起了雨。天色阴沉,像太阳已经落山了的黄昏。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客厅里传来阿姨和喜羊羊的嘻闹。喜羊羊老是在尖叫,他用尖叫来表达一切情感。说真的,这尖叫让我想捂住耳朵逃掉。我喜欢下雨的天气,从前是,现在也是。下雨的天气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床上睡上一整天。反正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打扰,大家都在闲,我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负罪感。下雨的天气里可以很自由地孤独,那是从前。现在是喜羊羊的尖叫让我感到不自由的孤独。我紧紧地关着房门,很想出去看看他是怎么了,又实在不想去看。因为他一看到我就会死死地抓住我不放。我要反复地给他念他根本听不懂的唐诗儿歌,还要捏着嗓子,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而我不擅长表演。可是不表演又不行,即使笑得很累了也要笑。育儿书上说我们不能伤害孩子,在他们三岁之前要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情感要求,这样他们将来长大了才会很自信。书上还说“天才是夸出来的“,于是所有的妈妈都学会了捏着嗓子说:“宝宝你真棒!宝宝你最棒!“我也一样。虽然是半信半疑。独处的习惯即使在有了喜羊羊以后,也仍然不能改变。
我经常想逃到一个安静的、只有我自己的地方。就像从前一样,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再没有第二个人让我牵挂。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多么美好的自由,永远失去了的自由。一切都已不可改变。当我孤独的时候,心里总会淡淡地滋生一点类似于爱的感觉。我想起了毛毛雨。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如果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的雨天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可能是我们两个为了逃避陪喜羊羊玩的重体力劳动,一起悄没声地躲在房间里睡大觉,任由喜羊羊在外面敲门喊着“爸爸妈妈“我们两个也不出去,还互相看看偷偷地笑。可能他是个合格的好爸爸。他主动去带喜羊羊而让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构思一篇可能永远也发表不了的小说。也有可能我们三个快乐地走在雨中,卷起裤腿,用穿着凉鞋的脚啪达啪达地踩在冰凉的水里。从前我们是两个人一起玩,现在是三个了。我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三个人。我们会快乐吗?在充满了雨水潮湿气味的房间里,我忽然很想家里有个男人。我曾经评价毛毛雨“性感“,他很高兴。不,我说的性感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个意思。而是只有我才能准确理解的那个意思。
我喜欢男人有短短的干净的头发和指甲,整洁的衬衫;马马虎虎大人大量。我喜欢某种天然的气味,胜过千言万语。我向往那样一个家,卫生间里挂着刚刚洗过的男式衬衫,门口有笨重的鞋子。一个结实的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男人正在花园里修修剪剪。一个穿着背带裤的小娃娃在花园里快乐地跑来跑去。想象力太过丰富只对写小说有好处。对现实生活着实是一种严重的摧毁。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人的人生,说穿了就是天注定。我不必再去追溯我小的时候有没有接受过夸奖与赞美,也不必再去痛苦地回忆一个又一个男人给我的情感教育。我只能说,一切都是天注定。对于一个孩子,天生地有了什么样的父母也就有了什么样的人生,都是天注定。喜羊羊天生地就有了我们这样一对父母。这没什么。下雨的天气里我想起了毛毛雨跟喜羊羊极为相似的脸部线条,想到喜羊羊将来的样子,我无声地对自己笑笑。觉得人生挺有意思。我已经很久没有爱的感觉了。但我得承认有的时候,我挺喜欢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喜欢。我们之间有相互吸引的生物本能,没有道德束缚。我们彼此从不掩饰真实的爱恨和需要,我们既爱对方也恨对方。
如果现在是原始社会,我们将会是多么和谐的终生伴侣,生儿育女搭屋盖房对抗凶猛的大自然。可是在文明社会里,一切都需要理由和解释。而我,给不出这个社会以光明的理由和解释。也给不出毛毛雨以光明的理由和解释。所以我要遭受被社会正常生活模式遗弃的惩罚,要以主动的姿态迎接被动的命运。我无话可说。我不能说对有些事情毛毛雨太在乎了。这本是社会惯例,无可厚非。他并不是非常出色出众的人,我不能要求他有着惊世骇俗的深遂思想。虽然有的时候,我很希望能得到他真正的理解。我想一边思考着、筹措语句,一边真诚地说:“其实有些事,只是某个人生阶段的需要,这没什么可责备的。男人需要,女人也需要。按照地球上的男女比例,有需要的男人,基本上会对应着一个有需要的女人。话说回来,为什么只有女人是受责备的呢?男人,女人,是同等结构的生物。“为什么我不追究他的过去,而他就可以对我的过去耿耿于怀。为什么我天然地就觉得比他理亏呢?--我不想再去说什么男女平等,那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命题。有了喜羊羊以后我更明白了男女平等是一个永远的虚妄:老有些人严厉地监督着女人是否做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妈妈,而极少人去关注男人是一个怎样的爸爸。
我不如自己背起所有的历史包袱完事。我不想说过去的一切是对是错,我只是觉得再正常不过了。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难道一定要我编出一个纯情少女上当受骗要用一生去赎罪的故事吗?我永远不会去编一个那样的故事。我宁可硬着头皮承认:“一切都只是出于某个人生阶段的需要。没人骗我也没人勾引我。事实上我也不觉得损害了别人什么,我自己,也没受到什么损害。“毛毛雨不愿意听我谈起过去,也不愿意听我的这套理论。他一听到就皱起眉头把话岔开。
他有点不耐烦地说:“行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不是已经答应跟你结婚了吗?“我一听就觉得头顶一凉。所有的话都是白说。过去的事永远不可能成为过去。它们将永远是将来的一个陷阱。于是我说:“你答应跟我结婚了;可是我答应你了吗?“每逢此时,毛毛雨的脸上就满是茫然和无奈。他搞不清楚我在想什么。他的请求,对于他和我和喜羊羊三人来说,算得上是一个三赢的结局。然而我却拒绝了。我只是拒绝,而没有再做任何具体说明。我相信一切都是白说。他觉得我神秘莫测不好捉摸。他又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还另外留了什么后路,傍了什么大款。这么一想,他就更难受了。这种难受,让他有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爱的感觉。我们于是欲罢不能地纠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