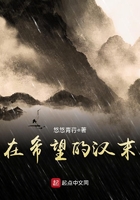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
由于亚东的经营状况,一直未有起色,汪孟邹日坐愁城,连陈独秀这个书生,也不得不下海蹚浑水了。他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促成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的合并。合并后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书局,庶可与其他大出版商一争长短。其实也是为《新青年》开辟一条活路,亚东、群益一天不告别“苟延”之局,《新青年》就一天不能摆脱“残喘”之苦。陈独秀与汪孟邹一起,仆仆风尘,到北京为书局招股。
其时陈独秀住在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北大校长任命发表的当天,蔡元培冒着严寒,到旅馆登门拜访。“这很像‘三顾茅庐’哩!”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本来不是蔡元培的意思,是别人推荐的结果,究竟陈独秀在教育上有什么主张,令蔡元培觉得非他不可呢?
1915年,陈独秀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病,曾公开宣示他的四大教育方针:一、现实主义(注重现实生活);二、惟民主义(民为邦本的民权主义);三、职业主义(从事实际的社会生产活动);四、兽性主义(体魄与意志的锻炼)。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在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陈独秀也曾与友人就教育方针交换过意见,他说:“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陈独秀《答胡子承》。《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这与蔡元培在民元鼓吹的“五育并举”(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不谋而合,蔡氏本来就爱惜人才,既已当面,焉忍错过?于是便三顾、四顾茅庐,要请陈独秀出山了。
但陈独秀觉得自己既无学位,又无大学教学经验,对教书兴趣也不大,还是想回上海办《新青年》,他再三推辞,并荐胡适以代。
蔡元培说:“你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同时也非常欢迎胡适回国,北大的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亟盼胡适能回来挑大梁。陈独秀没办法再推了,只好答应,约定以三个月为期,如胜任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回上海。蔡元培大喜,立即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
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这样做“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却忘记了蔡元培是个安那其主义者,痛恨国家制度,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杀人放火都敢做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而且陈列着炸弹。区区造个假履历算得了什么。
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知的。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按罗氏说法,仿佛陈独秀在北大学生中,是一颗万众期待的明星,其实,那时的北大,从上面几位亲历者的描述可知,简直是一个污水潭。“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有之,“无不热烈欢迎”则未必。
蔡元培亲自出来回答那些质疑:“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团结报》1983年6月4日。陈独秀在清末民初曾发表过《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荀子韵表及考释》、《连语类编》等著述。这才把质疑者的嘴巴给堵住了。
陈独秀终于踏入了北京大学的门槛。《新青年》也随他从上海迁到北京,在箭杆胡同九号落脚(但出版地仍在上海)。出乎陈独秀的意料,果然是树挪死,人挪活,他从上海挪到北京,不仅把《新青年》挪活了,而且亚东图书馆竟也咸鱼翻身,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凭借着聚集在北大的一批文化精英,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渐渐回黄转绿,现出了勃勃的生机。
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公子后来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
蔡元培没有错,陈独秀一任北大文科学长,很快就把全国杰出文科人才集中于北大,当时文科真是人才济济、教授成堆:
国文系教授:马幼渔(兼主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林损、黄节、单丕、吴虞、刘文典、吴梅、刘半农、张定璜、周作人、沈士远。
史学系教授:朱希祖(兼主任)、马衡、陈汉章、崔述、张尔田。
哲学系教授:陈大齐(兼主任)、胡适、马叙伦、徐炳昶、樊际昌、张竞生。
英文系教授:胡适(兼主任)、陈源、温源宁、林语堂、张欣海、关应麟、徐志摩。
法文系教授:李景忠(兼主任)、宋春舫、贺之才、李宗侗、铎尔孟(d`Hormou)。
德文系教授:杨震文(兼主任)、Hundhouse。
俄文系教授:顾孟余(兼主任)、伊凤阁(Ivanov)。
东方语文系教授:周作人(兼主任)、张定璜、徐祖正。
教育系教授:高仁山(兼主任)、樊标昌、蒋梦麟。
政治系教授:陈启修(兼主任)、陶履恭、李大钊、高一涵、周览、张慰慈。
经济系教授:顾孟余(兼主任)、王建祖、马寅初、罗惠侨、皮宗石、余文灿。
以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北大文科各系(当初“系”称“门”,如“国学门”、“哲学门”等等)包括文史哲、东西方语言学等各系(门)教授多达五六十人,如此雄厚的教授队伍构成当年北大独树一帜的风景线。马泰《永远的北大人》。《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其时北大尚在景山东街四公主府,校内北侧为讲堂,东侧为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称“卯字号”。新文化运动时期,卯字号星光熠熠,冠盖如云,真是猗欤盛哉,恒为北大校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时光。
说这些人都是受陈独秀的吸引而来的,那是夸大了陈独秀的影响力,他们当中不少人在陈独秀之前,已在北大执教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的经学家刘师培,以及“以骂人名海内”的音韵训诂学家黄疯子黄侃等等,都是蔡元培请回来(或保留下来)的名重一时的学术大师。蔡元培看人,只看称职与否,守旧也要守得称职,不能马马虎虎地守。
辜鸿铭脑后留着一条大辫子,到死也不肯剪,连雇回来替他拉车的车夫,也是拖着辫子的。他这条辫子在北大赫赫有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招来无数注目礼。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为之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有资格笑辜鸿铭的人,普天下确实数不出几个来。
蔡元培又聘请了孙国璋(芾仲)到北大教授世界语。这与蔡氏的安那其世界主义情结有关。世界语在民元前后,曾一度风行,后渐式微。蔡元培希望利用北大的阵地,重振旗鼓。而新学诸子又正提倡改造汉字,双方不谋而合,故积极推波助澜。
据曾执教于北大的傅振伦教授说:“苟无北大之世界语宣传运动,恐世界语早成过去历史上之名词,列入死的语言Lingvo mortita之林矣!”在校长及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推动下,“当时世界语学者Esperantisto,在五百人以上,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班讲习之。”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1933年12月。
应该说,很多人是冲着蔡元培去的,不是冲着陈独秀去的。蔡元培学养纯厚,胸襟廓然,奉行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如黑暗中的一盏暖灯。虽然身材瘦削矮小,但他雍容雅步的身影一出现,几有“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的盛况。
一所现代的大学,就应该在学术上有容纳各流各派的泱泱大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陈独秀对蔡元培也大加赞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不过,人们通常称赞蔡元培“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很少说他“容纳异己”。事实上,蔡元培从未说过辜鸿铭、黄侃等人是“异己”。他们也许是陈独秀、钱玄同的异己,但不是蔡元培的异己。陈独秀把蔡元培延聘辜、黄等人称为“容纳异己”,包含了一句潜台词,即蔡元培是“我们”这一边的人。辜鸿铭也曾经吹嘘,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他自己,他要和蔡氏共同进退。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读书》1994年第4期。似乎也表示,蔡元培是他那边的人。
蔡元培强调,他希望北大只有学术宗师,没有学术门派。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1917年,蔡元培聘请只有中学毕业程度的梁漱溟到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氏到校第一天,就问蔡氏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氏回答:“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是他的心里话。蔡元培反对的只是政治化的孔子,反对独尊孔子,并不是要把孔儒扫地以尽。他所持的完全是一种平等心和平常心。当梁漱溟表示,他到北大,“不仅是不反对(孔子)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时,蔡元培也照样无任欢迎。
后来梁漱溟对蔡元培有一个很恰当的评论,他说:“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有意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惟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若论对蔡元培的理解,梁漱溟比陈独秀深刻与贴近多矣。
白话文与文言文,一度被视为是新旧文化对峙的楚河汉界。蔡元培虽然毫不怀疑白话文最终将取代文言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言,但他却没有把赞成文言文的人划入“异己”范畴。他的主张很鲜明:“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