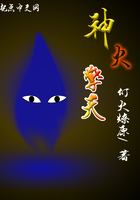族概念被中国人身份神化,中国政府对该问题的立场具有不可探讨性,这一立场很好地体现在它在“被割让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以及认为香港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部分的信念上,任何支持台独的观点都会立即遭到反对。中国人对民族问题的立场以及中国人身份包含什么意义,与其他人口大国--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美国--截然不同,这些国家公开宣扬它们多种族、多民族的特征,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个事实表示欢迎。
将中国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描述为意识形态是错误的做法,因为这种立场实在太古老、扎根于中国历史太深了,所以那样的描述不是事实。的确,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它经历了深刻变化,但此前早已深深融入中国文明上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关于民族和身份的立场也不可简化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它在中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举一个时下的例子:如果说支持台湾回归的普通中国人与中国政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前者态度甚至更强硬。
我们也不要期望中国的种族和民族立场会有任何重大变动。的确,由于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绝,这种立场被夸大了,同时,与世界不断的融合也许有助于削弱那些因封闭无知造成的偏见,但是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实际上,中国的封闭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是理解笔者所述的中华帝国思想的基础。“封闭”是中国世界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在宋朝和明朝前期也是如此,当时中国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视野上都是封闭主义者。这有助于解释某些现象,例如为什么中国对迁徙至他国领土的移民具有和欧洲大国根本不同的看法。欧洲人认为移民和殖民者是国家传播文明使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仍然归属于祖国;另一方面,中国的诸王朝对待那些离开帝国的人长期漠不关心,似乎离开中国就是游离于文明之外。这个观点提供了某种方式,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中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持续融合。中国正快速融入世界,但一如其历史所示,它也会保持疏远,心安理得地隐藏在人性等级观以及根植于文化和民族自大心理的优越感之下。
第四,中国人所生活工作的是一块与其他民族国家大不相同的大洲规模的土地,今后仍是如此。还有4个国家的领土也可以称为大洲规模。美国占有北美大陆相当多的土地,陆地面积只是略小于中国,但人口只有中国的1/4。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块大陆,陆地面积约为中国的80%,而人口不足2100万,比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都要少,且实际上全部居住在沿海地区。巴西陆地面积约为中国的90%,但人口少得多,为185亿。也许与中国最相似的是印度,人口相当,但陆地面积只有中国的1/3。因此,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各有某种相似点,但就人口数量和陆地面积综合而言,它是独一无二的。不论从人口还是领土面积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都将是大洲级别的。这不仅对中国过去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对未来也同样如此。对普通的民族国家而言,建设大洲规模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命题,因为这其中暗含如何实现同质性的问题,除非人口很少【例如澳大利亚】,或最早是殖民地【例如基本上由欧洲移民建立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当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时,它的特征就是巨大的多样性,某些方面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数个甚至很多不同“国家”组成的联合体。这么说不是为了削弱贯穿本书的关于将中国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的观点,而是为了表明这种统一现象更加非同寻常。我们是在和这样一个国家打交道,它既是民族国家又是大洲国家,换句话说,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因而必须同时按照民族国家和国家多样性的规则来治理。
因为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与普通民族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以非典型的方式管理这个国家。例如,反馈环就不一样。普通民族国家政府的行为造成的似乎顺理成章的结果在中国也许完全行不通;此外,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里,有可能在不推广的情况下由某个城市或省份进行试验,邓小平的改革正是这样推进的,即使其效果不具普遍意义,或者影响范围很小。因此,可以设想在比较发达的省份或大城市【例如浙江和上海】进行民主改革,但不涉及其他地区。如第6章所述,文明国家的概念包含“一种文明,多种制度”的认知,1997年香港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回归中国,让这个概念为更多国家所知晓。实际上,中国内部多体系的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中国应该按照西方的形象成为“民主国家”,这已是共识。然而,我们印象中的西方民主体系从未在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身上扎下根来,唯一的例外是印度。确实,除了印度,近似的例子只有像欧盟这样的跨国机构,而它的章程和运作方式又是极不民主的。未来某时中国也许会以自己的方式向着类似的民主制度转变,但西方要求它应该立刻干净利索地完成这种转变,这忽视了一个像中国这样大洲规模的庞大的文明国家和规模小很多的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和中国有同等规模的欧盟其民主程度也尚待提高。
第五,中国政体的本质极具特色。与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不同,中国的王朝既不会被迫,也没有必要,更没有意愿与其他竞争机构或利益集团【例如教会或商贾】分享权力。中国从未出现西方那样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同时,中国商人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获取更多利益,而是各自拜佛祈福。政府,不论是王朝时期还是共产党时期,都没有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它管理社会,享有至高无上、不受挑战的地位。将近两千年儒家精神熏陶并塑造了中国社会,未曾要求政府向民众负责,而是坚决要求它忠诚于儒家的道德意识。帝国的官僚机构要接受儒家道德伦理训练,对任何非王公贵戚人士来说,成为其中一员意味着达到了人生可能的最高成就。这个体系的效用显而易见:就效率、管辖权以及开展大型公共工程的能力而言,中国的政府机构无可匹敌。毛泽东时代,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依据的是阶级斗争体系理论,在该理论中,工人和农民被誉为国家的新主人;到了改革时期,部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重结果轻过程”的不成文契约,按照这份契约,政府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的统治机构具有历史延续性,证据就是同样的关键要素现在仍然界定着中国政体的特性。尽管20世纪帝国政权解体后中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大变化,经历了国民政府统治、军阀混战、半殖民主义、共产党政府和当前的改革,政府仍然受到崇拜,居于社会上层,享有巨大声望,被视为现今中国的形象代表、确保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力量。而国政体的这种精髓某种意义上说不符合任何西方社会的实情,甚至可以说不符合世界其他任何社会的实情。考虑到中国历史非同寻常的跨度--至少2000年【有证据表明也许要长得多】,上述特征应当被视为中国的先天属性。中国统治机构的合法性,影响深远、根深蒂固,不依赖于代议制;事实上,即使现在引入普选权,统治机构合法性的核心仍然会因为上千年的基础而保留。中国政府是颇为称职的机构,可以说比世界其他任何传统政府都要优秀,未来也许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它已证明自己不仅具有非凡的持续性,而且能够进行令人称道的自我改造。1949年以后的时期见证了两次这样的改造,第一次是毛泽东时期,共产党创立了新政府,中国重新统一;第二次是改革时期,这个政权获得新生、重新焕发活力,引导国家经济转型。
第六,中国的现代性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以国家转型速度快而著称。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经历不同,中国的现代性将过去和未来同时融入当前时代。第4章将亚洲四小龙描述为快速型社会,它们习惯于快速变革,天生比西方【尤其是欧洲】更能轻松面对新事物和未来。它们拥抱新事物的方式与孩童接触电脑或任天堂游戏机的方式一样,满怀乐趣和期待;欧洲社会则相反,它们对待新事物一般要谨慎得多,甚至感到畏惧,与成人面对不熟悉的科技发明时的反应相同。原因在于东亚社会没有完整经历像欧洲和北美那样典型的逐步递进的社会发展阶段及相应的科技发展阶段,因此它们的集体思维中没有塞满传统行为方式,不那么僵化。不过,由于规模庞大,中国式的现代化还应当与其他东亚国家区别开来。一方面,韩国用大约30年时间完成从整体的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化转型;另一方面,中国近半数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从1978年到现在过去30年了,还要再过至少20年,这个数字才会下降到大约20%。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比邻国更加漫长,而且更加复杂。因为广大农村的长期存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存将持续数十年。这体现在不同省份的生活水平常见的巨大差距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并存的效应突出反映了历史的重要性和影响,反映了农村在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作用。中国这个深陷于历史的国家甚至因此更加自觉地认识历史。
第七,1949年后中国一直由共产党执政。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那就是过去半个世纪中两个受争议的最重要年份记录的是似乎完全矛盾的事件:1989年,标志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及苏联解体;而1978年,代表的不仅是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经济转型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这场转型是由共产党主导的。前者表明一个重大时代的结束,后者象征着一个也许会被证明更加非同寻常的时代拉开序幕。考虑到西方对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特别是1989年之后,那么西方戴着厚厚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党,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实际上,1989年之后,西方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注定也会下台。共产党执政这一事实始终对西方的中国政策产生深刻影响,的确,偏见似乎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不是永远的话。但是,根据中国近来的经历,我们现在应当比过去更多地将共产主义视为多元化模式: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大不相同,自1978年以来,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它所展示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与前苏联共产党截然不同。不论长期变化是什么,作为这个国家大规模转型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也会令世界上更多地区印象深刻。它创立并且革新了现代中国政府,在经历一个世纪分裂后重新统一中国,在打败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制定出战略并付诸实施,毅然向经历150年衰落期的中国做出这样的承诺,那就是恢复与往日中华帝国相似的世界地位和权力。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它还成功地将现代中国与历史、儒家学说和鼎盛朝代重新联系起来。可以证明,所有伟大的历史转型要获得成功,都包含这样的与历史重新联系的过程。正如前文所强调的那样,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政权理论和儒家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儒家理论盛行了2000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成功实现目标,除了其他举措外,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改造和创新这些理论。
第八,未来数十年内中国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特征。对世界主要大国之一的中国来说,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条件,也是其幅员辽阔导致的结果:通俗点说,中国的转型是大洲级别的,具有大洲式的不同步性,非一般国家可比。其结果是现代气息与相对落后相互糅合、相互作用,在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引发众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后果。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能够忽视这一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事实上将长期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前文已经探讨过未来数十年里这个事实将如何让中国直面本国历史,并且对中国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以及与他国关系产生影响。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定位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体,两方面的利益都要考虑。我们会在很多场合发现这种表述,包括关于中国对气候变化承担哪些责任的讨论。当然,随着时间流逝,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分所占比例以及受雇于和受惠于这些成分的人数将下降,中国会逐渐像发达国家一样作为,而不再是二者的综合体。但未来半个世纪,它仍将考虑两方面的利益,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这样的趋势很可能因为中国的历史愤懑感而加强,此种感受源自日本和西方列强侵略下的“屈辱的世纪”,特别是那段被殖民化的经历。中国将是第一个来自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分化中“失落”阵营的大国,曾经沦为半殖民地,曾经是失败者而非胜利者。过去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在现代化时期将成为中国人思想中密不可分的部分,对这个全球大国的行为产生深刻
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