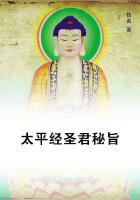嗯,她身份如何?
靖康王之女,西凉国王后,素影。
大哥就不怕再一次挑起战事?萧翎的性子古怪得很,可是你我都揣测不来的。
呵,挑起战事又如何,我堂堂大天朝一太子,还会怕了他不成?
那么大哥此番唤我来,所为何?
我想让你将她带回去,封为侧妃。
呵呵,大哥,你明知我对风月这码事不感兴趣,且绝对不会娶一个不爱的人。大哥这不是为难六弟吗?
就是因为你不娶不爱的人,我才有此决策。
大哥容我再考虑考虑。
素影觉得是时候醒来了,睁开眼睛故作陌生:“这是哪儿?”
太子一笑,俊脸凑近她:“刚才你的睫毛动了不止一下,怕早就醒来了吧?”
她干笑几声。
纳兰天漓盯着她的眼睛,像是发现了什么,清冽地笑出声:“大哥,我想我不必考虑了。”
素影起身靠在墙上,无力地闭起眼睛:“这算什么?我的终身大事就被你们如此草率地定下来了?而且我是西凉王后,理当母仪天下福泽百姓。你们这样做就不怕遭西凉子民痛斥?”
太子修长的手抚摸过她柔软漆黑的发丝,眼中有些冷意:“不怕。”
素影一声冷笑逸出鼻尖,眼底一丝波纹也无:“那我便无话可说。”
这大天朝若是有这样一人做了皇帝,应是避免不了血雨腥风一场了。
时处炎夏,烈日如火。这几日的饮食起居皆是这府邸里的丫鬟照顾着,素影有些烦闷。府里上上下下一片严谨,都似怕一不小心做错了何事不保项上人头一样,压抑得很,在太子府的日子竟不如西凉后宫面对着一多疑的太后来得更舒适一些。
那太子是个嗜血阴狠的人物,也怨不得这些下人视他如洪水猛兽。
一日有一小丫鬟过来为她梳妆打扮,说要把她眉间的印记用水粉遮盖起来。她一想也不算什么,便应允了。眉心红莲一消失,素影便觉得清淡许多,不算从前那般妖娆了。小丫鬟羞怯怯地为她拿出一件马装替她换上。
月白色的马装,将腰型束得极美,袖口处被银环扣着。领口高起,潇洒恣意。长而墨黑的发绑在脑顶,额际两缕碎发随风飘逸,倒颇有几分风流雅士的风情。
她又递给素影一银色马鞭,握着很舒服。
小丫鬟捂着唇羞涩得咯咯笑:“素姑娘你生得真是俊俏,无论穿什么衣服都这样好看。”
素影回过头轻轻翘起唇角:“谢谢你。”
小丫鬟又道:“不敢不敢。对了,太子殿下吩咐奴婢带姑娘去府内马场,姑娘可准备好了?”
素影淡淡点头。
马厩中一匹红棕色的骏马见着她就冲了过来,亲昵地蹭了蹭她的鼻尖。素影有些惊吓却没退步,伸出手拍拍它的头。
她的手不过刚碰着缰绳,便被另一只手牵了去,转头对上的竟是俊美如玉的男子脸庞。这个人她倒是见过的。
“六爷万福。”
他笑笑:“免礼。”
她抬起头,静静地接受他从上至下的打量。
“这一身行头,真是风流潇洒。”
竟跟她想到一块儿去了?她笑着说:“六爷勿要取笑我了。”
他淡笑不语。
素影看着他,不禁咋舌,这男子真是百年难得一寻的俊朗温柔,为人宽厚,高华风雅。他的笑容就如同一阵清风拂面,让人道不明的舒适。
他牵着马走在前头,身后的小丫鬟捂着唇暧昧地笑着去了。素影脸上烧得可怕,还是迈开了步伐紧跟在他身后。
骑马场中十分热闹,莺莺燕燕花花绿绿,甚是养眼。几位富家公子哥马上风姿英俊洒脱,笑容不羁,公主们骑马动作不断变换,马上马下动作行云流水一般。一片叫喝鼓掌声和嘚嘚马蹄声相互应着,很有节奏感。
纳兰天漓扶着她上了马,自己也翻身稳稳落座在马背上。
一阵疾风从耳边扫过,她只看见那飘逸的黑发和火红的马装,身下的白马英武有力。那双眼睛侧过头时冷眄她一眼,她顿觉身体血液被冻结,灵魂似被那双深不见底的洞吸了进去。似曾相识的情景,她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
似乎脑海中有那样一个冷漠而无情的背影,一双沉默而幽深的眼睛。
转过头去,却见纳兰天漓笑望着她,从容温和,刚才的忧郁全然被这一个眼神一扫而空,满心欢喜。
他笑问:“觉得眼熟?”
她挑眉淡然道:“没有,觉得他风姿不错。”
马场气氛极为热闹,可素影却总感觉一股冷气流围绕着自己,回过头一看却是一片寻常景,这寻常使得她不再寻常,非要捉出来弄得她浑身不适的这个人不可。趁着他们玩得尽兴的工夫,她静静地退了出来,眯着眼看了一会儿正俯身驾马的纳兰天漓,后者对她一笑。
她到暗处下了马,觉得前方有着冷冽气息,抬头见着一笔挺黑影,刚欲偏身轻手轻脚离开,就听见一低沉男低音:“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她讪讪地笑:“我闲着没事,过来散散步。”
身后的人道:“为什么不敢看我?”
清冷的气息一下子包裹住她的全身,身后的男子与她近在咫尺,她不动声色前进一步,与他保持距离。“没有,只是不想转过来罢了。”
纳兰天尘一声大笑,两只灼热手掌倏尔握住她纤细的腰肢,将下巴搁在她肩窝里磨蹭几下。他炙烈的呼吸喷撒在优美的颈项上,亲密暧昧。匪夷所思的是,她完全不想反抗这种亲密。
“若澜……你为何回来,是准备原谅我了?”
一声若澜将她思绪唤回,原是将她当做了别人呵。毫不犹豫地想要推开他,他却将手臂收得更紧,把她困在怀抱里。他只想感受她的存在,至于她想如何报复他,他完全不在意。
“这位公子,男女授受不亲,我仍待字闺中未嫁,你我不过初次相见,便这样毁我清白,可叫我情何以堪啊?”天知道她昧着良心说这话时是多么视死如归。共产党员是从来不说谎的,她多么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啊!
腰上的手臂又紧了紧,几乎要将她肺里的空气全部挤压出去,他自嘲道:“你就这么恨我?恨我恨到想跟我撇清关系?”
她苦笑:“大哥,你手臂松点儿成么?再说,那什么,我确实不认识你啊……这不过我们第一次见面,你虽非礼了我,我却也不太介意,如此,何时生的恨呢?”
他将她的身子转了过来,掐着她的下巴沉声问:“你不认识我?你竟敢说你不认识我?”又发现自己太过暴戾,柔下语调道:“若澜,你听我说,我所做的皆是为了保护你,你这么冰雪聪明,断不会看不出来。”
她看着那张比女人还妖美的锥子脸,狭长的眼阴戾一闪而过,琥珀色的瞳孔晶莹清透,一时间忘了反应,良久之后才道:“你说我冰雪聪明倒是极对的,至于旁的,我根本不知你在说什么。”
坚挺的鼻尖下优美的唇,苍白凉薄而坚定,那唇中发出一声轻笑:“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他怎么会笑呢?
半晌,她问:“我应该记得你?”
“不应该。”
纳兰天尘听见动静,皱了眉头侧身进暗处。纳兰天漓驾着马过来,伸出手带着她的赤电一同牵过来,柔声问:“怎么了?”
素影迷惑地看着他离开的方向,转回目光道:“方才有些晕了,来这里避避暑气。”
两人身影渐远,纳兰天尘只听见一句话,便似有所悟:你与太子为何想要利用我?
冷玉潇从旁边走过来,轻声问:“那个女子,倒真像是若澜。”
纳兰天尘冷笑,偏过头皱眉道:“你一卞国战神,怎么像是个幕僚一样……”
江南几舟水患历经秋冬两季,终于平歇下来,恢复男耕女织的和谐之景,朝廷分拨的银两也甚足。民心初初落稳,便被另一场灾难闹得人心惶惶。由洪水带来的家畜腐烂后散置各处,引发了不治瘟疫。此疫一起,气势便是嚣张跋扈,病种落播各人烟聚集地域。短短五日,因瘟疫故去的百姓已达七十余人。沾染其病者达二百有余。
天帝下旨封闭疫区,更失了民心,徒叫百姓失望。
昭帝二十八年夏,帝见诸位已有爵位皇子,研讨病情控制瘟疫。各位皇子皆用心出谋划策,帝觉并非甚善策,将此事一直拖延下去,帝甚忧。
昭帝二十八年五月初三,疫区死者达二百许人,无药可医,亦无良策。
天帝阅着折子,骤然大怒,将折子摞掀翻在地,怒喝:“一群没用的东西,私吞财物之时个个精明,细细打算,此时倒只会上书告诉朕‘臣等无能为力,无策以治。’朕要他们何用?朕阅奏折又有何用?”
案前的御前侍奉皆砰地齐齐拜倒在地,神色惶恐不安:“皇上息怒!”
李福回头使个眼色,同侍女们一起捡着奏折,天帝喝斥道:“捡折子有甚用!不必了!你们退下,李福你留下来。”
侍女们赶紧福身告退,李福看着她们离去才回头继续捡折子,忽然看到一上面最后一排书着“妾自知身份卑微,但仍愿皇上肯召见,妾定与皇上分忧。”的字样,于是没胆子看前面的内容,只扫了眼落款,觉得甚眼生。
李福捧着折子放到乌木案上,将刚才那本放至最上,呈给天帝。
天帝皱眉揉着太阳穴:“这些只顾福不顾忧的贪官,要他们真是半点用处也无,白白将国库里的银子被他们贪走。”
李福握着拂尘,欷歔道:“皇上莫气坏了身子,折子若不想阅就勿要再阅了,奴才扶皇上到偏厅休息罢。”
天帝松开手,被李福提醒才想起仍有一半折子未批,再怒也要看:“唉,国事第一,岂能说不看便不看。”而后随手拿走最上面的折子认真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