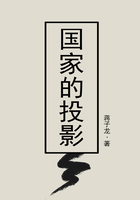早饭后,一团派一辆吉普和一辆中卡——他们都叫它“四分之三”来接我们。人人都很兴奋,坐在车上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唱,像一群从笼子里放飞的鸟。
吴安一说:“留守处的乔莹来信了,说长春被共军围得像铁桶,粮食紧张,当兵的都吃不饱,老百姓饿死老鼻子啦。”孔亮忧心忡忡地接过话:“沈阳也够戗,北边开原、法库,南边鞍山、营口都是‘老八’的了,闹不好沈阳也得像长春一样。”“喂,少说点儿丧气话行不?你这是长共产党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别把马路上听来的消息到处乱说。”梁大戈的脸拉得长长的。
我对这个人一点儿也不了解,只知道他会打鼓,是队里的情报组组长,情报组是干什么的,政工队里为什么要设这个组,谁是他的组员,这一切我都不清楚,既无人告诉我,也无人提及它。
“怎么是马路消息?我是从《扫荡报》上看来的,不信你自己去看嘛。什么叫长共产党的志气?哼!”孔亮指着自己的鼻子气呼呼地说,“干脆你把我当‘赤特’给肃了吧。”“打住,打住,越扯越远了,咱当兵的只管听上峰的,让往东就往东,让往西就往西,少操没用的心。”吴安一嬉皮笑脸地说。
“茶馆、戏园子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所以奉劝各位也莫谈国事。”姜瑞田做个“暂停”的手势给孔亮递眼色。
“咱们都是政工人员,不谈国事谈什么?眼前最大的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戡乱,对剿匪戡乱不利的扯淡话倒是应该‘莫谈’。”梁大戈脸红脖子粗,那样子怪吓人的。
“得,得,算我没说,算我多嘴。”姜瑞田不屑一辩地把脸一扭哼起小曲儿,“天牌呀地牌呀全不爱,单把那银牌抱在怀。……”车颠簸着,大家都闭了眼睛不再说话。一团驻地在铁西城乡结合部的一处旧军营,汽车通过大操场直奔团部,团长、团政工室主任以及政工干事一大帮人都出来迎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看着面熟,走近才认出是尹明,我来报到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我入队不久他就调到一团政工室当干事,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他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热情周到,和气可亲。
上午装台,大操场上有个洋灰砌的阅兵台,横三竖四架着木杆子,开会演出时用来挂灯吊幕布。以往爬高的活儿都由吴安一、徐伟做,韩德曾、于志强新来乍到,又比他们年轻,现在自然落在他俩身上。就在于志强爬下来取绳子时,韩德曾朝我喊:“安琪,帮帮忙,锤子掉了帮我捡起来好吗?谢谢啦。”我走过去把锤子捡起举给他,可是脚翘得再高也够不着。我搬来凳子站上去,晃晃悠悠心里直害怕。于志强急忙过来将我扶下,由他把锤子递上去。前天排节目时于志强极力反对唱《黄水谣》,韩德曾一直心存嫌隙,只管爱理不理地接锤子,不想失去平衡,身子一歪从木杆上掉下来。于志强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把他接住,可自己却被韩德曾手上的锤子砸破了头,鲜血染红了半边脸。我吓得大喊大叫,何队长、张队副都跑过来,立即派姜瑞田把于志强背到团部,简单包扎后又转到野战病院去。
韩德曾愣愣地站在那儿,半天才憋出一句话:“真是没事找事。”我一听就急了,愤愤地说:“你说什么呢?要不是为了你他能砸破脑袋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韩德曾见我脸色不对,急忙赔着笑脸道歉:“都怨我,都怨我,我不也是着急嘛。”“着急也不能好歹不分,什么叫没事找事?”我赌气扭头走开。
中午团部打牙祭招待我们,高粱米黄豆饭改成大米黄豆饭,豆子不比米少,菜是四素四荤。一个个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将八个盘子吃得像洗过的一样干净。我心里一直惦记于志强,第一次体验到为一个心仪的男人牵肠挂肚的滋味。
演出从午后三点开始,我从侧幕边上偷偷向台下看,大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步枪抱在怀里搭在肩上,齐刷刷的枪管闪着蓝光。
演出前黄团长致词,讲了一通欢迎、感谢的客套话,接着照例大谈反共、剿匪、戡乱。今天政工处处长丁怀仁也到场,在黄团长的盛情邀请之下也讲了话,对“劳苦功高的我军将士”表示慰问。
林婕担任报幕,她穿一套熨得笔挺的罗斯福呢军便服,头上歪戴着船形帽,脸白唇红卷发披肩,细腰上勒着皮带,脚上蹬着黑色高筒皮鞋,精神抖擞地走到麦克风前,不等开口就招来一片掌声和鼓噪。
第一个节目是轻音乐,演奏了《特别快车》和特意为广东籍老兵准备的广东音乐《步步高》《雨打芭蕉》《柳摇金》。
我被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所鼓舞,沉浸在从未经验过的亢奋之中。
接下来是女声独唱,我被排在最前面。听说小角色自然要唱“垫戏”,这是规矩。上台前我既未描眉也没敷粉,只在唇上浅浅地涂了口红。不想刚走上台,那些大兵比听口令还有效,刷地向我行了注目礼,接着便是一片震耳的掌声。
“这个小妞怎么没见过?”“新来的吧,真叫漂亮!”“看那小脸蛋儿,细皮嫩肉是怎么长的?嘻嘻。”“妈的,让咱们搂搂死了也甘心。”“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那德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嘻嘻嘻。”“哼,老子把脑袋掖在裤带上,有今个儿没明个儿,你们不是来慰劳的吗?那就来点儿真格的吧,哈哈哈哈。”……
大兵们一直坐到台根底下,七嘴八舌的混账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口哨声、叫喊声此起彼落。等我把两首歌唱完,台下依然不见平静,鼓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再来一个。”“咱还没听够哪。”我晕头转向地跑下台,跟站在侧幕后面的刘薇撞个满怀。她嘴一撇说:“怎么,找不到东南西北啦?别听见几声好就晕了头。”“大姐,对不起。”我急得要哭出来,“他们不是听歌,是拿咱们作践玩儿,我又讨厌又害怕,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嗯,你要是真明白这个就好。咱们是什么?是戏子,是花瓶,是摆设,是玩意儿,比婊子强不到哪儿去,多长点儿心眼儿吧,小妹妹。”“谢谢刘大姐,我一定记住你的话。”我不是敷衍,是出于真诚和善意,我知道她也是出于真诚和善意。
“我知道你这孩子挺懂事,我得准备上场了,有时间再唠。”刘薇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走开,这回好像少了许多情绪。
不等演出结束,何队长就陪着丁怀仁和一团黄团长跑到后台来“看望大家”。何勇把他们领到我跟前,眯起小细眼睛笑嘻嘻地说:“安琪呀,丁处长、黄团长特意来看你呢。”丁怀仁翘着兰花指梳理一下溜平锃亮飘着发蜡味的小背头,柔声细气地说:“你唱得很好嘛。”回头问黄团长,“怎么说来着?”不等回答自己先说,“对,声情并茂!她的《四季歌》还真有点儿周璇的味道呢。何队长,你要好好培养哟。”他针刺般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我脸上,吓得我赶紧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