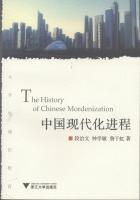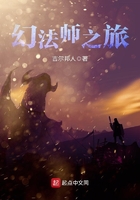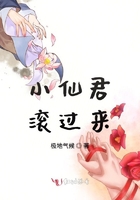那要看失败者是谁,是什么样的失败。从楚霸王的江边自刎到谭嗣同的视死如归,这类可歌可泣的人间悲剧可谓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败者”在荣誉上未必输给作为他们对手的“赢家”,倒是某些置对手于死地的“赢家”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人类还有很多谁都不愿意让它失败,但它又必然要经历或多或少的失败才可能成功的伟大探索,这类探索一时一地的失败肯定是“虽败犹荣”,而且是永远有光荣的理由的,比如美国的“挑战者号”失事。
这里我们主要想谈的,则是另一种失败者,我们身边诸多“英雄的失败”引发的荣誉问题。
禹作敏应该享有荣誉吗?他当年的确擎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并因此几乎被鲜花和掌声淹没。而面对由于自身局限而造成的突然坠落,历史老人只能付之以惋惜的苦笑。
牟其中应该享有荣誉吗?社会上虽然对他到底是“首富”还是“首骗”一度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分歧不大,即牟其中的思想观点启发了一批创业者和经营者,他自己看到、说到却没有做到的很多事情,他当年的朝拜者们却陆续做到了。
褚时健应该享有荣誉吗?用国家交给的一头奶牛为国家缔造出一个庞大的奶牛王国,就因为妄自接了一杯牛奶喝就差一点被拉出去枪毙……在社会上引起最大的荣誉观分裂的大概莫过于褚时健了。荣誉观分裂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分裂,是评判标准的南辕北辙。到底哪种价值判断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哪种荣誉观更应得到全社会的尊崇?褚时健妄自接奶喝肯定不对,因为他没按规矩办事。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规矩总是让那些能力强、贡献大、奉献精神比我们绝大部分人强很多倍的优秀分子被葬送掉,并连带给他们创建的各项事业造成重创,这到底是褚时健们的失败还是体制的失败?到底是褚时健们的耻辱还是体制的耻辱?“褚时健事件”发生若干年来,全国各地、各个领域又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褚时健事件”发生,除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的“硬伤”之外,这种导向效应又伤了多少人的心、泄了多少人的劲,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混乱了人们是与非、美与丑的标准?
以“褚时健事件”为镜,是重建我们的体制尊严、重建我们这个社会统一的荣誉观的时候了!
富人为什么而存在?
《中国企业家》2003年7月第7期
记得去年的某一天,社会上因查税风暴而引发了对富人种种议论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一个似乎荒唐可笑、估计李嘉诚先生听了也可能感到不悦的问题:李嘉诚为什么活着?
其实,如果表述得稍微准确一些,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李嘉诚为什么而活”,上面的表述方式只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命题的更大关注而已。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而且在今天又以“卷首语”的方式旧话重提?
中国自古就有贱商仇富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顺应大势,深得人心。但先富起来的人却难免鱼龙混杂,难免有一批人会钻政策漏洞、法律空子一夜暴富,暴富之后的某些表现又为贱商仇富的社会心理提供了新的理由。好在大浪淘沙的速度很快,劳动致富、创业致富、合法致富的主流迅速支撑起我们这个社会新的财富观,财富阶层尤其是创业致富的企业家阶层开始赢得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尊重,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也日益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时代英雄。
然而,先富起来的人毕竟只能是少数,几千年沉淀而成的社会心态也不可能猛然间得到彻底的扭转。于是乎,一有风吹草动,尤其是一有人们所熟悉的某个财富人物出了问题,就似乎整个财富阶层的来历都变成可疑的、靠不住的,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成为问题,似乎富人天生就是民众的敌人。
那么,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富人,是否真的了解作为我们主要评价对象的富人中的企业家呢?认真琢磨一下“李嘉诚为什么而活”,也许对我们真正了解和理解富人、对推动财富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融合大有好处。
李嘉诚到底为什么而活?如???是为了利,他已经是全球华人首富;如果是为了名,他不但已经名扬天下,而且有条件名垂青史;如果是为了成功,他已经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人士之一;如果是为了享受人间的各种乐事,凡是这个世界上有的,他想得到似乎都不会太难……思来想去,这些对别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似乎李嘉诚都已经做到、都已经超越了,他为什么对生活还那么大热情、精气神十足地对待每一天?支撑他的生命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也许,李嘉诚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说清楚的,那就是不唯李嘉诚,天下所有创业型的企业家,他创造的财富越多,这个财富与他个人的关系就越小;他创造的财富越多,这个财富与别人的关系就越大。因此,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天下真正伟大的创业型企业家,客观上都不是为自己而生,都是为别人而战,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使命而战的。
富人为什么而存在?一个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富人,越到后来他就越是在为别人、为社会、为我们而存在。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他们、爱护他们,千万不要动辄就因为一两个害群之马而误读他们、委屈他们。
富人就像大树,再高再大也需要合适的生态环境。而我们这些评价富人的人们,恰恰构成了富人的生态环境。在很多情况下,是我们的评价与目光决定着“富人的存在目的”。假如一个社会的舆论最终让富人退化到“只为自己活着”,那才真是最不幸的事情。
道成肉身之道
《中国企业家》2003年1月第1期
“圆满闭幕”、“精彩落幕”,分别是两大门户网站新浪与搜狐在对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进行全景追踪后总结式报道的栏目标题。会中和会后,不断有经常出席中外各种重要会议的企业领袖和学者对我们表示由衷的祝贺和鼓励:“没想到年会开得会这样成功,《中国企业家》做事情就是不一样。”“这是我所参加过的国内(面向企业家的)最成功、最有收获的大会。”“真没想到在一次会议上可以见到这么多的重量级人物,而且都是有备而来……”
积累了许多年,筹备了5个月,我们自己对这届年会满意吗?借用张瑞敏在年会演讲中的一句话,“帮助用户成功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功”,与会代表满意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但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这届年会只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开始,正因为是开始,所以与会代表和嘉宾才没敢对我们抱有太高的期望;正因为期望不是很高,所以才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才会给予年会各种各样过高的评价。我们也深知,作为读者,企业家是这个社会上最挑剔、最难伺候的人群,作为与会代表,他们将会更加挑剔和更难伺候,因为他出于对你的信任,把他看得最重的宝贵的时间交给你去安排了,把他的一部分生命托付给你了,那么,你能否把他的这点宝贵时间,比他自己,比那些天天研究他的需求、处心积虑要满足他的需求的其他机构安排得更充实更精彩也更有价值?应该说,这既是我们的压力所在,也是我们的动力所在、信心所在。因为我们太了解企业家、太熟悉这个群体,也太理解这个群体了。
比如说,谁都知道企业家是求真务实的实干家,是最讨厌空谈、最讨厌坐而论道的,我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办杂志,反而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去专门搭一个让企业家们坐而论道的平台,而且还期望把这个平台越搭越大,把这个年会越办越火呢?
很简单,在别人眼里,企业家可能是一个个日理万机、疲于奔命,为挣钱和各种俗务所累的“肉身”;而在我们看来,每一个创业者、企业家,更不用说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企业领袖,他们的“肉身”只不过是“道”的载体,是他们使命和梦想的载体。企业家创业的过程,也就是他们“道成肉身”的过程;他们想要追求的成功越大,就需要越多的人相信这个道、理解这个道,需要越多的人成为这个道的“肉身”。而这个“道”之所以可能被众多的“肉身”所接受、所推崇、所遵奉,又一定是因为这个“道”是合乎“肉身”的需要,“道”、“肉”是能够合一的。因此,如果说到“坐而论道”的价值,别人可能论完了就完了,这个“道”对不对无所谓;而对企业家们来说关系就大了:“道”对了可以成“肉身”,而且可以不断地成更多的“肉身”,“道”不对则可能被“肉身”所拒绝、所抛弃,最终导致“道肉分离”、创业失败。
如此,以“道成肉身”为使命,也最善于使“道肉合一”的企业家们,怎么可能不看重真正有价值的“坐而论道”呢?
2002年
企业家的政治预期
《中国企业家》2002年12月第12期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即使像白毛女一样逃到山上去,过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其实也不过是当时一种政治关系的结果。因此,人无往而不在某种政治生态之中,区别只是你自觉不自觉、与这种生态和谐不和谐而已。和谐了,你的状态可能就滋润、健康、安全,不和谐甚至对立起来,你的状态可能就痛苦、脆弱、危险,乃至一不留神就可能成为某种势力的牺牲品。
政治家们竭力维护的通常是一种大的政治平衡。这种平衡存在,政权就稳定,社会就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小的不平衡或某种局部利益的被忽略、被牺牲,往往被视为自然的或必要的代价,历史上的当权者们很少为此忧心如焚、睡不着觉的。只有伟大的政治家,才善于谋求并造就政治生态最大限度的和谐与共荣,在巧妙驾驭主要矛盾、强化主要逻辑的同时,还努力做到“阳光普照”,实现与大大小小各阶层、各利益主体的逻辑对接。
毋庸讳言,许多有识之士一度产生过深深的忧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打天下”出身的执政党,在“坐天下”的过程中能否一直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正确把握前进的方向?能否一直站在时代的潮头,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开辟道路?之所以产生这种担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人或阶层,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偶尔会感到自己的逻辑与上面的逻辑是错位的,自己的利益诉求与上面的利益诉求是矛盾的,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上面的话语体系是有隔膜的,有时甚至相互之间听不懂或不愿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那样说。令人高兴的是,基于2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和深厚积淀,江泽民同志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透过2001年的“七一讲话”和不久前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人们突然发现党实实在在又走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春天,在这个春天,似乎每个人、每个合法的利益主体、每个阶层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而安全的位置;在这个春天,气候、土壤、环境和每一种动植物都有望达到最大限度的和谐。
十六大刚刚落幕,撇开国内外传媒对十六大浩如烟海的报道与评价不说,十六大到底做了什么?当然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朴素地看,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两件:一是几乎零成本地完成了共产党自身的转型与革新;二是圆满完成了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权力交接。这两件事加起来,则又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企盼已久的东西:对党和国家积极、稳定、乐观的政治预期。我们的企业家阶层尤其需要建立这种预期。
6年前,我们曾隆而重之地推出了一个重要理念: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有人提出异议说,政治家的位置往哪儿摆?我们的回答是:政治家是创造空气和土壤、是为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只有政治家创造了风调雨顺、安全持久的生态环境,企业家才可能建立积极、稳定、乐观的政治预期;企业家只有建立了积极、稳定、乐观的政治预期,他们才可能彻底静下心来研究市场、经营企业,为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你看,好的政治家岂不是特别重要,也特别伟大吗?
张瑞敏比我们傻吗?
《中国企业家》2002年8月第8期
去年(2001年)下半年以来,经常会有各界朋友提出对海尔这样那样的质疑。因为我们离企业更近些,离企业家更近些,很多质疑就难免提到我们面前来,以求得印证或某种程度上的答疑。
作为与海尔有较多接触但又谈不上有真正研究的媒体人,我们当然不敢担当解疑释惑的角色。但既然不断有人问起,就难免作些思考,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尝试着作一些回答。在饭桌上和其他的聚会场所,我不止一次地向质疑海尔的朋友提出反问:你认为张瑞敏比我们傻吗?
在对更多的事情难以作出判断之前,人们对这个问题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即从他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来看,张瑞敏绝不会比我们傻。那么,既然承认张瑞敏不可能比我们傻,我们为什么还会拿办企业的那么多常识问题去很认真地质疑海尔、质疑张瑞敏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海尔,并不真正了解张瑞敏。那么,海尔为什么不大门洞开,热情地欢迎我们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去仔细地观察他们、深入地了解他们,而是给人们留下那???多疑问那么多谜,让人们越来越大胆地去进行一些不利于海尔的猜测和假想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想在这里替张瑞敏作出的一种解释是,他是迫不得已,就像一个魔术大师在舞台上变戏法,戏法变了一半的时候观众非要知道这戏法是怎么变的,你让他怎么办?可能有人会说,变戏法主要靠暗箱操作,搞企业却应该是全透明的,你怎么能把办企业与变戏法相提并论呢?办企业与变戏法当然不一样,但二者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决定了看得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张瑞敏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家中运了最长的一口气,想在自己任上画一张最大的企业版图,实现最大的企业循环的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另一位最了不起的企业家柳传志,他在以16年的努力完成了联想的第一个伟大的循环之后,顺利地把联想可能的更大的循环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去完成,在给自己的人生和事业画上了一个功德圆满的阶段性句号之后,应该说柳传志没有留给人们更多的悬念。张瑞敏不同,他仍然跋涉在自己设计的巨大的海尔循环链条之上。构筑心中的海尔帝国,张瑞敏也许需要再付出10年、20年甚至毕生的精力,而且越来越多的是在没有航标的水域里行船,越来越多的是在挑战各种不确定性与未知世界,那种凄美悲壮的孤独感是很难被人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瑞敏是当今中国最孤独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