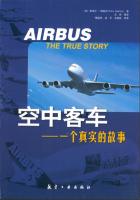在1979年5月,谷牧同志讲“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说是鼓励大于自信的。即使不怀疑中国人的能力,我们仍然对当时的特区决策充满着重重疑虑。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形成了转向经济建设的共识,但是如何开始经济建设?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如何改革一个形成了几十年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改革有没有可遵循的方案?到底从哪儿开始?什么是突破口?应该保留多少计划?引进多少市场?改革的目标模式到底是什么?对于政府而言,这些还都是未知数。而且当时,以前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经济理论界的权威统治时期,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或者“主义”)还仍然是中国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核心概念框架。因此,今天我们对三十年前深圳和珠海等为什么能被中央考虑并批准成为“特区”充满好奇。
回想起来,中国经济改革这三十年的过程,固然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创造性的做法和现象,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和研究。但从根本上讲,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始终采纳的是一种折中的道路。我们在中国的党政文件和媒体上经常见到听到、也习以为常的说法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或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什么那么多的政治家、官员、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不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私有制或者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之类的提法,却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提法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和认同?真是奇怪,中国经济转型的这三十年,始终没有脱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框架。如果它是杂乱的和缺乏逻辑的拼盘,那么它的生命力来自何处?
显然,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和制度结构给予更多的关注,但这却是我一直不愿意放弃思考的题目。为此,我也总是不断地去阅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而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感受。作为政治家的文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每句话似乎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有它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意义和力量。同样,尽管深圳的这个试验带有自发和倒逼的性质,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要在广东沿海一带正式设立经济特区并且中央要作出这个关于特区的决定,听上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更不会没有政治上的斗争。但是,这个决策似乎又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困难。这当然与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头脑中就有的局部开放思想和沿海发展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是唱遍大江南北的《春天的故事》里的歌词,形象而夸张地描述了深圳经济特区的由来。为了搞清楚设立深圳特区决策的提出和批准经济特区的政治决策的过程,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初发现整个决策过程的线索特别多,要理出一个头绪还真不容易。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里面不光涉及深圳特区的形成及其决策过程,还有一段关于深圳的蛇口与香港招商局的插曲,而蛇口工业区的成立要早于深圳特区。这个故事我会马上讲述,但总的来说,围绕深圳而发生在1978~1979年这一年的高层决策是非常值得记述的一个关于三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片段。那么,让我从1978年关于蛇口的故事说起。
历史的安排往往就是这么巧妙。在1978年年初,可以说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和改革开放的前夜,可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却掀起了一次出国考察热。据说一年里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邓小平也在这一年访问了日本、欧洲和亚洲。在1978年10月的最后一周里,邓小平访问了日本;11月5~14日,邓小平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他访问日本时,日本现代科技的发达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本体验了“新干线”,还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我在后来的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片段,印象颇深:邓小平在参观松下电器时,在一间展示微波炉的展示厅里亲口品尝了用微波炉加热后的烧卖。
后来,邓小平到了“新马泰”,它们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国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就在1978年4月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也曾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前往香港和澳门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内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刚从西欧考察回来的谷牧副总理深感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然对这个及时送上来的报告十分赞赏。于是,1978年6月,该报告就得到中央领导人的同意,并且鼓励把出口基地办起来。
这个决定促使当时交通部驻香港的商业机构“香港招商局”(前身是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的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在1979年的元旦之后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交了一份建议报告,主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个码头,发展招商局与香港的贸易。他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贵,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与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一定是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与谷牧。于是他们召见了袁庚,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决定给袁庚“一个半岛”去试验。袁庚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思想不够解放”,不敢要个半岛,而只要了2.14平方千米。就这样,“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在1979年年初挂牌成立了,于是也才有了后来关于“蛇口模式”的说法。事实上,在经济特区以及后来在整个中国推进的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都与“蛇口模式”有联系,是从“蛇口模式”扩散出去的。
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往往就是这样,只要是成功的做法,试验区的经验和模式很快就扩散出来,被别的地方吸收。我在2007年5月去参观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时就有很强烈的感受。我在想,为什么邓小平和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的万里对小岗村1978年“违规”的“包产到户”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而没有坚决取缔?一直有人传说,在邓小平看来,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过是一个小的试验,等做了之后并且看到了结果再下结论也不迟。我在国外讲课中经常会把这个细节与著名的耐克鞋的一句广告语“Just do it!”联系起来,每次都会引来学生们的阵阵笑声。
当然了,成立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还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等对开放中国经济有一种紧迫感。而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头脑中设想的蓝图似乎就更遥远更透彻了。我至今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邓小平在他第三次复出后不久的1977年11月会首选到广东深圳这个边陲小镇考察。实际上,从深圳回到北京之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深圳这个地方,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提到深圳。我想,深圳的恶性偷渡逃港事件肯定让老人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所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想法和政治策略了。于光远先生在几年前有过一次回忆,提到了有关邓小平的一个细节。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2004年)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其中涉及有关深圳经济特区决策前后的话题。于光远先生回忆说:“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就在这期间邓小平又被打倒。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也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1978年我参加了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实行党中央五个常委集体领导的办法。这五个常委就是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主席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四个副主席。他们差不多每周都要听取一次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六个代表团的汇报,汇报时各常委的发言和插话,由各代表团去汇报的人回去传达。大会对传达没有什么限制,各常委也就利用这个方式去讲想让参会的人知道的话。其中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举了十来个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而且说的就是深圳这个地名,而不是宝安。”
其实,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因为国务院于1978年6月决定同意《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的建议,要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建设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于是,在1979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38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为了凸显宝安的重要性,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成深圳市并在之后改为省辖市。
于光远先生还回忆道:“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把深圳放在首位,就是要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的办法。而这件事情的责任就落在吴南生身上,他在1998年和记者谈话时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其中包括‘发愁这块地方叫什么名称好呢?’他想可以叫‘出口加工区’,但这就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也可以叫‘自由贸易区’,但那又‘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吴南生为这件事请教叶剑英,叶剑英要广东省赶快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说要划出的地方的名称老是定不下来,他就说那就叫它特区吧,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邓小平这句话使吴南生觉得事情就好办了。”
对于经济特区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后来吴南生先生有过一个更详细的考证。而且对过程交代得非常清楚,也涉及很多的人,这里我就不去细说了。其实,我在阅读中注意到,广东省领导人在1979年年初已经有按照特殊政策的待遇先走一步的想法了。
根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徐现祥和陈小飞的文章,1979年1月底,广东省省委书记吴南生就带领工作组到汕头市开展调查工作。期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汕头可否仿照台湾的做法也办一个出口加工区?在历史上,汕头是中国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在五口通商时代就开始了。甚至恩格斯都曾为汕头写下这样的文字:“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与香港的差距并不大。吴南生的设想得到汕头地方领导认可。之后,习仲勋和吴南生一起向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这个设想,叶帅听了非常高兴,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2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公开向中央“要权”,他说,如果中央能给点权的话,“广东几年就可以搞上去,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尤其谈到,广东要求中央能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部分区域实行单独的管理,给些特殊的政策,自主权大一些,作为华侨回来投资办厂的地方,可以叫做“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还在叶剑英的授意下在邓小平家里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在这个时候,提出希望实行特殊政策的不仅有广东,福建也曾提到了特区试验的想法。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还组织中央部委领导前往广东和福建进行了考察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达了5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划出一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发挥比较优势,吸引外资,把经济搞上去。但报告主张先在深圳和珠海试验,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和厦门。50号文件特别强调了要重点把深圳的出口特区办好。
《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披露,1979年12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召开第一次特区筹建的专题汇报会议(京西会议)。吴南生在汇报筹建工作时建议把“出口特区”改成“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将“出口特区”改成“经济特区”。根据徐汝超的介绍,当时对于深圳特区的划定面积也有争论。为了划出深圳特区的范围,深圳的领导张勋甫、贾华和方苞等带队实地察看,最后经市里反复讨论,确定深圳范围为,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一甲村,东西长49千米;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岭,南至深圳河,南北宽约6.5千米,总面积327.5平方千米。
但是这个规划的范围遭到当时“省特区办”的否定,理由是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张勋甫等人就回复“省特区办”,深圳特区比延安时期“陕甘宁”小得多,应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国,特区是全国的特区,6平方千米这么小怎么“杀”?“省特区办”来电话说:你们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最后这件事情一直等到请示了北京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当时的主任是江泽民)才最终获准这327平方千米的范围。
与此同时,一部关于特区的法规条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仅仅2000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13次之多的修改,终于在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被批准公布。一部地方法规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审议批准还是一个例外。而8月26日这一天也就从此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日。
转引自董滨和高小林著《突破--中国特区启示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但是虹霞在《中国经济特区的形成之路》一文中则提到领导人的出国访问是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见《纵横》,1999年第4期,第39~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