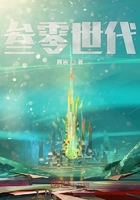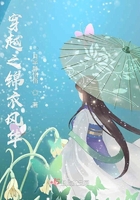突然,院子里传来沉闷的一声响。乔老大立即警觉起来,一骨碌坐起,爬到窗台上朝外看,也没发现什么,紧张的神经又松弛下来。
这时,乔老大听见柳霞开门的声音,便问:“这么黑的天,你还干吗去?”柳霞:“上茅房你也管呀。”柳霞走进院子西南角的茅房。片刻,一个黑影向茅房扑去。茅房里很快传来柳霞大喊救命的声音,但只喊了两声就不再喊。
乔老大一激灵爬起,到外屋抄起顶门杠,很快冲向院子。乔老大冲进茅房,举起顶门杠正要打,被二丫头粗壮的双手架住。二人厮打到院子中央。
二丫头不敢恋战,推开乔老大就去爬墙头。正当二丫头要跳下墙头的一刹那,乔老大的顶门杠也砸了下去。二丫头哎哟一声惨叫,滚到墙头外。
二丫头躺在地上抱着腿疼得打滚,口中不住地哎哟。
乔老大从墙头上跳下,仍对二丫头拳打脚踢。二丫头只是呻吟,却不哀求。
乔老大余怒未消:“你这个混账东西,连猪狗都不如!我真恨不得一下打死你!”二丫头辩护:“船主,其实我是好心,我是想照顾您,是想给您养老。柳霞她被安文忠迷了心窍,就是看不上我,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乔老大越听越气:“狗东西,你是在算计我的那条漕船。我让你算计,今天把你打死拉倒!”二丫头见情势不好,立即大声说:“打死我不要紧,官府能饶了您吗,您犯了事,柳霞怎么办?”二丫头的话果然说到了点子上,乔老大的顶门杠举到半空又停了下来。
周围邻居被惊动,纷纷赶来看究竟,纷纷指责二丫头办了一次不该办的事,又劝乔老大消消气,二丫头已经被打折了腿,就饶他一条命吧。
大家把二丫头抬回了家。
杨柳青猪市大街正逢集日,集上人山人海,各种店铺林立,摆摊卖农产品的也很多。
各种小吃应有尽有。
柳霞在集市上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挤在人群中。
曹家胡同口内也有不少货摊,卖各种妇女用品和小百货。柳霞来到这里,在一个卖丝线的货摊前停了下来。柳霞挑选着颜色艳丽的丝线,很快挑了一大把。柳霞付完钱后朝胡同的那头走去。显然她不愿意再走拥挤的集市。
柳霞发现迎面走来三个人,为首者一身绸缎,头发油光瓦亮,手里拿着折扇。柳霞不敢再抬头,低头靠边走。拿折扇者故意挡住她的去路。柳霞抬起头,恼羞成怒地瞪他一眼,继续走。穿绸缎者面带邪笑,两只眼不住地在柳霞身上上下转悠。
柳霞十分气恼,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将他推向一边,硬是挤了过去。穿绸缎者故意使劲碰柳霞一下。
柳霞回头骂道:“不吃人粮食的东西!”穿绸缎者使劲拉长声:“嗯——?”随即冷笑,命令两个随从:“给我盯着,看她是谁家的丫头。”随从答应一声,便尾随柳霞而去。
柳霞匆匆走进家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正发现那两个尾随而来的人。她的心一阵猛跳,赶紧插上了门。
两个随从走进大宅豪门,过屏风向第二进院子走去。
迎面是一个很讲究的正厅,正厅右侧是书房,左侧是卧室,一个人正在卧榻上吸鸦片。随从毕恭毕敬地:“三爷,我们都打听清楚了,那丫头家住河南岸东大街的崔家胡同,是养船户乔老大的女儿。”三爷从鼻子眼儿里哼了一声,轻蔑地:“原来是那个穷窝子里的人。这么穷的地方也能生出美人来,杨柳青这地界真是怪了。就这些吗,你们难道不懂我的心思吗?”另一个随从:“我们当然知道三爷的心思。我们来这么迟,就是打听事儿去了。据说,这个养船户乔老大很财迷,势力得很,一心一意只想攒钱买砖瓦房扎到这河北的富人区。他也很想把他如花似玉的丫头嫁给富人。总之,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离开河南边穷人居住的地方。”三爷突然坐起:“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你们快去找郑铁嘴呀!”柳霞正在布上比画花样子,突然听到敲大门的声音,急忙去开门。
乔老大提着鱼篓扛着鱼网不耐烦地进来说:“大白天插门干吗?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这是怎么啦?”柳霞羞恼地:“我去集市买丝线,遇上坏人了,有人跟踪我。”乔老大一惊:“啊,真的?你说你,又买哪家子丝线,整天缝啊绣的,那有什么用?告诉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你就是不听!”柳霞噘起嘴:“我就绣。”乔老大把眼一瞪:“你又犟!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柳霞正在收拾爸爸捉来的小鱼。郑铁嘴一脚走进来:“乔船主在家吗?”乔老大探出头:“呀呵,是您呐,郑婶儿。您可是稀客。”郑铁嘴仔细端详着柳霞:“哟,你瞧瞧,这丫头真是越变越好看了,脸蛋儿比粉扑扑的桃花还漂亮。”柳霞红着脸冲她笑笑,没说话。郑铁嘴跟乔老大进了里屋,放下了布帘。
郑铁嘴悄声问:“你这丫头有婆家了吗?”乔老大:“还没呢。怎么,你想给说一个?要说,你就给说富裕的,有青砖大瓦房的,有漕船有车的,或者是有地的。要是这河南岸的穷户,你就免开尊口。”郑铁嘴巧嘴巧舌地:“那是,那是。这么好的丫头,哪能让她受穷呢。有个歌谣不是说啦,‘在河南,穷人多,种地卖鱼卖柴火。拾柴火,跑细腿,棒面饽饽喝凉水’,就这样的地界儿,不光你闺女不能再住,就是你也不能再住。”乔老大:“你先说是河北的谁家。”郑铁嘴:“那可是咱们镇上有名的大财主。他家有良田百顷,漕船十几只,另在天津、沧州等处开有当铺。他还头戴红顶子呢,捐了个五品知府的官。他说了,只要你答应,他就给你一个河北边的青砖瓦房四合院。”乔老大不高兴地提高了嗓门:“你说的是曹家胡同的那个李占山吧。他可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家中已有一妻一妾,你不会不知道吧?你要让我的女儿去当他的三姨太?你这不是拿我们爷们儿糟改嘛!”郑铁嘴立即提高嗓门:“哎,乔船主,我这可是为你好。你拼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拼出一个四合院来。这样的大好事天底下哪儿找去?知道不,有好多家让我去说呢,想当三爷三姨太的人有的是。你要是嫌不合适,我可以让他再给你两只大漕船。”乔老大有些蒙:“啊?他真的给?”“还有三百两银子的聘礼呢!”乔老大动了心:“噢?”在外间屋做饭的柳霞总算听明白了屋里在说什么。她气得忍无可忍,抓起烧火棍,“啪”地撩起门帘,怒声问:“你说的那个三爷是不是住在曹家胡同?”郑铁嘴见柳霞手里拿着烧火棍,有些惊慌地:“是啊,孩子。曹家胡同是咱杨柳青的最高处,那可是地皮最贵的地方。”柳霞怒吼道:“就那个大坏蛋!你去给他当三姨太吧!你给我滚!”柳霞真的动了烧火棍,朝郑铁嘴屁股上狠打一棍。
郑铁嘴吓得直蹦:“哎,你怎么打人,哎哎,你别打人!”边说边向外跑。
乔老大板着脸,默不做声。
郑铁嘴跑了后,柳霞质问乔老大:“你是不是动心了?告诉你,他就是给金山银山也甭想!”柳霞冤屈得大哭,大声地喊死去的妈妈。
乔老大还是不做声。乔老大见柳霞只是哭,不再做饭,只好自己去收拾鱼。
天黑下来了。乔老大喊柳霞吃饭,柳霞不答应。
第二天,乔老大提着鱼篓扛着鱼网要出去打鱼,正遇李占山带人进院子。
乔老大有些紧张地问:“几位找谁?”李占山彬彬有礼:“你就是乔船户吧。鄙人李占山前来拜访。”乔老大闻听,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慌乱地深深一揖说:“呀,是李三爷光临寒舍。您可是镇上数得着的大财主,听说上面又封您一个五品知府的官衔,三爷真是洪福齐天,门庭光耀得很哪。快请屋里坐。”李占山摆摆手:“我更愿意看一看你这土屋土院土门楼。是够寒酸的,明日搬河北去住吧,我给你个青砖青瓦的四合院。”乔老大一下脸红起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胡乱地说:“土屋土炕的,也没个地方坐,慢待您了。”李占山一摆手:“不用坐。听说你的女儿把郑铁嘴打了。哈哈,真是好性情。可惜她不知道,想给我当三姨太的人有多少。就说我给的那些聘礼吧,乔船户,你这一辈子能挣那么多吗?”乔老大唯唯诺诺地:“不能,不能,对我来说,那是不敢想的事。”李占山:“所以,你要好好劝你的女儿,不要想不开。”柳霞在屋里做针线活,外面的事已经全部知晓。当她听了那话后,心中怒火陡然升起,竟顾不得女儿家身份,箭步冲出门去,大声斥责道:“是谁在那里胡吣!想打这姑奶奶的主意,你是瞎了狗眼!”乔老大一惊,立刻拉下脸来,厉声呵斥道:“不许无礼!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快给我回屋里去!”柳霞却不听,手指李占山骂道:“穿得倒是周武郑王,其实是装着满肚子臭粪!在曹家胡同你干的是人事吗?出去,都给我出去!”李占山假装大度。随从不干了,上前说:“你再骂三爷我就对你不客气!”乔老大害怕得罪李占山,要当着他的面责罚柳霞,抓起一把扫帚,朝女儿扑去。柳霞机灵,撒丫子朝门外跑。乔老大更加生气,奋力去追,恨不得一把将她拉回家来。柳霞跑到胡同里恰遇安文忠的三弟安文玺和他的几个伙伴。
安文玺见状,上前拦住问:“柳霞姐,你这是怎么了?”柳霞上气不接下气地:“那个穿绸缎的欺负我。昨日在集市上故意碰我,让郑铁嘴来说媒叫我打跑了,今儿竟带着人跑家里来啦!”安文玺性情比较刚烈。他很仗义地:“柳霞姐,别怕,我大哥不在家,还有我呢,看谁敢欺负你!”乔老大追了上来,李占山和两个随从也紧紧跟上。
安文玺却没在乎,手里紧握着弹弓冲李占山嚷道:“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胡作非为!我们人穷志不短,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你要是再敢欺负人,我就让你知道我们穷人的厉害!”李占山不紧不慢地问乔老大:“这是你什么人?”乔老大慌乱地:“啊是,是邻居。他们家人都是我的纤夫。”李占山冷笑道:“嘿嘿,原来是纤夫的兔崽子。”安文玺:“柳霞姐是我大哥的人!我看你们谁敢动!”乔老大:“不要胡说八道!再乱说我打你!”李占山连连点头:“明白了,你是在给你大哥拔闯呢。”李占山把脸一绷,厉声命令随从:“你们不是很会修理刺儿头吗?还不快给我好好修理修理,拔掉他身上的刺儿!”两个随从疯狗般扑向安文玺。安文玺哪里敌得过两个保镖护院级的人物,很快被打倒。
柳霞疯了般扑上前,却被乔老大一把抓住不能近前。两个随从拼命暴打安文玺。柳霞拼命哭喊叫骂。几个小孩吓得四处跑去喊大人。
安文玺腿上被狠踢了一脚,如骨裂般疼痛,忍无可忍,大声嚎叫。
“住手!”一条大汉贴近安文玺,左遮右拦,将那两人的拳脚挡开。
大汉:“手下留情,不要伤害人命。”随从:“哦,是杨润棠,杨师傅。你管这闲事干吗?”杨润棠:“这是闲事吗?我看你有些面熟,你不觉得这是为你好吗?要真出了人命,你可要吃官司。”随从:“吃不吃官司是我们的事,用得着你闲吃萝卜淡操心!”李占山不耐烦了:“啰嗦!你们两个还打不过一个吗?”两个随从一听,一齐上手攻击杨润棠。
杨润棠随即应战,但只是防守,尽量化解对方的狠招,想让对方知难而退。不想对方步步紧逼,一招比一招狠。杨润棠尽使破解之法,气运臂上,向外开挡对方的进攻。一个随从被杨润棠推得咚咚咚倒退数步,终未站住,石碑般倒仰下去,脑袋恰巧磕在一块石头的尖角上,也未见出多少血,蹬蹬腿就没了气。
李占山见出了人命,拔腿就跑,边跑边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杨润棠见死了一个,大惊失色,但他很快又从容起来,并没逃跑。
很快有官府衙役跑来,不容分说,把杨润棠押走。
安瑞章也跑来了,见儿子那样,心疼地大哭。
乡亲们把安文玺抬回家。乡医说,安文玺的腿骨被打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