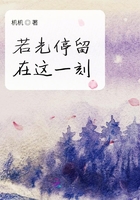为了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些鸦片商大亨不仅帮助巴麦尊制订计划和战略,而且提供必需的物质援助:把鸦片贸易船只租给舰队使用;鸦片贸易船只的船长给他们当领航员,而其他职员则充当翻译:自始至终给予殷勤的招待,并出谋划策和提供最新情报;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付陆海军的军费。
——(美)费正清
(鸦片战争)基本上是借助于你(斯密斯)和渣甸先生那么慷慨地提供帮助和情报,我们才能够就中国那边海陆军和外交各事发出那么详细的训令,从而获得如此满意的结果。——(英)巴麦尊
从1834年律劳卑事件发生,到1839年林则徐南下禁烟,中英两国之间的来往表面上改变不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只是偶尔突破与两广总督公文的直接往来,渣甸·马地臣行的鸦片生意依然在继续。然而,这期间,中英两国的政策走向实质上已发生根本改变。由于英国政府正式取代东印度公司与清政府打交道,官方关系代替此前的非官方关系,而且已不只是渣甸等广州英商对清政府持强硬态度,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与此同时,清政府在鸦片带来一系列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后,同样开始对禁烟持强硬态度。
其实,只要人们知道当时有多少鸦片流入了中国,又有多少白银流出了中国,中国朝野增加了多少“瘾君子”,就不难从道德风化与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看出禁烟之不可避免,禁烟之势在必行。
然而,禁烟却引发了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场为鸦片而进行的战争中,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还是战争的推进,渣甸和马地臣都表现“突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01
禁与弛:禁烟问题大辩论在中英双方争夺交往规则制订权的较量中,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显示,英国试图建立对华官方关系的努力,因律劳卑的莽撞行动遭到失败。然而,律劳卑失败的根源,则是英国的对华政策,即单方面改变规则,强烈要求官方公文直接往来及不得采用禀帖形式。
此后,德庇时和罗治臣两任首席商务监督均选择了“无为而治”。1836年12月,当年随律劳卑来华,资历尚浅的皇家海军舰长义律接替罗治臣,正式出任高级商务监督。
与律劳卑一样,海军出身的义律,也是苏格兰辉格党显贵。不过,出身名门的义律对鸦片并不感兴趣,对鸦片贸易也甚为厌恶。他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我的私人感情对于公众的、重要的问题无关紧要,那我可以说,没有人比我对于这种强行的(鸦片)贸易带来的耻辱和罪孽更为憎恶,我看不出它与海盗行为有何不同。作为一名官员,我在我的权力范围内,运用所有合法手段对其长期不予支持,并为此在过去数年内完全牺牲了我在所属社群中的个人舒适。”
不过,义律的公职责任其实一直在驱散这种“私人感情”,为在华售卖鸦片的英商护航,正如一位英商代言人所说:“义律上校承认自己并非这种药物(鸦片)的朋友,在原则上反对它,但他在如此重要的事务上并未让自己的个人情感干扰他的公共职责。”吴义雄:权力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历史研究,2007第1期。其实,我们从以后的发展中看到,在中英两国利益发生冲突时,义律还是以武力为后盾支持鸦片贸易的主张者和以战争解决鸦片贸易纠纷的行动者。
义律上台后,开始力图打破与清政府不相往来的僵局。
在没有得到巴麦尊指令的情况下,义律在1836年12月起草了致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禀帖,并在封面上用中文标明“禀”字,由浩官转交邓廷桢,从而打破了已维持了两年多的“沉默政策”。义律在禀帖中要求邓廷桢“给领红牌,准由内河进居省城”,并希望以此作为两国和睦关系的新开端。
邓廷桢收到义律的禀帖后,发现来禀“词意恭顺”,与数年前律劳卑不打招呼就擅闯广州有天壤之别;而且公文由行商转交、又用了“禀”字,邓廷桢自然喜不自胜。
1837年1月12日,邓廷桢向朝廷报告了义律的意愿,一个多月后,道光皇帝颁旨允准。
3月18日,义律从行商处获悉道光皇帝准许其入住广州后,当天即写信向巴麦尊报告。他激动地说:“一个外国君主派遣的担任公职的官员可以在这个帝国的城市居住,这在我们对华关系史上还是头一回。陛下政府可以信任,我将持续、谨慎且认真地推进这一事态。”Charles Elliot to Palmerston,March 18th,1837,FO17/20,p52.参见吴义雄:权力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月29日,义律领到了由粤海关核发的赴省红牌。4月12日,义律一行抵达广州。
义律由行商转交禀帖取得了作为外国官员常驻广州的历史性突破。然而,消息到达伦敦后,巴麦尊极为恼火,严斥其由行商居间传递公文,同时使用“禀”字的行为,并警告义律:国王派驻海外的官员,无权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擅自采取行动。
11月21日,义律收到巴麦尊的信后,只得遵从训令。29日,义律向在广州的英国人发布告示,告知他将中止与广东当局的官方往来。
不能与两广总督正常往来,又没有足够的海军展示武力,留在广州已毫无意义。3天后,义律扯下广州英国商馆上空的国旗返回澳门,结束了自4月以来与广东官方的关系。一年后的1838年12月,借助于共同打击鸦片走私问题,义律在广州原东印度公司商馆前再次升起英国国旗。
就在义律为打开广州之门而绞尽脑汁时,渣甸·马地臣行运送鸦片的船队一刻也没闲着,广州英商的鸦片贸易一刻也没停止。1834年之后,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在“妾身未明”的状态下,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被散商打破,并取而代之,鸦片走私在中国迅速扩展。
对清政府来说,直至1836年夏天,其官员也还在对鸦片走私是严禁还是弛禁而争论不休,政府也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禁烟对策。
1836年6月,两年前曾任广东按察史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皇帝上奏,提出弛禁主张。他指出,禁愈严而食者愈多,法愈峻官吏之贿赂愈丰,不如允许鸦片照药材纳税,鸦片进口“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既可增加税收,也可防止白银外流,夷商则因“纳税之费,轻于行贿”也会乐意接受。同时,开放栽种罂粟之禁,内地种植日增,夷人利润日减,就会慢慢达到“不禁而绝”。许乃济因这种弛禁观点而在后来付出了代价,被革官职,“以示惩儆”。
当月,许乃济的奏折发交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会同粤海关监督妥议具奏。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康、粤海关监督文祥奏复,赞同鸦片弛禁,准令鸦片交税进口的条陈,并提出了以货易货,鸦片贸易应限于广州一地等九条办法。
当北京朝廷接到这个奏折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相继奏请严禁鸦片,驳弛禁之议。其中,许球的奏折中列明渣甸、因义士(James lnnes)、颠地、打打皮等九大鸦片商人,并建议将其拘拿。
对于北京方面对鸦片禁与弛的讨论,广州外商通过行商及时知道了争论要点。
弛禁的前景促使广州外商加大鸦片进口,严禁的传闻又让他们满心忧虑。对此,渣甸的内心也是充满了矛盾:鸦片解禁,会引起印度方面的狂热投机和价格上涨;禁烟严厉,则会影响鸦片的销售。
道光皇帝在接到朱樽和许球的奏折后,责成广东方面重新妥善筹议。对于许球奏折中提到的拘拿不法商贩,两广总督邓廷桢变通办法,并没有捉拿渣甸等人,而是在11、12月连续发布将其驱逐出广州的谕令,但渣甸等人均以商务未完为由要求推延,最后不了了之。
清政府在禁烟问题上展开激烈辩论后,包括商人、传教士在内的广州外侨也在《中国丛报》上展开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
广东政府在朝廷严禁鸦片的督促下,1837年夏,邓廷桢展开了以清理伶仃洋鸦片走私基地为中心的禁烟行动,并获得成功。
渣甸和马地臣于是用武装船只运送鸦片,加大了在沿海一带的销售。然而,即使在沿海,禁烟的力度也加大了许多。一次,清朝的官船与运输鸦片的帆船发生交火,鸦片船上的一些人被击毙,同时船上的鸦片也被毁。
1838年,广州及沿海一带的禁烟措施时紧时松。欧洲武装走私船的使用,为当年夏季的鸦片贸易带来了短暂的繁荣。能够使用由精良武器装备的武装船只,也只有渣甸和颠地等大型商行才能办得到,因此鸦片价格又迅速上扬。马地臣在一封信中兴高采烈地写道:鸦片季节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至于“劄谕之类的装模作样的禁令,只不过被当做是一大堆废纸”。
随着伶仃洋鸦片基地受到重创,一些英国鸦片商随即将鸦片销售重点向广州内河转移。
但是到了9月,清政府的禁烟行动又一天紧似一天。尤其是在广东前线,11月以后,一连串的布告、命令、巡逻、搜查、处决的严打全面展开。
02
鸦片·白银·瘾君子其实,只要大致数一数当时有多少鸦片流入了中国,又有多少白银流出了中国,以及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出现了多少“瘾君子”,人们就不难想象鸦片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不难看出禁烟之势在必行。
在19世纪30年代,到底有多少鸦片流入了中国?
对于走私的鸦片来说,统计资料并不可靠。由于鸦片贸易的秘密性质,以及鸦片商贩间的商业竞争,数据无疑是不完整的。不过,从当时留下的记载中,依然可略见一斑。
就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特权刚取消的1833~1834贸易年度而言,马礼逊在其所著《中国商业指南》中说,该年度英国人和葡萄牙人输入中国的孟加拉国鸦片(公班土)分别为7 511箱和1 000箱,共计8 511箱;输入麻尔洼鸦片(白班土)10 1125箱和1 600箱,马地臣提及该年度英国人输入广州的麻尔洼鸦片为10 1025箱,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统计数据为10 103箱,均与马礼逊的记录相差无几。除了英国和葡萄牙人外,还有一些美国人、法国人等从事鸦片贸易,经他们之手贩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人们所知不多。共计11 7125箱。两者相加,这一年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2万箱。据历史学家统计,1835~1839年,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25万箱。
在19世纪30年代,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出了中国?
当时中国的白银外流,主要是流向印度,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对华鸦片贸易。据印度历史学家谭中统计,1829~1840年,中国流向印度的中国纹银为2 5548万元,外国银元为2 66188万元,黄金为36169万元,共计5 57839万西班牙元;平均每年为465万元,约合白银335万两。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前10年每年外流的白银为1 000万两,甚至有学者认为每年外流3 000万两,但这些说法可能偏高。
在19世纪30年代,到底中国又有多少“瘾君子”存在?
如果说在19世纪20年代,鸦片吸食者还多局限于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鸦片问题还多被清政府看做是一个社会风俗与道德伦理的问题,那么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吸食的人群与地域已经迅速扩大,鸦片已不只是一个关乎风俗与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
1838年,有官员在一份奏章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始而沿海地方沾染此习,今则素称淳朴之奉天、山西、陕、甘等省,吞食者在在皆然。凡各署胥吏、各营弁兵,沉溺其中十有八九。”
同年的另一份奏章则称:鸦片流入中国,近害耗民财,远害伤民命,可以说贻害无穷。“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
湖广总督林则徐在他那份著名的奏章中甚至认为:鸦片流毒于天下,长此以往,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粮”。
03
钦差南下与渣甸离华1838年冬,鸦片的烟雾笼罩着大清帝国朝野。全国的现实状况显示,不仅官宦士绅和富户人家对吸食鸦片大行其道,一般草民百姓也倾家荡产厕身其中,而八旗军队的官兵成为“瘾君子”者更是日渐增多。地方大员查获贩卖和吸食鸦片的奏章,从四面八方像雪片般传到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手中。
面对如此现状,道光皇帝终于下定决心,派主张严厉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展开禁烟行动。
林则徐南下广州,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相应对策的,尤其对渣甸等钦点的烟贩更是留意有加。道光皇帝让他带往广州查办的相关奏折中,渣甸被列为“奸猾之尤”;林则徐尚在京城时,便“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更断定“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人为祸首”。
然而,林则徐此次南来,并没有见到渣甸的踪影。就在1838年11月道光皇帝决定派林则徐南下广州的同时,身在广州多年的最著名鸦片商人渣甸正打算离开广州,返回伦敦。已经赚足了钱的渣甸,其实早在1837年便打算返回英国,两广总督曾在1836年11月23日下令,包括渣甸在内的9名外国大鸦片商必须在15天内离境;12月13日再次下令,限期延长4个月,展至1837年4月4日。在苏格兰买下大片土地,然后出任国会议员,翻开人生的另一页。
渣甸将公司交给马地臣经营,在一场广州外商参加的盛大告别宴会后离开了广州。
在热闹的欢送之后,渣甸写了封告别信给马地臣:“有关晚宴、演说、在大街上跳舞等等我就不说了,我的侄子大卫·渣甸会告诉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有一件事我谨向你保证:我绝对相信,洋行在你的带领之下,必如同我在时般蒸蒸日上。你只需对自己有信心,相信你自己的能力绝不在我之下,甚至超乎我。你会需要一些时间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在未达到这个目标前,我对你的经营手腕信心十足,对于把洋行交到你手里也很放心。”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90页。
渣甸是1月26日从澳门启程正式离开中国的。渣甸返回伦敦,也同样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相应对策,他尤其知道北京派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意味着什么。
04
禁烟风暴与马地臣缴烟“鸦片这种买卖是在广州的外国人最易做,也最惬意做的。卖出是愉快的,收款是平和的。这项交易似乎也具有了这种麻醉品的特性,一切都是愉快舒适的。卖出的手续费是3%,赢利的手续费是1%,没有坏账。代理商每箱可赚20英镑,年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