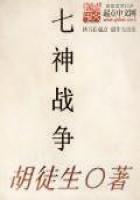小毛贼灰溜溜地缩回了墙角。
林子豪一夜没睡好,躺在地铺上看着铁窗外那黑沉沉的天空发呆。留置室的地面是一整块的地板,沿墙铺着一些干稻草,睡在上面浑身发痒,好在睡了这么多天,林子豪已经有点习惯了。唯一难以忍受的是,身边的嫌犯很多都是流浪汉和小瘪三,身上都带着臭虫、跳蚤,咬得人简直坐立不安。
第两天,天空刚有些发亮,林子豪便早早地起了身。
好不容易熬到八点,铁门一阵乱响,那位华捕带着一个瘦叽叽的外勤出现在“留置室”。
按规矩,送审途中必须戴手铐,但那位苏北口音华捕只是将手铐拎在手上,二人一前一后将林子豪夹在中间,顺着走廊弯七弯八地朝外走。
穿过一间办公大厅,出门就是大街,那辆黑乎乎的棺材车已经等候在门口。
林子豪突然发现,距离十几步路远的前方,果然停着一辆小轿车,排气管里冒着烟,显然一直没熄火。再一细看,车窗里是一张熟悉的脸:傅连生。
华捕突然轻轻一声咳嗽,林子豪顿时反应过来,伸出双手将一前一后两位巡捕同时一推,朝着小汽车的方向拔腿便跑。两位巡捕如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一样优美地摔倒在地,爬起身来,并不追赶,而是拼命吹响了手中的哨子,好像这么使劲吹吹,就能把嫌犯吹回来似的。
林子豪钻进小汽车,一阵浓烟升起,车头猛地起步。
“真简单啊。”林子豪回头望望远去的巡捕房。
“呵呵,你这一推是很简单,但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才让他们两个跌到的?”傅连生笑道。“跌一跌,整整五百大洋呢。”
“这么多?”林子豪有点吃惊。
“从里面的内勤到开车的司机,人人都得有份,”傅连生说道,“所以关了这么多天,没填解案单、没按手印。”
“那今天突然少了个人,他们怎么交差呢?”林子豪问。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啦,人家自有办法,”傅连生道,“肯定是写份报告,说你是马路上偷钱包的小偷,案值不高,惩戒释放。”
“瞧这世道,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林子豪叹道。
车轮飞滚,不多时回到克能海路二十一号,远远地便能见到紫玉正在石库门的台阶前焦急等候,心头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暖流。
“有没有挨打啊?”一下车,紫玉马上奔过来拉住林子豪的胳膊,有点像要哭出来了。
“挨什么打啊,他不打人家已经不错啦,”傅连生嘴里打着哈哈,转脸对林子豪说,“你这位未婚妻啊,成天催得我头疼。我跟她说,急不得,得慢慢打点,可她哪里肯听,还是每天十二道金牌照催不误。”
“林老弟,辛苦了,辛苦了。”范君谊一路高叫着亲自出门迎接,胳膊上挂着香气袭人的小桃红。
“哪里,给舵爷添麻烦了,还破费了那么多钱。”林子豪抱拳客套道。“惭愧,事情也没办好。”
“这个不怪你,那把火,还是烧得非常漂亮的。”范君谊安慰道。
“林兄,手上的伤口没事吧?”双眼皮雪根亲热地迎上前来,又转脸对众人说,“那天晚上要不是林兄出手相救,我这条小命,早报销了。”
“被关起来的几天里,没受什么委屈吧?”小桃红关切地问。
“没,谢谢九姨太。”林子豪恭敬地答道。
“那天要不是你最后点着那把火,咱们山堂那才叫面子丢尽呢。”范君谊叹道。“烧得好,烧得好。”
“不过,我那天被他们认出来了。”林子豪道。
“那怎么办啊?!”紫玉马上吓坏了。
“不要怕,有我们山堂在,怕什么呢?”范君谊的目光在紫玉的脸上来回扫了两遍。
“山堂又不可能每日每夜都陪着我们。”紫玉咕哝道。
“那就你们每日每夜陪着山堂,如何?”范君谊嬉笑着接过话头。
“是啊,林老弟,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傅连生说。
“怎么个说法?”林子豪还不大明白。
“正式归标入会啊。”傅连生道。
“巧了,再过几天就是农历五月十三单刀会[ 纪念武圣关公过江去东吴赴会的英雄事迹。],”范君谊说道,“我为你开香堂,特准你翻山越岭、上山插柳[ 黑话,直接提升叫“翻山越岭”;从最末级的“小老幺”跳级提升叫“上山插柳”。],你看怎么样?”
“呵呵,你看舵爷对你多器重啊。”傅连生道。
“林老弟若愿归标,”范君谊看林子豪有点动心,连忙加重筹码,“山堂封赠你五排中的‘青刚’[ 哥老会“外八堂”第五排中的职位,与红旗、黑旗、蓝旗、执法同级。]之位。”
“哈哈,都跟我平起平坐啦,林老弟。”傅连生大笑道。
林子豪虽然听不大懂,但破格提拔的意思还是领会了,想想自己现在已如上海人所说的“赤脚地皮光”,而且害得方家父女无家可归,更严峻的现实是,那帮袍哥以后还会放过自己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庇护,不要说开店做生意,恐怕连性命都难保。自己倒也罢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带累了紫玉,怎么说得过去呢?
晚上,跟方家父女商量了许久,衡量来衡量去,觉得还是入了会要稍微太平些,至少目前不会有性命之虞,待以后情况缓和一点后,看形势再作理会。紫玉说,入会就入会吧,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有一点,不许做坏事。
林子豪想,是啊,行走在上海滩上,入帮入会,几乎是早晚必须迈越的一道门槛,但人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把握好自己,一定能与一般的流氓恶棍划清界线。看看“家法”所要求的——“第一父母要尽孝,尊敬长上第二条,第三莫以大欺小,兄宽弟忍第四条,第五乡邻要和好,敬让谦恭第六条,第七常把忠诚抱,行仁尚义第八条,第九上下宜分晓,谨言慎行第十条。此外还有三大要,一个色字便包含,若逢弟媳和兄嫂,俯首潜心莫乱瞧。一见妇女休调笑,犹如姊妹是同胞。寡妇尼姑最紧要,宣淫好色要捱刀”——就凭这“十条三要”,如果严格做到的话,又与关圣何异?
不多几日,便是五月十三单刀会了,一大清早,大小头目纷纷齐聚山堂,忙忙碌碌为开香堂做准备。林子豪发现,今天出现的陌生面孔中,好些人看上去都是极为普通的商人、职员、小官吏,甚至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像是在校学生。按规矩,今天开的是小香堂,有资格参加的人在帮内至少都有一官半职,全部人马加起来怕也有一二百人之多;若是开大香堂,各路喽啰全部到场的话,那还了得!
哥老会发源于川、湘一带,但现在于上海滩上早已出落得枝繁叶茂,与青红二帮几成鼎足之势,主要原因就是放低门槛,兼收并蓄。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严格按老规矩办,又有几个人是合乎要求的呢?单拿一条“身家清”来说,就能将许多人拦在门外。剃头匠和裁缝师傅就不说了,谁让他们的前辈曾经为虎作伥为清王朝效力,强迫汉人剃发或缝制象征奴才身份的马蹄袖短褂,连看门的、修脚的、唱戏的、吃公事饭的、偷盗扒窃的……如此等等都算下九流“贱人”。林子豪想,自己倒是相当硬朗的“身家清、己事明”,上查三代都不带半个“红疤黑迹”。
山堂布置得森严而神秘,堂前供“五祖牌”,祀“关帝像”,案前还摆着算盘、尺、秤、镜、桃枝、木鱼等物,林子豪请教了一下傅连生,这才知道这些器物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秤是用来表示哥老会的公正无私、镜子是拿来照一个人的善恶邪正、尺子用来衡量行端、桃枝用来纪念桃园三结义……
今天同时入帮的还有七八个年轻人,范君谊衣着一新,摇摇摆摆走入大厅。按老规矩,开香堂程序繁多,礼仪复杂,但现在大部分已经简化了。范君谊升座之后,由红旗管事司仪,一齐向祖圣行拐子礼,说许多赞词,也即以唱诗的形式传承本会的历史、宗旨和规矩,随后焚香、上祭、盟誓。
红旗老五,也就是傅连生一声令下,堂前闪出两排“小队子”,亮出手中的刀剑架起了一座“剑桥”,林子豪带头,其余几位年轻人尾随,一一从“剑桥”下方弯腰钻过。
“矮起!”傅连生高喊道。“歃血为盟!”
傅连生已经提前为林子豪扫过盲,这“矮起”就是跪下,“歃血为盟”是用香案上的银针刺破中指,滴入酒碗中共饮。林子豪与新人们一一照办,最后,由范君谊亲手“放布”——发给一份“腰凭”,一方票布上书写着本人姓名和山堂水香的名号——从此,持有人便正式成为帮会中的一员,除生老病死之外,不得脱离和背叛。
作为一名“新福大爷”,林子豪现在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哥老会的规矩和礼节极多,有个说法叫:“矮子心多,哥老会规矩多”,在短时间内将隐语、手势、茶阵等背得滚瓜烂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咽下口中带着血腥气的烈酒,林子豪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悲凉,也许,从今往后,得跟原来那个美丽的梦想彻底告别了: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老板,与紫玉日日厮守,生养一堆小儿女……
“礼毕!”傅连生又是一声高叫。
郑青阳和陈宝火结交的两位新朋友果然不是中国人。
矮个子是日本人,名叫木村金井,在虹口地界上开设一家“东华贸易社”;高个子是高丽人,名字跟中国人差不多,叫崔永吉,是日本老板的跟班。
陈宝火暗底里告诉郑青阳,这两个家伙,其实就是最近报纸上经常提到的“虹口浪人”——当然,现在浪人的涵义已经非常宽泛,已不再局限于“流浪武士”的概念,凡是在国内混不下去而冒险到海外碰运气的人,都可被视同浪人,其中,还包括不少混水摸鱼的高丽人和台湾人。
郑青阳想,将这两个狗娘养的叫作“浪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一是不务正业、吊儿浪荡;二是不爱女色喜男风,浪得别出心裁、奇形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