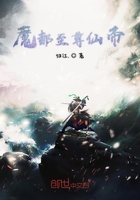‘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忽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以奇杰。
哪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赢,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话说吴奇等人出城以后,一路往南,晓行夜宿,却也平安无事。随行几位公人见已出了扬州地界,已非是漕帮势力范围,便告辞回去向柳媚儿复命。方吴二人继续前行,闲时便将鞭中所藏‘燕双飞’鞭法取出研究习练。二人情投意合,此时又无旁人打扰,两个青春少年,自是日渐情浓,心意相通,这双鞭合击之术,已是初窥门径。吴奇初出门时尚且时时想起柳媚儿之事,总觉得对方柳二女都是心中有愧,不免闷闷不乐。方倚云只当是情郎初次离家,思念父母所致,总是百般体贴,软语温存。直到二人走到池州地界,吴奇这才放下心事,渐渐开朗起来。
这一日二人一路走来,看看前边已是池州城门,此时天已向晚,腹中饥渴。二人便紧催座马,进城来寻客店打尖。进得城门不远,就见街边有一家客栈,迎门金字招牌,上书‘双鱼客栈’。门旁挂了一副对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唯大英雄能本色;一掷千金,一挥万字,是真名士自风流。’店门前一个伙计肩上搭了一条雪白的毛巾,正在招呼客人。这吴奇也是饱读诗书,不脱文人本性,加上年轻好奇,见这店名取得奇怪,忍不住催马上前,想要问个究竟。那店小二见来了客人,忙上前招呼。方吴二人此时已经恢复平民打扮,只是方倚云扮成了一个假小子而已。两人一个潇洒,一个俊秀,显得气度不凡。店小二不敢怠慢,上前打拱作揖,将二人让进店内。
二人进得店门,找张桌子坐下,抬头打量。却见店面不大,收拾得却是极为干净。正面廊柱上一副对联:‘常迎天下客;难得故人来’。这时那店小二沏了一壶香茶,放到二人面前,含笑说道:“二位爷是吃饭还是住店呢?”吴奇答道:“你先去给我们准备几个精致小菜,一壶好酒,然后收拾两间干净客房,我们吃过饭要早点歇息,明早还要赶路。”那店伙答应一声自去准备。
不一会酒菜上齐,店小二道声慢用,便转身欲走。吴奇连忙叫住,问道:“小二哥,在下有件事觉得奇怪,不知道能不能问一下究竟。”
小二忙点头陪笑道:“客官不必客气,有话但问无妨。”
吴奇笑道:“倒也无甚大事,只是适才我进店之时,见你店名取得奇怪,故此动问。敢问这店名是何人所取?有何寓意?”
店小二笑道:“这店名就是我们老板所取,至于其中有什么意思,小人没读过几天书,这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家老板性喜交游,一会他出来时客官不妨亲自问他。”说完去了。
吴奇见问不出什么,只好回头坐下,招呼方倚云用饭。两人一边吃酒,一边不时低声细语,那方倚云不时低头浅笑,二人甚是相得。正在此时,忽听门前脚步声响,一个闷雷般的声音叫道:“小二,快给道爷上酒上菜,他娘的,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方倚云一听,不禁峨眉微皱,抬头看时,却见门口一前一后,走进两个出家的道士。当先一人身材魁梧,一脸虬髯,背后背了一口又宽又长的奇形长剑,走起路来咚咚作响;后边一人却是瘦如竹竿,面色苍白,背插双刀,手持拂尘,步履轻盈。方吴二人都是行家,一望而知这两人都是武学高手,不欲惹事,仍是低头吃饭,只以眼角余光注意二人动静。
只见二道落坐之后,那魁梧道人不住声地催促上酒,那瘦长道士似是有些心烦,细声细气地说道:“我说老二,你能不能安静一会,不怕别人笑话吗?”说话间眼角不住向方柳二人腰间扫视。
那魁梧道人显得颇为不服,却又似是对瘦长道士甚是忌殚,坐在桌前不再作声。不一会伙计把酒菜端上,二人喝酒吃肉,略无忌讳。只是二人不时扫视方吴二人一眼,神态暧昧。
吴奇二人心知有异,暗中戒备。两人草草吃完,便欲起身回房。突听那瘦长道人尖声说道:“两位小兄弟且慢走,贫道有事请教。”
吴奇见走不脱,只好回头拱手道:“不敢,前辈有话尽管问便是。”
道人笑道:“小兄弟客气,请问二位可是一位姓吴,一位姓方?可是自扬州而来?”
吴奇心中一惊,面漏警惕之色。
那道人又笑道:“小兄弟莫慌,贫道并无恶意。”
吴奇答道:“晚辈正是从扬州而来,不知两位前辈有何赐教?”
道士面色一寒:“赐教不敢,只是贫道受人所托,来问二位讨还一件物事而已。只是不知道小兄弟肯不肯卖这个面子。”
吴奇心中恼怒:‘这话说笑了,晚辈与二位素昧平生,何来欠物之说?前辈若无他事,晚辈告辞。”说完回身欲走。
这时那魁梧道人起身站起,张开蒲团般的大手,向着吴奇肩头便抓,口中说道:“小子不识抬举,道爷摔死你。”
吴奇早有防备,肩头一沉,右手食中二指竖起,径点对手曲池穴。那道人忙沉肩缩手,吴奇旋身回头,左掌斩向对方咽喉。那道人却也身手矫健,急忙后退一步,让开来掌。
吴奇并不追击,收势而立,注目二道问道:“两位前辈究竟何人,为何如此为难晚辈?”
魁梧道人面色发红,尚欲作势上前,那瘦道人抬手止住,挥挥手中拂尘,笑道:‘小兄弟好身手,怪不得我师妹伤在你手上。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二人便是眉山快刀鲍月清、重剑仇月明,那扬州梅月红正是我们师妹。今日受小师妹所托,来问二位取回龙凤鞭。二位若肯相让,咱二人回头便走,以前恩怨一笔勾销。若是不肯,那就莫怪我们以大欺小,得罪二位了。”
吴奇与方倚云对视一眼,心中恍然大悟。
方倚云怒道:“这姓梅的好不要脸,别人的东西,看上了便要,要不到便抢,抢不到还要找了帮手再抢。这龙凤鞭是在我们手上,不过你们想要,却是决无可能。要想硬抢,就要看二位的本事了。”
鲍月清尖声大笑:“小丫头牙尖嘴利,看来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一下,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说完将手中拂尘往桌上一放,反手将双刀拔在手中,便待出手。
突听店面后门处有人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一个矮胖书生,手提一支巨大的秃笔,浑身墨迹淋漓,从后门走了进来。
只见他摇摇晃晃,走到四人中间站定,口中不紧不慢地说道:“看几位拔刀弄剑,可是要打架吗?须知古人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又云;‘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却不知几位有何不得已之处?小可不才,倒愿意替几位从中调停,不知几位意下如何?”
那仇月明性情暴躁,大声道:“酸秀才,这里不是你插话的地方,你赶紧滚到一边去,莫要惹道爷发火。”
那书生并不生气,只管摇头晃脑道:“道爷此言差矣,其一,小可昨天刚洗过澡,不酸;其二,小可未经乡试,不是秀才;其三,这家客栈正是小可所开,几位要在此处打架,岂有不容小可插话之理?其四,道爷身为出家之人,却出口伤人,让小可滚到一边去,有违教规,有伤天和……”话未说完,那边方倚云已经笑出声来,吴奇也不禁莞尔。
那仇月清暴跳如雷,起脚便踢,只见那书生手舞足蹈,向后跌来,手中秃笔连挥,在那仇月清脚踝处抹了浓浓一道墨迹。吴奇见书生凌空跌倒,恐其受伤,忙一纵身将其接住,放在地上。那书生兀自口中哇哇大叫,似是伤得不轻。
却见他并不罢休,摇摇晃晃,又向鲍月清走去,口中大叫大嚷:“这位道爷且来评评理,小可好心劝架,你这同伴却出手伤人,这还有王法吗?”
鲍月清也是心中不耐,刀交左手,右手劈胸抓住书生衣襟,便要扔出,那书生极力挣扎,手中秃笔无巧不巧,又在鲍月清手腕上抹了一笔。鲍月清心中气闷,把那书生提起,往外便扔。再不迟疑,双刀一分,便向吴奇扑来。那仇月明也大喝一声,拔出巨剑,扑向方倚云。二人不敢怠慢,各自在腰间一扣,龙凤双鞭出手,四人斗作一团。
四人甫一交手,方吴二人便知道遇上了真正强敌。这鲍、仇二人武功之高,却与那梅月红不可同日而语。那鲍月清双刀使开,直如风车一般。双刀互为攻守,左拒则右进,左出则右守,变幻无方,难以捉摸,快如闪电。而仇月明则是双手握剑,横扫直劈,长剑带风,呜呜作响,似拙实巧,似慢实快。加上房中空间狭小,吴奇二人长鞭却是难以尽展精妙。交手不多时,二人便连连遇险。吴奇鞭中夹杂拳脚,尚能强自支撑,那方椅云却是左支右绌,渐觉不支。好在仗着身法灵活,不住在桌椅板凳缝隙间游走闪避。那仇月明追得心烦,突然大喝一声,剑劈脚踹,屋中桌椅顿时遭殃,转眼间变为一地碎木。方倚云此时无可倚仗,顿时陷入险境。吴奇见情侣遇险,心中发慌,招式愈乱。那鲍月清口中唿哨,向仇月明使个眼色,二人招式加紧,将二人慢慢向屋子中央逼去。方吴二人越靠越近,长鞭不时碰撞,愈来愈难抵挡。鲍仇二人心中得意,攻势愈急。正在危急之时,突见刚才被鲍月清扔出店门的店主人居然又摇晃着走了进来。口中不停念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话音未落,只见仇月明突然脚下一个踉跄,差一点儿跌倒。长剑擦着方倚云肩头斜削而下,在青砖地面上入地盈尺。方倚云眼疾手快,手一抖,鞭作枪使,抖得笔直,刺向对方咽喉。仇月明侧身急躲,鞭梢尖刺在腮帮上哧地划过,登时血流满面。百忙中撒手丢剑,单脚点地,纵身后退。方倚云毫不迟疑,回身一鞭,便向鲍月清抽来。适逢吴奇也是挥鞭扫向鲍月清脚踝,鲍月清右手刀横拍,左手刀下撩,来挡双鞭。鞭刀相交,鲍月清突然右手剧痛,拿捏不住,钢刀脱手而飞。吴奇手腕一带,身子一侧,长鞭抡起,自上而下,直击顶门,方倚云却是旋身送臂,长鞭径点小腹。鲍月清躲避不及,双鞭一中肩头,一中大腿。鲍月清大叫一声,向后急退。吴奇刚要追击,却见鲍仇二人唿哨一声,兵器也不要了,纵身出店,顷刻之间不见踪影。
吴奇二人一番苦战,侥幸脱险,暗叫万幸。只是二人却不明白刚才为何敌人在占尽上风之时突然落败。二人百思不得其解,知道此地已不能久留,便叫店伙结帐,准备连夜离开。连叫几声,才见那店主人换了一件干净长衫走了出来。却见他此时已不见方才穷酸轻狂之相,举止间仪态从容,竟显出几分儒雅之气。吴奇二人虽是初出江湖,此时也隐约明白眼前之人并非寻常之辈。连忙上前拱手施礼:“店家请了,适才在下莽撞,打碎了贵店许多东西,还请原谅。店家只管一一结算,在下定当照价赔偿。”店家却是毕恭毕敬,躬身施礼:“不敢,钱财小事,二位且不忙结账,请随小可到后房奉茶,小可尚有要事请教。”二人心中犹疑,并不动脚。
店家笑道:“二位但请放心,那二人中了小可墨汁之毒,虽说不至丧命,但短期内想要动刀动枪,却已决不可能。小可对二位也绝无加害之意,否则也不会相助了。二位请!”二人这才心中恍然大悟,连忙道谢。再也不好推托,只好跟了此人向后房走去,只是暗提内力,手按腰间,全神戒备。
那人看在眼里,并不说破,只管将二人引入后院一间小书房内。只见房中四壁挂满了狂草书法,似是出自一人之手,字意落拓,狂放不羁,直有一种大气磅礴,意透纸外之感。屋中央一张绝大的书桌上书堆中间,尚有一张宣纸,墨迹尚新,似是刚写不多时:‘男儿何不带吴钩,收拾关山五十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那吴奇也是读书之人,见此情景,顿生好感,心中警惕已是放下大半。那人将二人让进房来,回头将房门关上,突然对着二人倒身下拜,口称少主。
吴奇吓了一跳,连忙俯身相扶,连称不敢,口中说道:“先生这是从何说起?这可折煞在下了.”只见那人站起身来,仍是毕恭毕敬,将二人让到椅子上坐下,自己垂手立在一边,躬身说道:“少主二人初登尊位,会中尚未来得及准备,少主便惹上祸事,离家远行,是以直到今日,会中喜讯早已传遍天下,众兄弟人尽皆知,却只有少主二人蒙在鼓里。属下知道少主心中疑惑,请少主只管垂询,属下自当知无不言。”
二人只觉莫名其妙,心中郁闷已极。
吴奇起身拉那人坐下,开口问道:“先生何人?为何口口声声称在下为少主?”
那人恭恭敬敬地答道:“属下姓佟,名子鱼,祖籍河南,现任藏龙会池州分会会主一职。请问少主可是从扬州一家兵器店中将龙凤双鞭买得?”吴奇点头称是。
佟子鱼又道:“那间兵器店,便是本会设在扬州的分会会馆,店主杨飞,便是本会扬州分会会主。那日少主一行前去游玩之前,其实会中长老早已留意少主多时。也是天从人愿,少主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且一眼便看中了这对龙凤双鞭,岂非天意!少主却是不知,这鞭乃是前任总会主之物,代代相传,只有总会主夫妇方能持有此鞭,兼修鞭中所载武功。若非本会早已属意于少主,慢说此物根本不会让少主看见,就是见着了,也绝不可能卖给少主。如今少主既已持有此鞭,且已开始修习其中武功,属下等称一声少主,那是理所当然之事。”
吴奇啼笑皆非,心中微怒,沉住了气问道:“但不知贵会所谋何事?为何江湖中从未传闻?在下只听家父谈起过燕双飞前辈之事,却从不知藏龙会为何物。况且这选取会主,应是十分重要之事,最要紧还要你情我愿,岂可如此儿戏?”
佟子鱼微笑道:“这些均是帮中机密,少主当真要听吗?”
吴奇负气道:“先生愿讲便讲,若有不便,吴奇正要告辞。”
佟子鱼急忙起身拱手:“少主且莫生气,属下讲来便是。我们这藏龙会起自明初,当年鄱阳湖一战,陈王败北,只留下一个幼子,名叫陈镇乾。手下几位忠心臣子保护其隐姓埋名,流落民间,只盼有朝一日能重招旧部,东山再起。当时幼主身边别无他物,只有当初陈王所赐这一对龙凤鞭和一套武功心法。幼主天赋极高,聪明能干,二十岁上已经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加上几位心腹旧将扶持,暗中联合旧部,成立了如今这藏龙会。只是此时朱元璋早已坐稳龙廷,江山稳固,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幼主便以所学鞭法为名,自号燕双飞,携妻行走江湖,行侠仗义,寻找机会。而这藏龙会之名,却是绝不敢露。是以江湖中只知燕双飞,不知有藏龙会。谁知这一去便是三十年,直到年华老大,也是毫无时机可寻,这朱家的江山倒是越坐越稳。幼主心灰意冷,于十五年前突然留下双鞭,留书出走,至今无影无踪。因幼主无后,留书中又有交代,故此才有以鞭寻主一说。只是老会主所订继任者条件极为剋刻,以致会中十几年群龙无首,全仗几位长老勉力支撑。如今几位长老已经渐渐老迈,看看不能理事,会中各地年轻会众蠢蠢欲动,眼看局面将要不可收拾,谁知天可怜见,终于让我等寻到少主来主持大局,这可真是我藏龙会之幸!”
吴奇二人越听越惊,面面相觑。要知道明代刑法极为残酷,什么剥皮剜眼,抄家灭门,都是常事。这密谋造反之事岂是儿戏?况且当时锦衣卫眼线广布天下,如有风吹草动,稍有不慎,便是灭门惨祸。想到此处,吴奇起身说道:“先生言重了,在下无才无徳,难以当此大任,况且家有父母在堂,这反抗朝廷之事,在下岂能做得?至于龙凤鞭之事,更是无稽之谈,先生这玩笑开得大了。在下还要赶路,先生若无他事,这就告辞!”说着一拉方倚云,回身便走。
忽听门外一个苍老老的声音响起:“少主且请留步!听老朽一言!”
门开处,一位白发老人手拄铁拐,昂然走了进来。
佟子鱼抢上一步,扶住老者,口中说道:“爷爷,你老人家怎么来了?”老人手臂一抖,将佟子鱼推开,笑道:“小兔崽子,少献殷勤,爷爷再不来,你就要把少主气走了!”说着走到吴奇面前施礼:“属下佟玉,见过少主。”
吴奇连忙还礼:“吴奇后生小辈,不敢当老先生如此大礼。老先生唤我吴奇便可。”
老者笑道:“少主不必客套,老朽虽然年纪老迈,终是下属,岂敢如此无礼!少主请坐。”吴奇无奈,只得再次坐下。
老者也在吴奇对面坐下,掂须笑道:“不知少主为何不肯接掌会主之位?要知道藏龙会虽在江湖中籍籍无名,暗中势力却是遍布中原,长江南北,黄河两岸,到处都有本会会众。少主如果接手,不要说一个小小的扬州漕帮,便是当今朝廷,也有分庭抗礼之力。又何必如此背井离乡,江湖逃亡呢?况且大丈夫生于世上,正当建功立业,横行天下。否则空有一身本领,却与天下碌碌之辈同朽,平淡终生,又与草木何异?还请少主三思!再者本会门徒遍及天下,会中机密已为二位所知,少主若是不肯入会,必将置万千会众于险地。”说着面孔一寒:“今日二位别无选择,若不肯入会,莫想生离此地!”说完手掌轻拍,就见四面窗口打开,一支支利箭正对着两人。
吴奇勃然大怒,站起:“老先生将我吴奇看作何人?吴奇虽然流落江湖,却也不想仰仗贵会庇护。虽有一身武功,却只愿扶弱济贫,仗义行侠。至于拜将封侯,争霸天下,却非我所愿。方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有何不足之处?若是刀兵一起,势必生灵涂炭,老先生为一己之私,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居心何在?今日吴奇纵死不能从命,老先生若要动手,悉听尊便!”说完抽鞭在手,直视佟氏祖孙。
只见佟玉愕然良久,突然哈哈大笑,手一挥,四面弓箭手应声退下。
吴奇心中莫名其妙,收鞭问道:“老先生这是何意?”
佟玉笑着请吴奇坐下,老脸上满是得意之色:“老夫没有看错,吴公子果然是人中龙凤,侠骨柔情,处市井而怀天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看来这藏龙会主之位,是非吴公子莫属了。”
吴奇怫然不悦。
佟玉这才庄容说道:“吴公子且莫误会,刚才老朽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其实藏龙会建会初期,确实是抱有争雄天下的宗旨,只是后来岁月更迭,朱家的江山越坐越稳,会中的老人又都渐渐去世,年轻人却都未经历过元末的那些战争,自然不会对朝廷有多大仇恨。时日一久,就连会主也对复国一事失去了兴趣。终于有一天会主留书出走,携了夫人隐居山林,享清福去了。留下喏大一个藏龙会,如一个烫手山芋一般,交到我们几个老不死手上。这十几年来,我们仅存的几个老兄弟分散各地,一边极力约束会众,一边寻找新任会主人选。当初寻机复国的初衷,也早已泯灭无遗。只想借着这一股庞大的势力抑恶扬善,扶助黎民。然而象藏龙会如此庞大的一股势力,其中也难免良莠不齐,暗藏了许多包藏祸心之人,总想借帮会的势力,达成自己的野心。若是所托非人,后果难以预料。方才这鲍月清、仇月明二人,加上那位梅月红,都曾是藏龙会众。只因这三人生性恶劣,野心勃勃,才被逐出会去。这几年这三人一直在寻觅这双鞭踪迹,图谋不轨。所以方才老朽才以言语相探,吴公子雅量高致,且莫放在心上。这十几年来,一者人选难觅,二者我这几个老兄弟又各怀了那么一点点私心,所以迁延十几年,未得其人。直到七年前,山东柳轻侯在河北万县方家庄一战,震动武林,会中之人沿途暗护令尊与方柳两家遗孤回到扬州,这才注意到吴公子。经过我会中几位老人几年观察,终于认定公子就是本会会主人选。所以才指派扬州分会杨飞想办法将本会信物龙凤鞭交到公子手上。好让公子与方姑娘早日练成老会主遗留武功,出来主持大局,免得老朽等归天之后,帮会落入奸人之手,岂不误尽苍生!所以若是吴公子真的心怀万民,这会主一位,还是接了的好。”
吴奇二人这才心中恍然,只是心中越发忐忑不安。沉思片刻之后,吴奇起身说道:“贵会对吴奇如此厚爱,本不应推托。只是晚辈初出江湖,年轻识浅,难以当此大任。况且贵会究竟是否真如老先生所说,晚辈也不尽了然,故而……”
不等吴奇说完,那佟玉站起说道:“这一点公子且放宽心,老朽并非蛮横无理之人,要公子今日便作出答复,自是为难。好在吴公子本就要游走江湖,这样吧,老朽就替公子作主,让我这孙子跟二位一起,路上也好有个照应。顺便让他带二位巡视一下各处分会,也好让公子了解一下本会的底细。至于何时接任会主一职,等二位回扬州时再说。公子你看如何?”说完不等吴奇表态,回头对佟子鱼说道:“孙儿,这次陪伴吴公子与方姑娘游历江湖,一路上要小心谨慎,不得有半点差错,对吴公子要事之以会主之礼,不可怠慢。到各地分会巡视之时,不要声张,务必让吴公子见到各处分会的真面目,以便将来接位之后,相机行事。你明白了吗?”说完对吴奇施礼道:“老朽年纪老迈,精力不济,吴公子若无他事,老朽这就告辞回房休息了。”说完回头出门,扬长而去。吴奇啼笑皆非,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