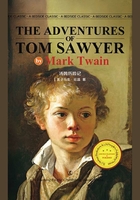春天的心太广大了
我再也探索不到
春天的心
是在海上依着朝阳呢
还是在山中逐着山洪……
现在,为这许许多多的
崭新的景象所惊奇
为这许许多多的
不曾经验过的感情所冲激
我感到了
十九年来
我等待的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这样的一天
是的,从来
我不曾看到
也不曾听见
这样响亮的
第一次的雷鸣
没有一个春天
我看大地看得这样贪婪
没有一次
春天的歌声
能这样紧紧地擒住我
我相信
就在这里
——这烟花灿烂的江南呵
这样的春天
也是少有的
在今天
有血
有笑声
有青春的梦
有太阳
有黑眼珠的少女
有群队的歌
有半夜烧起的火炬
有大红花和锦旗
有红星
有爱
有不眠的夜
有捷报
有大地的诱惑
而
没有
——等待与空虚
这一切
都好像在从前看过
却又和从前有多大的不同啊
于是
在我心中
爆发出了
压抑不住的歌声
我发誓:我要战斗下去
我已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的胸中塞满了自己的誓言
那誓言,简单,决绝:
“离开了战斗,
我的生命就等于零!”
即使将来
这大地被泛滥的血液所淹没
即使野火再度把她烧焦
风暴再度吹去草野的芬芳
即使冬日的冰雪
再度麻痹了大地的生机
即使那样
——那只是暂时
即使那样
春天还是要回来的
六
只有今天
我们才这样亲切地感到大地
才能这样亲切地感到春天
这是我们的大地呵
我们的大地
是雄伟、壮丽
自然写就的一首诗篇
洗涤了屈辱和灾难
她和天国那样相似
春天是我们的
春天是我们的
春天
是我们的
——你没有听到那战士所唱的歌吗?
那捍卫祖国大地的战士
他属于春天的队伍
在我的心里有着他
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他
他和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个战士相像
那队伍里的每一个战士像他
有热烈的青春的火
有无比顽强的战斗意志
他们的梦
用星星写在天上
温暖,璀璨,光明!
他们不曾为诅咒而退却
嘲骂也不曾使他们停止前进
他们不曾——也不愿这样
他们是纯洁的
他们只顾一心向前
“我只爱战斗!”
他们这样说——好像久已想好了一样
多大的骚动呵
多大的叫声呵
是有多少人拥抱他们呵
是有多少人害怕他们呵
一个奇怪的队伍呵
这样年轻又这样沉着
这样幼小又这样刚强
好心的人们看着他们
眼光充满忧虑
他们会胜利吗?
他们能生存吗?
——一个多大的奇迹啊!
战争
显示我们的力量
战争
决定我们的命运
铁和火
使我们壮大
鲜血和热泪
死,和坚固的信念
鄙夷
帝国精锐的炮弹
回答
存心不良的懦怯者的
无耻和顽固
千百次地击退了侵略军
在怒水汹涌的江边
在泥途泞滑的田问
在街巷
在堤岸
在僻静的渡口
在公路和铁路的交叉点
在河港湖泊密布的水乡
埋伏与穷追
包围和截击
战士
人民
天皇的叛逆
——一家人
日夜积累着
胜利的果实
向
所有受难的城市
村庄
进军!
攻击!
我亲身体验了这些
我感到荣幸
我要对非难他们的那些人
皱起鼻子,咬着牙根
直截了当地说话:
——难道你没有看见平原上的春天吗?
难道你没有看见平原上血红的斗争吗?
我要用早晨的玫瑰
插到战马红色的鬣毛上
我要要求太阳
用她的光芒给战士做一身闪亮的战袍
让他们挥动真理的宝剑
奔跑在
向光明的路上
让所有遇见他们的人
都禁不住齐声高呼
——万岁呵!人民的战士!
一切光荣属于你
不朽的功绩属于你
春天的手抓住了一切
而你的手
抓住了春天的一切
七
为什么呵
我的心——这样沉重
有着少年人习惯的忧伤
烦恼和郁闷
我不轻易说到这些
我知道:什么
我的血将为它而流
其实我无须重申我的决心:
我要用我全部的血液
在我的被诱惑的青春的日子里
勇敢地
去爱——
爱春天
爱大地
爱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们
爱这平原上的火红的斗争
并且——
去为爱而死!
我走了多少路程呵
我忍受过多少艰辛呵
我有多少春天的梦呵……
祖国呵!
从来我没有像今天这样地爱着
有许多允诺
甘心为你受苦
要做你忠诚的卫士
不曾有半句话埋怨
也没有要求些微的慰劳
——一至于此
我是不会说谎的
我在这里是
走了又走呵
看了又看……
积留在我的脚趾头里的
你江南的泥沙呵
在三月的
和暖而柔软的
泥泞的路上
那伙伴们走过后留下的
许许多多的足印中间
那瘦小的一个
就是我的
如今该也积满春水了……
我在路上唱着歌
这歌——
模仿春天所唱的
感染了大地的诱惑
叙述着我初恋的心
是怎样天真烂漫
我在路上想着这些
激动地挥舞两手
老实说
我是带跑带跳地走着
——一个难忘的日子呵
我想了许多
并为这一切所鼓舞
惊讶而又满意地
感到了
今天
我已经再也遏制不住
我的热情的泛滥
我是再也不能掩蔽我的希望了
相信我的话吧,同志们
凭我的忠贞起誓
不要以为那是近于疯狂
我要去呵
不能这样长久地盼望着他们
我要
冲上去
不顾一切地
向着所有的受难的城市和村庄
我要跌倒在她们的怀里
在那里
去流尽我痛苦的眼泪
我将用颤抖的声音
去告诉每一个亲人
一个确实的消息
我将这样地去说焦我的嘴唇
“春天来了
胜利来了
我是来报信的!’
作于一九三九年春
战斗在茅山下
陈子谷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在山头,
枫叶红遍了原野;
别嗟叹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注:
这首诗当年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广为流传。庄江生、詹尖锋说:“陈子谷这首诗,流传到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大家看了都很喜欢,有人把它抄在本子上,有人将它背熟记在心上。”有人还为之谱写成歌。陈子谷在《皖南事变前后》一书中,写到在苏南一次行军途中,“这时不知是谁,用高亢的声音,唱出了这样一首新歌(歌词就是这首诗,略),我们望着布满山道两旁的红色枫叶,随着歌声的鼓舞,快步前进”。
陈子谷(1916—1987),广东澄海人,泰国华侨。1934年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诗集《宇宙之歌》。1936年回国。1937年到延安。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当过战地服务团三大队副队长、敌工干事、支队敌工科长。1940年,他把去泰国募捐的6万元和分得的遗产20万元(相当于当时新四军全军两个月的军饷),全部交给新四军。这一壮举受到《抗敌报》的通报表扬。叶挺赞扬他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说等胜利以后,要打一面金牌奖给他;并在皖南事变后被囚禁时写下的《囚语》里,还特别提到他,希望他能“免党狱折磨之苦”。陈子谷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于1 942年在上饶集中营参与领导了茅家岭暴动。暴动成功后,在武夷山游击一年多后才得以归队。1949年后,曾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58年,被打成右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著有《皖南事变前后》和《上饶集中营》。
这首诗的作者,有的说是作家丘东平。1990年第4期《大江南北》上,刊载了歌曲《茅山下》,署名丘东平作词。歌词除四、五、六句中的个别词、字外,其他与这首诗完全一样。歌曲的附记中说,1946年3月间,陈辛仁将丘东平遗作《茅山下》诗一首送交陈大荧,誉为“历史性的成功作品”,希望谱成歌曲。1999年出版的《新四军歌曲》收入这首歌时,也署名丘东平作词。但在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陈辛仁等人怀念陈子谷的文章中,却有这样明确的说明:陈子谷“写下一首记录当时我军战斗的壮烈而动人心弦的歌词(引用了这首诗,略)。后来在苏北反‘扫荡’中以身殉国的作家丘东平,把子谷这首歌词作为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茅山下》的主题诗”。看来,把这首诗的作者题为丘东平是误传所致。
在哨上
高占标
深夜里,
我一个人握住枪,
站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那草棚的门前,
月亮从山那边落下,
大地一片昏黑:
正像暴风雨将来的刹那,
那情景非常可怕。
我想:要是敌人来摸我的哨岗,
就准备给他一枪。
在山脚下——
那古老的村庄上,
小狗嗥嗥的恶叫。
我想:大概是敌人来了。
我隐蔽那草棚旁边,
凝视着那敌人的方向,
——那模糊的黄泥道上。
一个高高的暗影,
渐渐和我的视线接近,
我喊——口令!
那回道的是:老百姓,
他报告敌人的阵营,今夜没有什么动静。
然而遥远的古城上,
仿佛闪现一盏红灯,
那灯光,时明时暗。
又引起我很大疑心:
今夜敌人的沉寂,
也许是准备明早的攻击。
我因此怀着一颗警戒的心,
静静地站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等候着天明……
五月一日寸新四军
注:
原载《抗敌五日刊》第1期第3版《文艺》。1939年5月11日。
学习
樊其祥
大树下面是我们的课堂,
用不着高楼和洋房,
集体生活是最好的教育,
群众是我们的先生。
何必化钱进学堂!
学习艰苦的作风,
学习优良的传统,
学习,学习,学习,
不断的学习!
学习新的军事技术,
也有了政治武装头脑,
更学会了文化会唱歌看报,
敌人看见这种军队只好逃!
注:
原载1939年5月21日《抗敌报》第3版“青年队”副刊。作者系新四军四团一营青年战士。
新四军很重视学习,学习气氛很浓,但学习条件却非常艰苦。不要说在连队,就是在新四军的专门教育机构——新四军教导总队里,也没有专门的教学设施。露天教重(操场或野外),席地而坐,便是常见的课堂教学场景。
向你敬礼史沫特菜同志
若楞
向你敬礼,
亲爱的史沫特莱同志!
你伟大的人类——
被侵害的民族的诚挚的友人,
全世界被榨取的劳苦大众的爱人!
你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你是一阵蕴藉的春风,
你是被残害者的英勇的战斗号声!
在亚美利加州,
你曾向无耻的强盗主人战斗
而夺回你的幸福自由,
在那里,
还有那悲惨的棕红的印第安兄弟,
那口口的乌黑的亚非利加兄弟,
你为他们向世界向人类
控诉了那非人的奴隶生活,
你也指示了他们为自由解放的斗争!
在中国,
在亚细亚的东方海岸,
在蒙古风沙地带的山巅,
在黄河的急激的浊流的旷野,
在扬子江的苍郁的田园:
你猛烈的火焰燃烧着
为祖国抗敌的子民们的心脏,
你蕴藉着的春风温暖了
被残杀、奸淫……与饥寒、流落的
苦难百姓,
你光芒的剑锋,
戳穿日本法西斯疯狗的暴戾狰狞!
你向全世界向人类
射出了正义的愤怒,仇恨的语言!
你海燕般卷入我们的抗战洪流,
你更号召全人类
共同来保卫这世界和平的堡垒!
你——
中华民族的伟大友人,
亲爱的史沫特莱同志,
得你的指导,
我们抗敌阵线会更广大坚强!
由你的号召,
全世界正义的人类
将一起来共同消灭法西斯野兽的疯狂!
从你的帮助,
在这被凌辱被侵害的国土上,
我们要用我们的鲜血来浇灌,
使那金色的光明的嫩苗生长,
使那绛色的幸福自由之花开放!
亲爱的史沫特莱同志啊,
那时呀,
我们要摘下那最鲜红美丽的一朵呵
挂在你的胸膛!
亲爱的史沫特莱同志啊,
你伟大的人类
向你——
我,我们
一致举起为民族为人类的自由解放
的革命的手,
敬礼!
注:
原载《抗敌五日刊》第3期第3、4版《文艺》。1939年5月26日。
史沫特莱(侣94—1950),美国进步记者、作家。她于1928年至1941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作采访报道。期间,参加过进步文化活动,与鲁迅等人有交往;采访过苏区;抗战期间,到过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过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1938年,她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访问。她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积极而又热情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她对中国人民极为友好,“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她说如“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遗嘱将骨灰埋在中国。
她的著作甚多,其中,《中国的战歌》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的战地报道。
营火
彭燕郊
呵!五月的榴花般的灿烂呵!
照亮眼睛的火焰的欢乐的舞蹈,
青蓝的、橙黄的、闪金的、血红的……
雄壮的舞姿,美妙的舞姿,
跳跃在河岸上似的
水影般的摇晃,水影般的荡漾,
红的涟漪的波动,钻石的七棱色的交替,
青云,在无限好的夕阳下
变成明霞般的彩蝶了,
突然打开的金扇,扇开了
芬芳的火的香气,
踊跃而出的
初升的太阳般的急步!
有兴奋的脸庞,
感激的笑,和孩子般
受到爱抚的娇气,
笑着,叫着,拥挤着的一群。
火焰的节日,
火焰的联欢,
火焰的庆典呵!
火焰喷涌,
火焰翻卷,火焰飞溅,
在大红月亮般的醉态里,
在振翅翱翔的赤燕的盘旋里
未来含笑着迈步前来,
乐园的门
为我们开启了!
我们,褴褛的、卑贱的、
穷苦的一群,
是被火光照耀成金色的巨象,
而有叱咤风云的雄姿了。
虽然此刻,
我们冻僵的双手
捧的是水淋淋的破旧的单衣,
赤脚上的草鞋
也给烤得冒出水汽,
十几个人
共吸一支胡乱卷成的苦味的烟卷……
无私无畏的心永远向着光明,
虽然是,呵,虽然是
褴褛的、卑贱的、穷苦的一群,
却潇洒地吹着口哨,唱着豪迈的歌,
笑谈中鄙视一切的困难和畏怯……
让火焰用热情的手,
殷切地
衔着邀请的使命
——火焰,未来所派遣的使者呵
向我们不停地招手,
拉着我们的手,拉着我们的衣襟——
向前,向烈火的道路奔去呵!
保团的捷音
方徨
二营营副他姓萧,
年青英勇智谋好。
扮了个,青年老诚庄稼汉,
探入虎穴观根苗。
朱府顺安通公路,
每天“皇军”摇头摆尾大队过。
路两旁,有那密猛树林子,
土冈瓦砾和坟墓。
营副地形看端正,
回来召集弟兄们。
他说道:此去胜利有把握,
大众勇敢提精神。
披星戴月赶路程,
一夜路途五十零,
到那里,六连隐蔽树林内,
突击队四连来担任。
神不觉,鬼不知,
刚到清早七八时,
便一见走过三个狗侦探,
怕死大队后面跟。
轰的一排手榴弹;
机关枪声“哒哒哒”,
接连起:“哗来哗啦”叫口号,
打他措手来不及。
咱们弟兄多英雄,
火拼肉搏八点钟。
鬼子一共廿三个,
结果一个不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