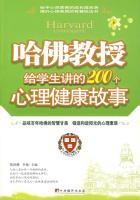陈洪金
那是在我一直向往着的城市里,当我和表弟满脸风尘地出现在车站的出口处,对着那一片陌生的土地和土地上高高的房子,怀着一种崇敬与惊奇的目光扫视这个城市的时候,那里的黎明正在到来,空气里有一种冷冷的意味,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就像是一个秘语,让人对它们又是好奇又是恐惧。
陌生的城市,它的清晨里,没有鸡声和犬吠,没有水声和露珠,没有鼾声和树林。当我们走在那些宽阔的人行道上,看着前面几个正在晨跑的影子一耸一耸地来到我们面前,然后再一耸一耸地离开,喘息声沉重地表达着一种生活的姿态。我们的身体上,也布满了汗水,可那是一种微微的紧张所引起的汗水。细密的汗水,表明我们对于一个刚刚闯进来的城市,这个不属于我们的地方,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不知所措的脚印。
表弟的肩膀不时地与我的肩膀磨擦着,一些车子,在街上飞快地驶过,它们每过去一辆,都会带起一些灰尘,让我们的鼻孔明显感觉到那空气里的很多的刺激鼻粘膜的颗粒。经过了一个夜晚的宁静的城市的街道,收集了所有在天空中飞扬的纸片和人们在夜色里随意地丢在路上的纸片。当汽车旋起的气流波浪一样飘荡过去,那些纸片也就在空中低低地扬起,飘了几米远,又落下来。紧靠着高楼底层的店铺紧闭的卷帘门,着了地,向着我们漫不经心的目光展示着减价、展销、招工、出租的字样。僻静的角落里,我们还看到那些密密麻麻地张贴着专治性病的广告、代办文凭证件的电话号码、房屋出租的价格。偶尔有一些人,睡眼朦胧地路过我们的身旁,浓烈的香水味,裸露的臂膀,向我们展示着一条陌生的路途。城市的早晨,在我们的眼里,就像一个尚未洗过脸的老妇人。
在我们居住着的乡村里,更多的文字就是“要想富,水电路”、“十分珍惜每一寸土地”、“一胎安环、二胎结扎”、“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刚刚进入我们的视线里的城市,我们看到的文字,在还没有来得及关闭的霓虹灯的闪烁中,是某某某夜总会、某某商城、某某有限责任公司、某某电脑、某某西服、某某大酒店。是的,我们在那些被玻璃包裹着的高楼里看到了钱,它在电流发出的光芒中,用尽了各种色彩,诱惑着我们远道而来,想要挣上小小的一把破旧的钞票,带回家去,补贴村子里年复一年地生长着的庄稼。在乡村,在稻田里,我们梦想着一个城市能够给我们以温暖和希望。
车子无动于衷地经过我们的身边,我们的鼻孔里充满了汽车尾气那浓烈的汽油味。城市里的灯光渐渐熄灭,街道上是越来越多的人群。一家又一家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的餐馆,开始对着街上匆匆忙忙的行人敞开了门厅和窗口,广场边上的小摊点,冒着腾腾热气,牌子上写着:“包子!豆浆!牛奶!米线!”门口:面孔。背影。面孔。背影。面孔。背影。皮鞋。西装。背心。短裙。红发。眼镜。屋内:餐桌。纸巾。嘴巴。手提袋。卫生筷。找钱。书包。吸管。汤匙。一碗面条,少加辣椒。三根油条,一杯牛奶。一碗米线,两个包子,一杯豆浆。一碗米线,大碗,盐多放些,快点上来。
我和表弟绕过了广场上的小吃摊。虽然有老妇人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去“请”点什么,但是我们听说吃了那里的东西会拉肚子,就没有停下迟缓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们没有停下来,看那老妇人很不高兴的样子,自己也在心里觉得好像是拂了她的面子,甚至是得罪了她。怀着一种内疚的心情,我们迈进一家吃客不多也不是很少的普普通通的餐馆,认真地看了看贴在墙上的价目单,打算每人吃一碗面条。我对窗口里面的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不知道具体岁数的女人说了两遍:请您给我们两碗面条!女人用普通话对我们说:“到门口买餐票”。我们在门口买了餐票,递进去。站在窗口等。陆陆续续地又来了两个人。不知道他们要吃什么,他们讲本地口音。我们等着。等着。那两个人端着碗,吃得满头大汗。我们终于等来了我们的面。进来吃早点的人渐渐多起来,餐馆里人声嘈杂,我装作一本正经很轻松地吃着一碗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面条,表弟也跟着我,装出笨拙的一本正经,吃一碗不知是什么口味的面条。
阳光艰难地从楼群之间照到地上,我们从天桥上走下来,经过一条窄窄的小街。街道两边是低矮的百货店、音像店、服装店、雕刻店、中药店、理发店,然后是一家小学。我们路过小学的时候,刚到学校门口,从后面冲过一辆自行车,擦着了表弟的肩膀,却使那骑车的孩子把握不住方向,撞到门边花台侧面的一棵小小的梧桐树上。孩子连同车子一起滑倒在地上,他把车子扶起来,转过头来,让我们看到了他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他看看我们的样子,冲着二十一岁的表弟骂道:“小杂种,眼睛瞎啦?”我们没做声,继续走路。
行人如潮。在到处都是水泥地的城市里,我们走得疲惫不堪。眼前不断变换着的陌生的面孔,抬着头不停地往前走着。商店里传来各种各样的音乐,与路上的车声混在一起,仿佛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不知道走过了几条大街小巷,我们来到一个宽大的广场。那里坐满了人,他们望着广场中心那些手里挥舞着装饰了长长的绸穗的钢剑的老人,缓慢地,一招一式地比划着。在广场边上,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的地方。实在累极了,我们在一家酒店的第一级台阶上坐下来,望着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发呆。正当我们兴趣浓厚地观望着路中央那不停地比划着手势、嘴里含着一只哨子“唧唧”地吹着的交警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一个穿了黑色制服的人,用不是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吼:“滚到别处去,再在这里死挺着,老子踢死你们!”我们赶快站起来,脚底又酸痛起来。
楼群高高地站在我们的目光难于抵达的地方,遮住了天空中飞鸟的影子,也遮住了泥土向着窗子旁边的树丛弥漫的欲望。我和表弟,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像两只蚂蚁,被向往了很久的城市惊得目瞪口呆。中午很快就来了,在城里很偏僻的一个地方,我们走进了那街道背后被高楼遮住了的低矮的房子。城市里窄窄的巷道是用砖头砌起来的,天长日久的风吹雨淋,砖头都变成了黑色,一种落满了灰尘的很肮脏的黑色。我跟在表弟的身后,左一拐右一拐地走得快晕头转向的时候,才走进了一个小得让人窒息的院落。院子里晾晒满了男人和女人的各种衣服。一个胖妇人,穿着一件跟我嫂嫂那样旧的白得发黄了的短袖衫,腰间的肉一浪一浪的,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她胡乱地打了结的奶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