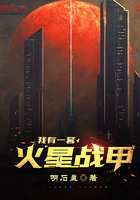不想那赵御医只道:“看来那墨砚是探花郎病症关键的所在啊,只是不知道那墨砚是探花郎在哪里的来的。”
二人一面说着,一面像夜子轩的房间走去,那夜文宇也不知道,便打发人去喊来向官。
向官也听说了公子突然醒来,而且还无头无脑的说了那句话,可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嘴臭,老爷是断然不会让自己去看公子一眼的,所以便也老老实实的给公子煎药,也连同方太太的跟着一起煎了。
此刻听见丫头来传话说老爷叫自己回去,不由得又惊又喜的,便将药罐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丫头,就连忙匆匆的回了夜子轩的院子。
一见夜文宇,便连忙行了礼,一面问道:“老爷,公子醒了过来么?”
夜文宇看着此刻的那满脸兴奋的向官,并没有回他的话,只是问道:“公子的那方被打碎的墨砚,是哪里买来的?”
这个向官想起来,似乎不是公子自己买来的,所以便回道:“这个小的不知道,不过听说是人家送的,在公子新婚的那天给送来的。”至于是谁送的,这个恐怕自己不能说。虽然公子没有向自己提起过是谁送的,但是只要看着公子那么宝贝的对待着那方其貌不扬,而且也不是什么珍贵之物,出来外行上有些新鲜别致的墨砚,自己也能猜出是谁送的,才能得到他这样的宝贵着。
“送的?”夜文宇有些惊讶,子轩是对待朋友重情重义,可是也没有重到这个份上,会因为朋友送的一方墨砚被打碎,而病成了这一个样子,说出那样的胡话来。
不由得有些怀疑的问道:“谁送的?”
向官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地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小的不知道。”
“不知道,你整日里跟着少主寸步不离的,他的什么事情不是不知道的。”夜文宇明显就看出了他的心虚,他定然是知道那墨砚是谁给的,可是又不肯说。心里是不由得更加的判定了那方墨砚的来路果然是不正当,说不定是个女子送的。
而夜子轩因为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那个贱人,反负了那个女子,所以心里觉得对不起那女子,所以才如此小心翼翼的把她送的东西珍藏,如今东西叫水依然给砸碎了,又给方太太毫不知情的给扔了,现在他大概是有些心死了。
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任性过爱过的,自然知道这爱情指教人生死相许,现在当然懂得他的心思,如今这么来看,只有那个女人来了,在他的床头唤着他的名字,或是说着他们之间的事情,恐怕才会让他有好的希望。
果然,夜文宇这里才这样想到,那赵御医便道:“九十九天离恨天最高,三十六病相思病最苦,如今我看探花郎是受了相思病,而且那放墨砚的来处是至关重要的,如今那墨砚的主人若是亲自来探花郎的床前的话,定然是能让探花郎信过来的。所以我小书童里若是知道个什么就还是说了吧,若不然恐怕你这公子的病是难以,单不说能治断根,就是想让他醒过都很是艰难,难道你就能这样看着你家公子在病痛的折磨么?”赵御医说着,看朝向官道。
向官的心里却是一阵纠结,若是公子喜欢的是那平常的贵女,即便是公主都好,可是公子喜欢的是原来澜四爷的妾室,现在将军府的二夫人,这叫他如何能说出来,不但是在影响到陆尔雅的声誉,二来少主若是醒过来之后,也不会放过自己的。少主那么信任自己,让自己知道他心里挂念着的人,可是自己却出卖了少主。
可是自己若是真的不说的话,少主真的像赵御医说的那样,连醒过来的可能性都不大么?然即便是说了,老爷会拉下脸去请陆尔雅么?如今两个府邸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夜文宇见向官还不说,不禁着急起来,“你难道是要把公子害死么?还不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老爷,不是小的不说,只是这对方的身份实在是”实在是叫他不敢说出来,若是老爷知道少主钟情于陆尔雅,而且还是单相思,一思就是快两年的时间里了,这还了得么?说不定老爷一气愤,索性的不在管公子了,这可怎么办?
夜文宇听他提到对方的身份上去,不以为然的说道:“难道现在还有我们永平公府见不得贵女千金么?如今就算是那个公主,若是我们永平公府看得起,那也是她们的福分。”
只听向官低声唯唯诺诺的说道:“她不是什么高官贵女,而是人家的妻子。”
“什么?”夜文宇实在是有些反映不过来,这夜子轩向来是最听话,最规矩的一个儿子,怎么可能去跟着旁人之妻有染呢?不由朝向官骂道:“你简直是一派胡言,你伺候公子这么多年,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难道你还不知道么?竟然这样诽谤他,你说你存个什么心思。”
向官只道:“是老爷要逼着小的说的,小的这会儿说来了,老爷您又不相信,反倒是说小的在诽谤公子。”
赵御医见这向官不过还是个童儿,知道个什么就说什么的,哪里会去说谎骗自己的老爷,便连忙劝说夜文宇道:“夜大人,你先不要着急生气,让这小书童把话说完,现在救探花郎的性命要紧些啊,这样留在以后论吧。”
夜文宇闻言,也只好是作罢,如今自己这三房有出息的就只有夜子轩了,自己还指望着他给自己在大房二房的面前争争脸,所以是断然不会让他就这么撒手而走的。所以便又问道:“那你说,是谁家的妻子?”
向官低声回道:“就是状元郎的亲妹妹。”如此一说的话,老爷应该是知道的吧,公子与陆长文是同窗,自然是知道他妹妹为何人的吧。
果然那夜文宇当即便反映过来,大喊了几声:“冤孽,真是冤孽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说着,似乎又觉得向官是在糊弄着自己,一把提起向官的衣领,“你胡说,子轩何来有时间与那个女人见过面,况且那个女人如今是将军府的人了,他面都没有见着,怎么可能会?”